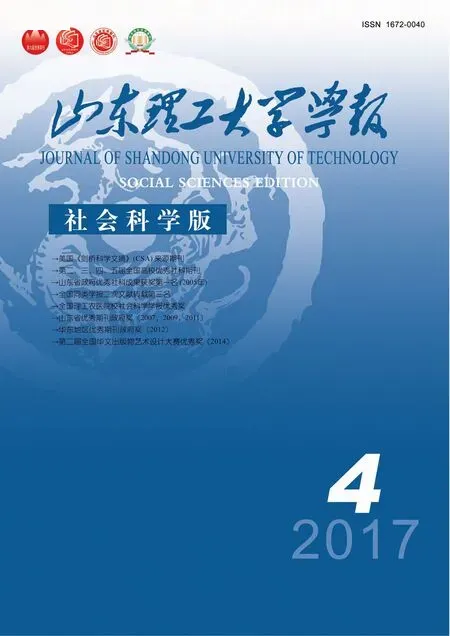基于民法占有的动态解构
吴庭刚,朱伯玉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基于民法占有的动态解构
吴庭刚,朱伯玉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占有的主要问题有占有的概念、对占有的保护原因以及后者在具体制度上如何实现等。占有的概念应当体现占有本质。对占有概念的界定与区分直接体现为对占有保护原因的理解,继而影响到保护政策的制定。基于对占有的动态观察,可将占有解构为三部分:占有的取得—占有之事实(包括自然事实与法律事实)—占有的效果(包括自然效果和法效果),此三者恰好形成一个辩证法式的圆圈。这种动态的解构意在帮助理解占有现象以及对各种占有保护作出相应的合法性证明。
占有;占有取得;占有事实;占有效果;动态解构
自19世纪初萨维尼与耶林之间从占有保护而介入的争论,到由霍姆斯发起的普通法系英美法学家的大讨论,占有本质一直是民法理论中极富争议的问题。迄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仅在大陆法系范围内就有权利说、法益说、法律关系说、权能说、事实说等①事实说为现今通说。从立法上看,事实说亦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承认,如《法国民法典》第2228条、《德国民法典》第854条、《瑞士民法典》第919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40条。,在普通法财产法中既有像“当占有与财产法联系在一起时,它的真实含义是指一系列占有权利的集合,这种集合总称为占有权”[1]4的说法,又有如Pollock提出的“相对所有权说”,即占有是一个相对的所有权,可以对抗除了真正所有权之外的任何人[2]15-16。法学界的众说纷纭丝毫没有影响到占有本质对整个占有体系的重要性。而对占有本质的认识程度直接影响到对占有概念的界定,后者直接决定了对占有保护原因的理解,继而影响到保护政策的制定。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动态视角对占有本质进行解构。
一、占有的概念及解构方法
概念必须符合其本质。对占有概念界定之所以存在巨大争议,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人们对于占有本质认识的不足,以及占有自身的模糊性。目前人们对占有概念的界定仍是在经验所及范围之内,这导致不易判断何种占有需要保护,以及对这种保护如何作出合理性的说明(譬如对盗窃占有的保护)。
(一)作为制度的占有的概念考察
汉语中本无作为制度的“占有”(英possession,德Besitz,拉丁possessio)一词。“占有”一词系由日本人翻译德文著作时创设,后传入我国,清末继受制定《大清民律草案》规定了“占有”这一制度[3]698。因此对占有概念的考察,应从西方的论述开始。“欧陆民法上的占有制度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始自罗马法的possessio,融合日耳曼法的Gewere,而成文化于各国民法典”[4]142。与纯粹理性法学的各种建构概念不同,占有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一个贴近文化范畴的语词,在各种语言中有着迥异的所指,有的民族指的是一套制度,有的民族则是指一些散碎的生活惯例(common practice)。诚然,同一语言符号所指不同,意味着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自有其各具特色的占有规则,但最先对其进行理性的制度化建构的无疑是拉丁民族,其思想精髓则见诸罗马法。对作为制度的占有之考察,也应从罗马法开始。
通过对罗马法中possessio制度产生根源的历史考察,萨维尼认为其滥觞于罗马市民法中市民对罗马公田的占有,以及对于这种占有进行的保护(类似于在裁判官令状中的保护),继而这种为公田而发展出来的占有也应用于私田之上,随着占有令状的引入和占有裁判程序的不断简化,占有便被作为制度被固定下来*相反的观点:耶林认为是令状催生了占有制度。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55页。[5]141。而对于日耳曼法Gewere起源则不甚明朗,有认为是从对物的支配关系发展而来,亦有说是对部落共有土地的占有发展而来[6]26。德国人从自身的日耳曼民族性出发,以Gewere为主旨创新融合两者,形成现代大陆民法中的事实与权利混合属性的占有制度*除法典的民族性考量之外,尚有民法体系化的技术要求。参见[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与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174-178页。。
(二)占有的解构方法
1.占有的静态解构
(1)占有的静态解构原因及合理性
萨维尼在《论占有》之“占有的取得”中系统阐述了抽象自罗马法的占有要素,即体素和心素,并明确以之作为占有的构成要件,从而为占有解构奠定了基调。这种解构方法的历史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萨维尼之后的学者均或承认或默认并在事实上采取了这种解构方法;同时可以看出,迄今大陆法学家争论不休的所谓占有意思之界定问题亦归于在此大框架之下的小分歧。纵然单从此书篇章结构来看,这仿佛是对占有动态要件(“取得”是个动作)的分析,但实际上,萨维尼作此区分的目的在于更方便地对“占有既成事实”进行解构。
从一事物的最初发端来审视这同一事物的方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这也是人们认知事物的普遍方法,大多数现象是可以通过这种实证方法加以研究的,特别是在进行具体案例中各种法律关系分析时。从时间层次来看,这种分析无疑是动态的,可名为“时间动态解构”;相应地,本文之所以把它归于静态之下,则是站在逻辑的立场上,把它归于“逻辑静态解构”中。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时间上动态等于逻辑上动态,但在一些特别情况下,时间上动态却可能等于逻辑上静态*关于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在法律思维上的体现,王泽鉴先生将前者名为“历史方法(historische Methode)”,而其“请求权方法(Anspruchs methode)”则可归于逻辑解构思维。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49页。,尤其是对于诸如“占有”等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复杂现象来说。因而,逻辑解构较时间解构要更为宏观些。
(2)占有的静态解构方法
在萨维尼分析抽象出占有要素的基础之上,经过二百多年民法学说历史的积淀,迄今学者对占有静态要件的分析已然十分精致完备。通说认为占有为占有人对物事实上管领力之事实,其须有:第一,对物事实上的管领力;第二,占有人占有的意思[7]84。此系根源于希伯来传统的身心二元对立思想的应用,即把占有现象在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心中意思分开来看。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是否有物之支配,不得依物理的见地决定,而应依其时代之社会的观念,客观的决定之”[8]530。问题在于对占有意思的定义从静态上殊难决断,“系占有理论上最有名的争议问题”[4]158-159,是以有各种学说予以解释。本文将在占有事实中概列举之。
2.占有动态解构的可能性:静态涵摄于动态
单纯静止地看占有的本质,便会陷入对其无法判断是事实还是权利的困境。在对占有静态解构的分析基础之上,可以将占有之静态要素归于动态要件之下,尤其是动态要件中“占有事实”这一范畴之下。
第一,所谓占有的动态要素,是把占有看做一个用逻辑理解的整体过程后解构出的各要素,即“逻辑动态要素”,可简单理解为包括“前占有”“占有中”“后占有”。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前”“中”“后”并非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上的先后,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有时可能统一。这时,“占有中”这个逻辑过程便外化为占有事实,即我们观察到的外部现象界。
第二,作为对事物的认知规律,人们最为信赖的是对静态事物的解构,因此通常做法是把一个过程划分为若干部分,分而考之。然而,在整个认知过程的最后,部分必须放在整体中来看才既不失其个体意义,又能够解释整体的功能。倘一味关注部分而忽视其整体作用,所谓庖丁解牛,窥一斑却失全豹,其意往往有所不达。
第三,静态的占有与所有权之间存在着相互交融难以明晰的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将权属或者所有权与占有权等同起来”[9]215问题的产生。乌尔比安说“要严格区分所有权与占有”,其自有历史背景与独立化之后单独保护的意义,但将静态占有与所有权武断分离产生的诸多问题却是学理上难以解决的,如对恶意占有人的保护问题。为此需要返回占有概念所以界定的源头,审视其区分目的。
综上,把占有之静态要件统摄于动态要件之下,这既是出于全面看问题的意图,又包含对静态占有理论的扬弃目的。对体素、心素的划分当解释为占有的静态要素从而被动态要件所涵摄(überhaben),毕竟运动是常态,静止是异态。作为一个期望阐述占有本质的尝试,本文把一个完整的占有过程进行了动态的解构:得占有的权利即本权—占有之事实(包括自然事实与法律事实)—占有的法效果即占有权。这一动态的解构意图以权利—事实—权利为图型(das Schema)*图型(das Schenca),康德哲学用语,意指连接感性世界与知性世界的先验主体活动。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145页。,其中首尾两个权利当同为所有权时实现重合,构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圆圈,同时体现了人对占有本质在法与非法两个世界中来往穿梭的动态认知过程。
3.占有的动态解构方法
如果把占有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必有的一些要素包括取得、占有事实以及效果。因为对于一个物理上的持有(拉丁有detention或tenere两种说法),若它想成为占有(possessio)*我们把受法律规定的世界一般性地理解为存在于思维中的世界,于是便出现了外观世界与法律世界的区分。应该说,法律视界下的世界与现象界有很微妙的关系,后者是自在的前者。,就要牵扯到原因。这个原因可能是事实,亦可为行为,这就产生了占有稳定性的问题。这里的稳定性与占有的本权相关,也是占有正当性要解决的问题所在。诚然,缺乏本权的占有是不稳定的,亦即有瑕疵的,它可能轻易地被有权人的请求消灭;同时,具有稳定性的占有也非“稳若磐石”的,它亦得因某些不可归于占有瑕疵的其他原因而消灭。但对占有“稳定性”的研究依然具有理论实益,即通过对占有的取得原因进一步抽象可以对占有取得有“自权利而得占有”(取得所有权与他物权等)和“非自权利而得占有”(行为人自事实行为、侵权人自侵权行为等)之划分。占有事实的研究在历史上可谓汗牛充栋,本文主要从其性质来分析。占有只是一个事实,但或因人们对其观察角度的不同或因抽象思维追求严谨而拟制成为两个事实:自然事实和法律事实。前者因其身处于现象界又可名为自然占有、物理上的持有等;后者则为法律视界中的事实,可名为法律占有。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所谓占有之静态要素归入占有事实,对占有事实讨论的重点在于:物理上的持有是如何转变为法律上的占有的,也即占有的自然效果与法效果之间的能动关系。占有的法效果有二:产生所有权、排他效力。前者恰恰又可以构成下一个占有的“得占有的权利”,这体现了占有的“辩证法”。
二、占有的动态解构辩证法式圆圈
基于对占有的动态观察,可将占有解构为三部分:占有的取得—占有之事实(包括自然事实与法律事实)—占有的效果(包括自然效果和法效果)。此三者恰好形成一个辩证法式的圆圈。
(一)占有的取得
1.各种取得方式
物权法教科书上对占有的取得分类一般采类似物权变动的划分方法,即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又有细分为自主占有的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他主占有的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等。无论怎样,均意在说明从持有(Detention,tenere)到占有的转变。通常情况下,占有的取得有如下几种方式:交付(交付替代)、取得所有权与他物权、继承关系、亲属关系、事实行为、侵权行为等。但是因为通过各种方法取得的占有存在着稳定性的差异,所以下面主要从占有稳定性角度对占有取得方式逐一进行讨论。
(1)交付(交付替代)
交付究为一种事实抑或行为,甚或是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均争议颇多。物权行为理论坚持交付具有意思表示于其中,即“交付构成一项真正的契约”[10]312;反对的人则力推交付为事实行为。就我国立法情况而言,《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财产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表达含糊,不易从中判断交付之性质。但不管怎样,交付“就是出让人向受让人转移占有的行为”[11]417,因此交付是取得占有的原因。物权行为与否讨论的问题也就在于这里的“占有”究为法律占有抑或自然占有,对此本文不予详究,由于占有取得因系法定成就,姑且看做法律占有。
交付的原因一般视其债权行为而定,在他物权的设定时应视他物权之取得行为是否有瑕疵,如主债权等;也有可能受其公信力瑕疵影响,如因买卖合同或租赁合同而交付债之标的等。所以在交付时,占有的稳定性应视交付发生原因的稳定性而确定。如A向B购买一房屋且已交付并登记,则A取得房屋之占有且可对抗一切他人。但若尚未登记,而A自然依交付取得占有,且此占有因债权本权对抗B。但因其未登记,为公信力之瑕疵,故此占有不得对抗有所有权本权之他人C;又倘A发现该合同因欺诈而被撤销,则A之占有亦可能丧失,缺乏稳定性。另外,传统民法上尚有占有锁链(Besitzkette)一说,系对无权处分而得的补充性说明[12]68-69。
(2)取得所有权与他物权
因取得所有权等而获得占有,譬如A欲赠一物于B,于是将该物置于B衣袋之内但并未告知。此时B因无占有意思殆不能享有占有。若A告知B此情事以后,B作出受让所有权之意思表示时其持有当然转化为占有。我国《物权法》第38条规定“所有权是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故所有权具有占有之权能,对它的取得也自然获得占有。一般来说,拥有所有权作为本权的占有是最为稳定的。但应当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场合之中,取得所有权和他物权与交付在外观上并无不同,且在动产买卖中所有权移转更是自以交付为要件。譬如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买卖中,买受人获得的占有究竟是基于交付还是所有权,实难区分,且无实益。此外,有时随着所有权和他物权取得的只是“间接占有”,而并非对物的直接控制,在外观上殊难判断,又使得这个问题表现得愈发复杂。因此在这里当需要对占有稳定性进行判断之时,更要严格对待。
(3)继承关系、亲属关系
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为遗产。至于继承权之标的究为遗产之所有权抑或占有并无说明,其自可推定为所有权。因此,基于继承关系和亲属关系的占有实为具所有权保护之本权。但对于有些情况,譬如A对继承原B之房屋处于现时占有但尚未移转办理登记之时,A之占有在对外关系上并无所有权之保护,仅系于继承权。在更常见的情况下,对于遗产的占有应视继承人是否构成现时占有而定,其对于并未占有的遗产可以请求现时占有人返还。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占有,亦同。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因其继承权、亲权等身份权本权而当然取得,但对于那些已取得的占有因其所有权本权而具有稳定性。
(4)事实行为
事实行为是获得占有的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如先占无主物、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等,加工、添附甚至无因管理都有可能作为事实行为获得占有*关于《民法通则》之规定关于埋藏物遗失物等个人并不能拥有所有权,系数国家所有权之规定,可视为私法之特例。但其并不可否认个人对占有的拥有,只不过其因缺乏本权导致稳定性要弱一些。。此类情况下占有之取得与所有权之取得一般来说是同步的,人们一般不去加以区分;或者说是因先占而原始取得所有权,是以总体上来看占有是稳定的。当然对无主物之占有,须依民法先占之规定始能取得所有权,否则即为无权占有,从而稳定性有可能被弱化[13]956。
(5)侵权行为
占有亦得通过侵权行为获得,如抢夺他人之钱包,霸占他人之房屋[4]216。在罗马法上表现得尤为清晰,即小偷占有物,因为他“存在真正的支配意图”[5]94,在其占有因暴力丧失时甚至可以提起制止暴力剥夺令状(interdictum de vi)。在这种情况下,占有也显然不存在本权,所以欠缺稳定性。原占有人可以提起占有返还之诉以消灭他的占有。要讨论之处在于对侵权占有人的占有,即对于瑕疵占有是否保护。通说从维护社会秩序之考量对此作出肯定解释,但其保护限于非“对于现占有人或前权利人有瑕疵”[8]592。
2.占有取得方式与稳定性
通过对各种情况下占有取得及其稳定性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对占有取得的保护是依其本权而具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导致了如下情况:虽然在理论上法律对各种占有不问取得一视同仁,但由于某些占有的“先天缺陷”,这种保护在事实上产生了差异,其外化便是占有稳定性的差异。对于那些稳定的占有,其共同特征是具有“得占有的权利”,亦即本权,诸如所有权、他物权、部分债权、亲属权、继承权等,其稳定的程度当视本权的稳定程度而定。因此,一个有本权保护的占有也可能不稳定。如在上述购房之例,在未登记时,A之直接占有具有与B缔结之契约的债权本权,C之间接占有则具有登记产生的所有权本权;若A之本权债权具有相对性,原则上不为第三人所知,故此占有只能对抗B本人,而C之本权具有对世性,并有物权效力优于债权效力之原则的适用[14]80-81。问题在于倘C明知A与B债之关系时是否也受此债之约束,本文认为此系举证问题,若A能举证说明C之明知当然可以对抗。
(二)占有事实(静态要件)
1.哲学界定下的占有自然事实
法律调整之下的世界与客观存在的世界是同一的,同一于自在的世界,即是倘没有法律没有人类存在,所剩下的那个自己在那里(德an sich英as self 自在)的世界,也就是康德所称的本体世界;在此之上并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律世界,即“法律视界下的世界”*大陆法系的“法律关系”概念即来源于此种思想。本体世界只有一个,有了人以后才有了别的世界。后者统称现象界(die Welt als Erscheinung),有很多个,法律世界是其中一个,当然还有经济世界、政治世界、文化世界等,不一而足。。当然,本体世界并不是固定下来一成不变的,它同时也是潜在的法律世界。这样就可以解释从持有到占有的转变,即这个转变只是观念*可能用“名分”要更形象一些。《商君书·定分》:“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此处“分定”便意味着观念上权利意识的建立。上的,在外观上我们看不出什么不同。而占有恰恰是连接这两个世界的中间部分。于是在占有这里便产生了悲剧式的含混。萨维尼用了很大的力气来区分持有、占有、自然占有、市民法占有这几个概念(如图1所示),目的即是要严格地分开两个世界。
基于这一前手理论,本文试图表明:萨维尼在对罗马法占有制度进行经验性的归纳进而总结出的占有概念,与其说是仍然摆脱不了经验的束缚(如图1所示,萨维尼的建构建立在罗马法所使用的概念之上),毋宁说是不可能摆脱经验的束缚。而现代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语言哲学告诉我们:一切意在从先验角度构建占有概念的试图最终也不得不宣告失败。那么,剩下的方法便是“回到事实本身”,这里所说的事实是在逻辑上被理解的事实,它超越了单纯经验本身。逻辑是能动的,因之逻辑的事物是动态的,于是有了本文对占有概念的动态要件的界定。
诚然,存在单纯自然事实上的(reinen und natürlichen)持有而不构成占有的情景。对于这种情况,法律一般不予过问,只有这种持有通过各种途径*如持有人具有了占有意思、持有人欲出售其持有物等。扬弃(aufhaben)其自身而成为自为的(für-sich-Besitz),即进入法律的视野时,才获得法律上的意义*马克思将之表述为“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82页。。这样占有自然事实便过渡到法律视界下的占有事实。

图1 萨维尼对罗马法占有概念的建构[5]43
2.法律视界下的占有事实
自然占有若想成为法律占有,尚需要法律的存在。一旦身处现象界的物理持有进入了法律的视界,法律占有便产生了。不同于哲学思辨上的动态认识,法律一般仅仅把占有看做一个既成的静态事实。既然是作为静态的事实,占有事实便包括以下方面。
(1)对物事实上的管领力(tatsächliche Gewalt),即体素(corpus,体控)
萨维尼将之界定为:在取得时,为动产的现时在场,且动产可在任何时刻被占据;在持续时,为占有人根据其意愿而再现直接关系的能力[5]81。
(2)占有人占有的意思(Besitzwille),即心素(animus)
至于所谓Besitzwille究应如何界定,则众说纷纭:一是所有意思说。萨维尼所说的心素是占有人将物据为己有的意思(所有意思animus domini)。二是支配意思说。此为温特沙伊德(Windscheid)的主张,占有的意思是支配物的意思(animus dominandi)。三是为自己意思说。为邓恩伯格(Dernburg)所坚持,占有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而持有物(animus rem sibi habendi)[7]85。
(三)占有的效果
拟制而成的不同占有事实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自然效果和法效果。这种产生并不是严格一一对应的,即并非截然的“自然事实→自然效果”“法律事实→法效果”,而是交互杂糅的结果。同样地,排他效果亦得及于法律事实,自然事实亦孕育着法效果。占有天然具有的这种无论法律承认与否均有的排他效力,也是私力救济得以存在的原因。诚然,法律为追求社会秩序之平和并不希望其被滥用,是以有“禁止私力”之原则。法律对若干允许私力救济的场合亦严加限制,并努力将之引导到法律救济的道路之上。法效果(Folgen des Besitzes)即占有权利(德Besitzrecht,拉丁jus possessionis),萨维尼认为在罗马法中仅有两种:时效取得和令状(interdicta)[5]7。在现代民法体系中则表现为维持功能和公示功能[15]105,详言之,就是产生所有权和排他效力,前者又是在最高层次上的后者,体现了由自然效果向法效果的上升过程。
1.自然效果:排他效力
排他效力当归于占有的自然效果之中,也即这一自然效果本身就包含保护的涵义在内。至于占有具有的这种类似“免疫功能”的自我保护,其根源乃在于人类追求和平安宁生活之天性。正如法律是对现实生活规则的高度概括,这种排他效力也被法律所正式接纳而成为民法上的私力救济。同时,由于它具有的潜在的对社会秩序冲击之危害性,法律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占有的这种效力早在古老的罗马法占有保护令状中窥得一斑,萨维尼也正是从“是否得产生令状”这一角度来界定法律占有与自然占有(即持有)的。诚然,在罗马法时代关注程序救济的指导思想下,排他效力更多地表现在占有人的诉讼权利上,而在现代民法,占有人的实体权利则受到更显著的关注。这也导致了占有事实保护与占有效果保护在现代法中的不易区分。
2.法律效果:产生所有权
仅仅凭借天然的排他效力尚不足以使一个占有被稳定维持。换言之,一个占有若想被稳定维持,则本权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那些“非自权利而得占有”的情况,如先占无主物取得的占有,法律上并无也不可能有所谓“基于先占权的占有”之类的说法。这时作为对占有人的救济,法律便赋予占有可以从自身产生所有权*可归于所有权的原始取得,此亦罗马法上所有权原始取得的唯一方式。来作为本权对抗世界的效果。民法中这方面的制度规定主要有时效取得和善意取得。
在罗马前古典法和古典法时期,有诸如取得时效、长期取得时效、特长取得时效、古老的取得时效、特长消灭时效等若干规定。在优士丁尼法,则只存在时效取得(usucapio)和特长时效取得(praescripito longissimi temporis)[16]165,后者不以占有取得的正当原因为要件。应注意的是,罗马法中无善意取得一说,而善意取得作为近代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在德国民法典融合罗马法与日耳曼法“手护手”(Hand wahre Hand)原则的基础上创设[17]474。就我国立法现状来看,《物权法》并无时效取得的规定,但有善意取得制度。后者的构成要件综合视之有五:标的为动产或不动产、无权处分、合理价格受让、交付或登记、受让人善意[18]208。由此可见,单纯占有事实并非取得所有权的充分条件;而所谓“善意”,不过是对占有取得正当性的另一说法,要解决的亦是占有稳定性问题。善意取得所有权制度的规定基于占有的公信力,而这也恰恰是占有本身法效果的自我实现。
三、占有的动态解构实益
对占有之保护,乃基于何种思想,为长久之争议。自19世纪以来,德国法学家们总是提到两种理论:一种据说源自萨维尼,认为是保护公共秩序(法律和平思想);另一种则是耶林的观点,认为是为了对所有权给予更完全的保护[9]216。正如本文已阐明的,这些争论生发于对一个问题自不同视角的观察,即对“占有”概念内涵的认同差异。诚然,萨维尼对占有概念的界定已经包含了动态的倾向,尽管这种动态仍停留在时间范畴中。作为对萨维尼学说的扬弃,占有概念的逻辑动态内涵包括占有事实在内,而后者的二重拟制性质即是占有保护得以私力与法力双重救济的原因:对占有本权的保护意味着对占有权属的保护*当然,又因为此种权属多为所有权,耶林的著名论断亦应是在此意义上得到理解:“占有是所有权的事实状态”。;对占有效果的保护则可以较好地用作对社会平和秩序维护的解释;对占有事实的保护终极性地站在每个理性人享有的不可侵犯的人格基础之上,从而避免了既存占有保护学说的龃龉之处,收获理论实益。
占有是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复杂现象,其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法治下尤具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各种民商事交易活动日渐频繁,占有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况(如在租赁、用益权使用等中两者无法实现重合)导致的争议问题也趋于增加。而在立法工作中,我国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对占有制度仅有五条规定,且多限于无权占有。这显然不能满足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大量问题的需要,更与我国理论界的研究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仍系对占有理解的不到位。本文所提出的占有动态解构的观点正是针对此问题的一种尝试性说明。
四、结语
从占有本质及概念的界定出发,比较了对占有本质既有的静态解构方法与动态解构方法的异同之处,表明了静态解构所得的要件可以涵摄于动态要件之下。对占有概念的动态解构所得到的是三个部分:占有的取得—占有之事实(包括自然事实与法律事实)—占有的效果(包括自然效果和法效果),它们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具有动态意义的完整的占有。占有的动态解构,是理解占有现象和占有保护合法性的一种尝试性说明。
[1]F.H.劳森,B.拉登.财产法[M].施天涛,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2]Sir Pollock.F,Sir Wright.R.S. An Essay on Possession in the common Law[M].Oxford:Clarendon Press,1888.
[3]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王泽鉴.民法物权2·用益物权·占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占有[M].朱虎,刘智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杨佳红.民法占有制度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6.
[7]崔建远,申卫星,王洪亮,等.物权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8]史尚宽.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9]J.高德利,U.玛迪尔.论保护占有[M]//李凤章,译.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4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0]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M].Berlin: Veit und Comp.,1840.
[1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第三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2]李太正.债之关系与无权占有[M]//苏永钦.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3]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7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5]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M].张双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6]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7]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8]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李逢超)
2017-03-03
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立法表达研究”[CLS(2016)D74];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私法视域中的集体成员民主决策权研究”(16BFXJ02)。
吴庭刚,男,山东龙口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伯玉,男,山东青岛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D923.2
A
1672-0040(2017)04-004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