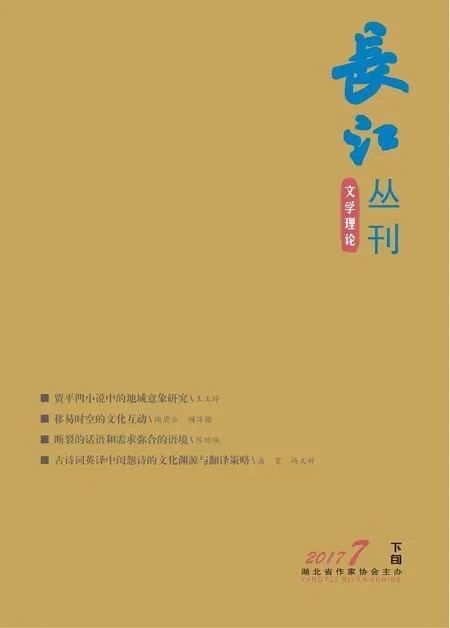六月清泉
简 媛
六月清泉
简 媛
一
鸡叫头遍,青苗就起床了。
别在胸口的花,是白绸做的,花瓣已经揉皱。她已经是第七日这样静静地坐在乡下的河堤边了。坡上的黄蝶花,沟里的野百合、山上的映山红……都卯足了劲往外挤。
她看不见这些。
眼前的蝴蝶,有的平飞,有的时高时低,有的互相追逐。青苗只是静静地看,看它们从哪里起飞,飞到哪里落下,看它们身上的花纹,数它们翅膀煽动的次数。看着看着,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只蝴蝶在半空飞舞时,还是独自的,可是当它绕到远处返回时,突然变成一对。它们变成一对时,往往是一只与另一只交叠而飞,长时间地舞动着翅膀,重叠的色彩有点眩目,眩得青苗的耳边老是响起阵阵令人焦心的刹车声。每每这时,青苗就会狂奔过去冲散这对交叠的蝴蝶,不知所措的蝴蝶慌得四处乱窜。
这是经常都要面对的局面,青苗先是静静地看飞舞的蝴蝶,之后把目光盯到一对蝴蝶上,等听到“驰驰”的紧急刹车声后就是不要命的狂奔……。
青苗觉着自己就是这只被追赶得无处藏身的蝴蝶。
当街上有人喊:不好啦,健东遇车祸,死了……她的耳膜就像被利器撞破了般难受,随之是长时间、无休止的耳鸣。如四十年代日本来袭时拉响的警报。
健东是县邮电局的维修工,常年穿梭在大街小巷,一辆破旧的二手摩托车如瘸腿的老驴,发动时总是发出“突突”的喘息声,那“突突”的声音似近又远,似远又近,只要响起,就如一把钩子——钩上的铁锈被健东的血浸透成了鲜红——紧紧钩住了青苗的魂。她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身,跑到大街上,站在邮电局门口绿色邮筒旁那棵空了心的老樟树下,痴痴地朝远处张望。奇怪的是,在屋子里她明明听到有摩托车开来的“驰驰”声,可出了大街,落入眼里的只有那团被风卷起的黄泥灰尘。
一只遭到惊扰的流浪狗站在街对面发出恼怒的吼叫。那只正顺着青苗左脚鞋带攀爬的蚂蚁也吓得四处乱窜。风卷起的黄尘附在樟树叶上,吞噬掉了樟树叶的润泽。没有望到摩托车,转身时,青苗双脚仍旧断了筋似的立不直,扶着门,才将身子勉强稳住。
对面成一字排开的小街铺面里,不时探出些人头。有些明目张胆地将目光扎在她身上;有些躲闪着,像风吹动的墙头草。他们已经习惯于青苗每天不定时像个草垛般站在路边。他们喜欢她这样子。起初是因为好奇而喜欢,后来因为习惯了而生出些瘾症般的迷恋。小街成了戏台,青苗成了戏子。
县邮电局家属楼的大门前,狗尾巴草从没有被水泥覆盖的间隙挤出来,如同此刻填充青苗心里的荒凉。她决定离开这里。
要走了?婆婆对青苗说这话时,手中依然抱着健东的遗相,泪水顺着皱纹漫布在她脸上,泪痕斑驳的纹路形如被急流冲刷过的丘壑。
要走了。青苗对婆婆说这话时,青苗不敢看她。婆婆见不得光,家里四方的窗户都遮掩在深紫色的窗帘下。她害怕走进这房子,一走进,就能嗅到尸体的味道。
健东在世时,心痛青苗上班坐得太久,怕她伤了脊柱,每天傍晚,专门陪她去河边跑步。青苗心痛健东白天像骡子般穿梭在县城大街小巷,只让他坐在江边看着她跑。
回了乡下,青苗还是天天上河边,可不再跑步了。
她在河边看见过一辆翻在河床上的小三轮,被汛期涨起的河水卷下来的肚皮撑得像个吹胀的气球样的死猪,以及那些顺着河水漂流时牵绊在河滩荆棘上的五颜六色的布条。
这样的境况有些时日了:一入黑,青苗的眼前就晃荡一张面孔,忽远忽近,并不清晰——仿佛健东遇车祸死后不时响在青苗耳际的摩托车发出的“突突”声——乍一看,觉得他就在眼前,一旦走近了,仔细看,什么也看不见了。
昨晚不同,青苗看见的面孔是清晰的——血肉模糊的脸颊旁,高挺的鼻梁塌陷成了空洞,深情的眼神凝结成最后的绝望,两腮气球样肿了起来,嘴角上的淤血结成了厚厚的一层黑痂。
就是这血肉模糊的面孔,天一黑就飘进了她的房里。
于是,像掉进万丈深渊后又栽进了水里,青苗的脸和枕头,包括她的身体,全淹在了深水里,她经常不知身在何处,甚至,常常把自已的哭声当成了白天街上飞速向前的摩托车发出的声音。
“驰、驰、驰……”
待到深夜,青苗的心却沉到最低,四肢如同肢解般摊在床上,再也无处可沉了;又仿佛一条被巨浪推至浅滩的鱼,再不借助仅存的浅水挣扎着游回去,便无路可走了。
她就这样,无声地看着床边泛黄的墙壁——村后那只乌鸦从下半夜起,一直发出有节奏的叫声——直到天亮。
调换到离娘家不远的镇邮电局上班,是她自己的决定。
在临街的邮电局对外营业厅打开门之前,青苗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尖贴在窗口黑油油的锈铁柱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门完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上,镇上通常没有闲人。可是,现在不光孩子们在街上,对面泡桐树下面还聚集着一堆大人。一只老黄狗穿梭在人群里,邋里邋遢,是那只被人遗弃的流浪狗。
这天来邮电局办事的人特别多,男人是因为仰慕青苗的美貌而来;女人是因为想打听她得了多少抚恤金而来。更有好事者当着大家的面,说,年纪轻轻就背负寡妇名声,可惜了。
二
季节,已进入了枯水时节,就像青苗的身体没有了水一样。小镇岔路口的清泉也被深秋的枯枝败叶掩埋了。一窝黑黑的浅水,早已没有了六月时节的沁人肺腑,那份丰盈也随之而去。
青苗将身子埋进了土里。她的土就是被几根黑油油的锈铁柱隔离的这几平米的储蓄前台。
直到花出现。花是街对面刚开张的小餐馆老板,烫着乱发,爱穿超短裙。她和青苗一样年轻,还是寡妇。她的男人死于矿难。“男人死前,我在家里喂猪;男人死后,我在镇上喂‘猪’”。这是花的名言。在花眼中,那些肥头大耳又经常想在她身上耍点小动作的老板是花猪;那些吃霸王餐的地痞流氓是黑猪;经常赊账的勤吃懒做的单身汉是赖皮猪。而真正的人几乎不上她这吃饭。
青苗觉得花的喧嚣与自己的冷寂同样惹人注意。望着小店出出进进的食客,离花家不到十米远的那家餐馆老板重新装修了店门,开张时放了一天的礼花。可除了招惹来一群流浪狗,以及被风吹得满天飞的五颜六色的纸屑,还有镇上人撇着嘴说出的“新瓶装旧酒”。大家都知道这家餐馆的菜是用地沟油烧出来的。对比就在于,花每天都上街口蔡屠夫那里称猪板油烧菜。隔壁老板认为问题不在于此,在于花过于暴露的身体。
花不在乎这些,依然像只彩色的蝴蝶,穿梭在菜市场、工商所、税务所……她那长了翅膀的笑声震荡着整条街,来店里喝酒的男人恨不得拖住她的笑容,不让她的笑容溜走。到后来,她真的被他们拖住了。不知谁灌了她整整一大杯,她一点也不生气,也丝毫不见醉意。往往这时,满屋的男人们都会发出满足的大笑。而花总能在这些笑声背后,听到一声微弱的长叹,仿佛从墙面上开裂的石灰缝里挤出来似的。她会装作喝醉的样子背过身去,将巴掌砸在墙上,连续这么几下,然后又扎进男人堆里。谁也没有发现,就在刚才,在她背过身去的时候,眼角已经浸湿。她的死鬼男人,午夜出门下矿前会来到床边,将他沾着煤味的嘴巴狠劲地亲她两口。而此刻,这些喝了酒的男人用潮湿的舌头舔她的脸颊、唇角时,只会让她恶心。
谁也没有发现这些。
青苗自然不知道这些。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她走进了花的小餐馆吃饭。她看着花被男人们呼来喊去,拖着花让她陪他们喝酒。竟如花的热烈一样,青苗的冷艳同样令人侧目,有男人试图拉她入席,她只顾埋头吃饭,仿佛自己与这场面毫不相干,或者只是一个过客。而心里,青苗羡慕花能这样自如地周旋在男人堆里。她甚至有些嫉妒她。
鬼神差使,青苗去发廊烫了头,像花一样,像只被风吹乱的波斯猫;还买了一条超短裙,在小镇上转了好几回才买回家。当浅浅的唇线蛇逶着爬上她厚厚的嘴唇时,合着嘴唇上鲜血般的口红,青苗看到了另一个自己——那个死去丈夫不久的年轻的寡妇被她抛弃在荒郊——她喜欢这样的自己。
摆在床边的台灯是从镇上灯具店买回来的,光线是白色的。卖灯的男人患有白内障,他死粘在青苗身上的眼神令她想到死鱼的眼睛。而此刻,她站在镜子前,那双白内障眼正从镜中飘荡出来,落在短裙上,唇线上。她吓得惊出一身冷汗。
小镇上的女人已经开始议青苗的爆炸头和超短裙,青苗照样去菜市场东边买豆腐,西边买青菜。
屠夫是新来的。原来的屠夫昨天夜里死了。不是他杀,死的原因很简单,中风身亡。他私约在肉铺旁卖豆腐的马棉花去镇上吃夜宵,一时贪杯,多喝了两碗水酒,吃完夜宵,他搂着马棉花在小巷深处啃嘴,多喝的两碗水酒让他尿急,他躲进一旁的茅草堆里方便时,惊动躲在草丛里的青苗——小镇太小,青苗远远就看见了他们,她不想惹事非,躲进了茅草丛——她在慌乱中碰到了他的脚踝。蛇,他以为是蛇。他杀了二十年猪,却怕所有的软体动物。一条蛇要了他的命。不是蛇咬了他,是蛇吓得他心慌,惹发中风,一头栽倒在地上,嘴角边是那滩还冒着白沫的尿液。
“买前腿还是后腿?”
新来的屠夫将砍刀尖扎进案板,案板被一层又一层血痂覆盖,成了酱黑色。健东出事那天流在地上的血,没几天,也成了这样的颜色。
“她买猪腰。”
马棉花正怀恨在心。她去扶屠夫时,看到了草丛中那双惊恐的眼睛。同事小秋早上看青苗的眼神与此刻卖豆腐的女人眼里神色是一样的。青苗那只没有提菜的手慢慢蜷缩成拳头。好事者迅速围拢了过来,有人故意吹响口哨,暗含挑衅。
青苗受不了了,连付了钱的青菜跌落在地也顾不上捡,踉跄着跑了。
受不了的还有青苗的母亲——素秋。当别人把眼睛看到的青苗向素秋描述时,素秋一向挺直的腰杆瞬间佝偻了下来。她男人是郎中,生下青苗那年,上山采草药,爬崖时,一块松动的石子让他失去重心,坠崖身亡。一晃就是几十年:田里种禾、土里种菜;上山砍菜,下河掏沙;逢人三分笑,从不议是非……连三岁小孩都没咂嘴巴说坏过她。她早饭也没有顾得上吃,赤着脚赶到小镇。看着女儿乱七八糟的头发和露出大腿的短裙,素秋感觉无数双眼睛向她投来鄙视,接着一些听不太清楚的耻笑落进耳里。小秋坐在青苗对面,不动声色地等待一场好戏。素秋看出了这小妮子的心思,她把右手用力按在左胸,待青苗带她进了宿舍,确定门关严实后,才将巴掌落在女儿脸上。
“你怎么学花一样的打扮?”素秋压着声音怒喝,“花是暗娼,你看不出来吗?”
“除了花,没有人愿意当我的朋友了。”青苗望向窗外,电线杆上趴着一双麻雀,“连鸟儿都知道要成双成对,你难道要我像你一样守寡。”
“你正儿八经找个男人嫁了,娘不拦你。”素秋不禁老泪纵流,“镇上的人都在说,花每天半夜从各种不同的小车里走出来。”
目送母亲消失在路口,对街的泡桐花落了一地。青苗上楼梯时,小秋眼珠子砸在她身上,上下滚动。“看什么看!”青苗发现自己不想再忍了。
小秋没有马上接话,悠了一会儿,才说:“花开窑子是在自家饭馆,你总不能把窑子开到办公室里吧?”
小秋的话音刚落,那声音又回来了。“驰驰”的刹车声,如同当初的声响。她画了唇线的嘴唇筛沙子般抖得厉害。
青苗不想在小秋面前掉眼泪。她仰头望向天空,一张脸飘浮在空中——血肉模糊的脸颊旁,高挺的鼻梁塌陷成了空洞,深情的眼神凝结成最后的绝望,两腮气球样肿了起来,嘴角上的淤血结成了厚厚的一层黑痂——她一时恨不能拽净自己的卷毛,恨不能扒下对面小秋的长裤,罩住自己稍一弯腰就能看见屁股尖的下身。
三
青苗的反常没有逃脱花的眼睛。花依然用她的热情大声叫响青苗。
看着迎面颤动着前胸跑来的花,青苗低头伪装成很忙的样子。一种从花身上发出来的香气——那种香气藏在她满头瀑布似的乌发里,还有那拥挤的胸脯中——扑鼻而来。湿漉漉的香气如夏日明晃晃的太阳,无遮无掩地暴露她的热情。青苗身上原来也有这样的香气。健东喜欢这样的香气。青苗身子突然一颤,一股久违的六月清泉涌动在她的胸口。可花身上的香气并不纯净,有一股刺鼻的气味。
那晚,青苗的梦里又开始飘浮那张忽远忽近的脸。街上传来老黄狗令人恐慌的惊叫,她打开窗户,就着有些昏暗的路灯,恰巧看见花从一辆小车上下来。
两天后,又是夜里,又是犬吠,青苗发现送花回来的小车不是那晚那辆。“她就是一暗娼”母亲那日的话回响在耳际。青苗终于明白那股香气为什么会裹挟污秽。像驱赶恶魔般驱赶身体里被花诱发的不安。青苗剪碎了超短裙,扎起了蓬乱的头发,把嘴唇擦得几乎脱皮,摆在桌上的化妆品全扫进了垃圾桶,又站在镜子前反复审视自已,确定自己确实没有任何被花覆盖的迹象了,才开门去上班。
花又来了,似阵风,飘浮在正下楼梯的青苗面前,那股似是而非的香气,青苗闻着恶心。她已经打定主意,索性阴着脸说:“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花的脸皮抽动了几下。
“我和你不一样!”
“你敢说你不想男人?”花在狂笑,眼神似鞭子抽在青苗身上。
青苗索性横下了心,说:“我不卖身!”
“谁卖身了!”小花尖叫着推了青苗一把。青苗没有站稳,摔倒在楼梯上。滚到楼梯口时,鼻血流了一脸。
小秋正下楼来,她装作啥也没看见的样子,一声不响地从两个女人面前走过。
“滚!”青苗甩掉花扶她的手。
“一个朋友约我去南方赚钱。今晚餐馆就不营业了,到时我炒两个菜,你过来陪我喝两口,不枉咱们姐妹一场。”
花走了。被她家小餐馆宠坏了的老黄狗似乎也听出了什么,失意地耷拉着尾巴跟在她身后。
晚饭后,青苗房里的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对面餐馆的灯,熄了一盏又一盏,最后只留下一盏了。青苗听见了花在唱曲,她从没有听过她唱曲,虽然听镇上的人说,她从前跟一个从北方过来的老人学过唱秦腔,可自打她男人死后,她再也没唱过了,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本地煤老板想听她唱曲,她砸碎桌上的酒瓶抵着他的脖颈,说,你能让我男人死而复生,我就唱给你听。自此再也没有人敢叫花唱曲。
听着花凄惨的唱腔,青苗有些害怕。她顺着曲声坐到了花的对面,发现一副拐杖正立在花的身旁,除了害怕,又多了一丝好奇。
花摇晃着身子站起来,说:“好妹妹,陪姐姐喝两杯。”花已经醉了,没有发现青苗端的是茶杯。
“你现在赚的钱不够花吗?”
“不够啊。差一大截!”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那么多钱?”
“你不懂的,我那死鬼男人,做鬼我都舍不得抛弃。”花又哼起了曲,酒瓶围着她,叮叮咣咣,倒了一地。曲声渐渐弱了,她趴在桌上,睡着了。青苗隐隐约约听到了抽泣声,仿佛从墙缝里生长出来的。
花走的那天,青苗下乡揽储去了,回来时看到小餐馆大门已经挂上了“停业装修”的字样。邮电局门口的狗尾巴草发疯了般往上蹿,她在营业厅坐下时,眼里看到的全是它们。
青苗把营业厅地板拖了四次,办公桌上的文件整理了数次。窗口没有人,街上也没人有,老黄狗耷拉着头,趴在街对面的泡桐树下。她拖着近乎僵硬的躯体,试图使自已陷入混沌的忙乱之中。可无论她将目光投至哪里,那前胸跳跃的身影,那夸张而任性的笑声,那闪闪发光的眼睛,那超短裙下扭来扭去的大腿,那副拐杖及其它莫名的东西,像幽灵般缠紧了她。
她无意中发现,那只老黄狗又开始了它的流浪生活,似乎比以前更邋遢了。而她,不由自主地,一听到摩托车启动的声音就想往外跑,可她并没有像过去那样,跑出去是想找到健东,她甚至不知道她的目的在哪,她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什么。
到了夜里,她像条被网住的鱼,怎么也找不到出口,垂死挣扎换来的只有遍体鳞伤。然而,在网的外面,有一张脸在晃荡,她看清楚了,是健东。此时的健东不再是那个血肉模糊的人了,完完全全是干净的、完整的。不仅脸是干净、完整的,身体更是干净、完整的。青苗看见健东那扇面似的胸膛里有一团火在燃烧。这是健东死后,青苗第一次看见完整的丈夫。当青苗看见健东向自已缓缓走来时,散在屋子里的劣质香水味消失了,变成了缓缓自上而下的清泉,那种久违的感觉瞬间弥漫她的全身。她看到丈夫正一点点地靠近她,他的手正一点点地伸进她的身体。于是,慢慢地摇晃,慢慢地变成了惊天动地。透亮清爽的六月清泉正自她的眼窝、嘴唇、胸脯深处、小腹下边往外流。她在眩晕中扑倒在床上,进入梦乡。
四
二顺子爬上青苗的床时,已是凌晨一点了。二顺子是住在街对面花原来的餐馆旁边的理发店的老板兼理发师。
什么时候喜欢上二顺子的,青苗不记得了。收到花寄来的信后,她知道了一个秘密——街对面的二顺子也是知情人。他没有出卖花——从此,她不再自己洗头。每次去二顺子的理发店都要二顺子帮她洗,人多的时候,她就坐在那看他洗,等前面的人洗完了,她就静静地躺在二顺子前面的躺椅上。二顺子的手比女人还软。有一次帮青苗掏耳朵,她身子都酥了——只有健东让她有过这样的感觉——她咬紧牙关没有让身子抖动。二顺子是有老婆的人,还有一双儿女。她忍耐着不去二顺子那洗头了。几日后,二顺子来柜台寄钱给他河南老家的双亲时,问她为什么不上理发店了,青苗撒谎说头上长了暗疮,过几日好了再去。
青苗再躺到二顺子面前的躺椅上时,二顺子在她头上抚动的动作更加轻柔了。她闭上眼不敢看二顺子,二顺子的店是夫妻店,平时在店里收钱的是二顺子老婆,这会她上麻将馆去了,不到做晚饭的时间不会回。除了青苗,店里没有其它人。二顺子背对着临街的窗户坐着,头越低越下,最后落在了青苗的唇上,外面的人不仔细看还以为二顺子贴近了在帮客人掏耳朵。
青苗惊了一下,心里“咚咚”乱跳,可她没有躲闪,依然紧闭双眼,直到二顺子的手落在她的胸口,她才坐起来,头发也没吹,湿漉漉地走了。
两天后,青苗又躺到了二顺子面前的躺椅上,依然紧闭双眼,任凭二顺子轻抚她的每一根发丝。掏耳朵时,二顺子趁她媳妇上外面晒毛巾的机会咬着青苗的耳朵,说:“夜里等我。”
二顺子什么时候走的,青苗不知道。她是被街对面一阵能穿透墙的咒骂声惊醒的。若是过去,青苗早就慌了,可此时,她一脸漠然,似乎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二顺子媳妇一看见青苗,立马加大声音,其词恶毒不堪。青苗脸色依旧,迎着小秋幸灾乐祸的目光坐到了她的对面。
二顺子是凌晨四点回的家,没有人看见他是从青苗房里出来的。二顺子媳妇原来怀疑花在勾搭二顺子,可花走了。镇上不正经的女人都去了沿海城市。除了青苗,不会有别人,大家都理所当然这样认为,二顺子媳妇更是这样认为。可没有证据,她不能撕烂她的脸皮、拽光她的头发,更不能攻击她的下体。她只是扯着自己破沙罐般的嗓子告诉镇上的人,他老公昨晚偷人去了。直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她才恼羞成怒地捡起一块三角形青石,对着趴在她脚边的老黄狗狠砸过去,骂:“再偷,我打折你的狗腿。”
那天晚上,青苗又梦见健东了。他从那辆瘸腿摩托车上下来。她明明看到进屋的是健东,可是搂紧她的却是二顺子。
从梦中醒来后,青苗怎么也睡不着了。她痴痴地看着漆黑的墙面,回忆那个遥远的梦,梦里有她的男人,那个叫健东的男人。他忽远忽近,飘飘荡荡,好像就在眼前,走近了,他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样的恍惚之间,青苗又看见了另一个身影。正是他,在她男人死后,在这间屋子里,引出了她心底久蓄的清泉。
青苗长叹一声,算是压抑。恰巧一场大雨冲刷掉了小镇青石板路上的黄尘,如同冲刷掉二顺子踩着青石板路走向青苗房间的蛛丝马迹,以及残存在他们彼此身上的气味。老黄狗再次出现在青苗面前时,已经瘸了一条腿。青苗想到它曾经尾随花时忠心的样子,一时有些忧伤。刚好要回乡下看母亲,青苗吆喝上老黄狗,将她带回到母亲身旁。老黄狗不再流浪了,母亲也有了伴。
青苗给二顺子写了封信,约她去五里外的大山上见面。二顺子怎么出来的,青苗不知道。
二顺子看见青苗的时候,流了眼泪,说自己这辈子能遇上青苗算是没有白活。
“我们离开这吧?”青苗像是在自言自语。
“离开这?”
二顺子的声音刚落地,青苗的心就散了。她知道二顺子只是二顺子,不是健东。
从山上回到镇上时,夜已深了。二顺子先走的,青苗迷了路,像误闯入迷魂阵,在山上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绕出来。下山时,被路旁的一根青藤绊倒在小渠,她的鞋全湿了,脱下拈在手里,赤脚行走在青石板路上,看着屋檐下长灯里跳跃的火光,它属于这,属于木楼,而她不属于这。母亲上个月和村里的护林人来福叔好上了。来福叔多年前死了妻子,如同守护那山树林般默默守护母亲几十年,如今来福叔的儿女都成家了,母亲才松口依了他。
五
天渐入冬季,小镇岔路口的清泉早已堆满了枯树枝,偶尔还发出腐烂的沤臭。
青苗在一个枯水的季节离开了小镇。村后那只乌鸦,在她走后就骤然不叫了。她去了哪里,无人得知——就像没有人知道花在信里告诉她,花的男人还活着那样——也许是去了有泉水的地方,也许永远也找不到她心中的清泉……

简媛,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湖南新邵,2005年定居长沙。2004年开始小说创作。2015年获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年度新锐作家。2016年长篇小说《摆渡》获省、市重点扶持作品。2016年9月获长沙市文艺新人奖。代表作有《空巢婚姻》(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