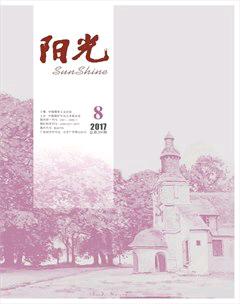河水流过的村庄
我家住在一个丁字路口,端直上去是高垣,左拐是西川,顺着两条路的方向是两条河,两条路在我家门前汇成一条路,两条河在我家门前汇成一条河,这条河绕着我所在的村庄流过,形成一弯新月,将村庄紧紧地环抱。
这条河长年不断。自我能记事起,它就一直流淌着,现在,也一直这样长年不歇不知疲倦地流淌着。
村庄里住着五十多户人,沿着山脚下一序儿排过去,排成一个长长的“一”字,将村庄拉得老长,在这个“一”字形的零零碎碎的房屋前,是一片六十亩肥沃而宽展的大平地,这是村庄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土地平整开阔,光照充足,太阳一出来,就能朗朗地照着。
村里分上院和下院,下院的人在村口的小溪里取水吃,上院的人就在这条绕村而流的大河里取水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条河流滋养着我们的村庄。
河流有五六米宽,水质非常清澈。水是从秦岭沿线大山中流出来的,没有污染,因此河水总是清洌冽的,一望见底。水里的鱼很多,有黄豆瓣、金钱鱼、黄辣丁、还有泥鳅等等。它们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与人相见惯了,鱼便不再怕人,无人的时候,它们畅游,有人的时候,它们仍畅游,反正河水是属于鱼儿的,那里便是它们快乐的家园。有时,在打水的时候,一不小心,便会将鱼同河水一起舀进桶里,舀进桶里的鱼儿见自己突然被圈住了,便四处乱窜,以求逃脫。有人无欲无求,便将它放了,有人见这是自己撞进的勺中之物,便将它带回家,养于盆中,供孩子赏玩。孩子得了鱼,便有了乐事,每日观赏,打捞,戏耍,直到鱼儿的生命奄奄一息。当然,这是一条不幸的鱼,它是为了人类的欢乐而牺牲的。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人总是处于主宰地位,其他的一切物种都处于从属地位,它们基本上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为人类所享用的,它们没有决定自己命运和生死的权力,人欲之生则生,人欲之死则死。
就拿鱼来说,鱼的命运无非两种,一种被人吃掉,一种供人赏玩。在这个村庄里,我无数次地看到过鱼被电击或被药死。
每年的夏天,都会有城里的人来到这条河中,他们要么去到西川,要么去到高垣,将成包成包的鱼塘精放到河里,药物自上游而下,迅速地冲遍全河,一会儿,河里便泛起了白花花的鱼儿,那些药晕的鱼被冲浮到水面上,顺水而下,药鱼的人便拿着塑料篮子和网兜,顺河拾鱼,一河两岸,便聚满了拾鱼的人。幼时的我们,也会参与到这浩浩荡荡的拾鱼大军中,将拾得的鱼拿回家,让母亲给我们拌上面粉煎着吃。
记得有一年,我拿着父亲编织的塑料篮子去河里拾鱼,一不小心,踩着了石头上的青苔,脚底下一滑,半篮子鱼“哗”一下倒进了水里,鱼一下被冲散,顺河而去,我费了好大心力拾的鱼又被别人分拾而去,我急得“哇哇”大哭,村里的一个大叔将他拾的鱼分了一半给我,说,这些鱼拿回去,够你妈给你煎一盘吃的,我破啼为笑,将鱼带回家。后来,母亲为感谢人家,专门请那个大叔来家吃了顿饭。
村里的人,多如母亲和大叔这般厚道。
等我慢慢的大了,我才意识到,我们吃鱼没有错,这是自有人类以来,一直在践行和传承的事,我们无法论定对错,也无法说自己会不吃,但是我们不能将那些没有长成的幼鱼也一起药死,这简直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药鱼的时候,常常是大鱼小鱼一起药,无一幸免,大的鱼可以吃,小鱼苗就这么不负责任无情地被药死了,有的还不够半寸长,简直就是小鱼婴,药一次鱼后,这样的小鱼河面上漂浮着一层,这样小的鱼没法吃,可它们的生命却这样戛然而止,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和遗憾的事。一次药鱼之后,河上到处荡漾着鱼儿弱小的尸体,在阳光的暴晒下,几天之后便开始腐烂,发出一股难闻的腥臭味,看着这些死去的小鱼,我就觉得,人为了贪吃,简直是在造孽。
但就算这样,这条河里的鱼也一直很多,年年药,年年生,年年生,年年长,河里的鱼的数量似乎并未减少。这,让我庆幸。
现在想来,最主要的是这条河的水源好,水质没有污染,适合鱼的生长,在这样纯天然的生态环境中,无须刻意为之,鱼都会自然地繁殖和生长,保持着一种生态的自然平衡。
在村庄里,生活着一群人,他们大多数跟我是族亲,有的是我的长辈,有的是我的晚辈,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亲戚关系,外村人称我们是“徐家大院”,因为在这个村庄里,以徐氏一姓为主,少数的外姓人,都是从西川和凤镇搬来的,他们来后,与徐姓一族成了一个共同体,成了世代相依休戚与共的乡亲。
村里的人都爱来河边,有的来担水,有的来洗衣服,有的来河边闲坐,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会来河边读书。因此,河边总不会寂寞,总有人影晃动,人一来,河便活了,有了一种动静相宜相得益彰的美。最热闹的是洗衣服的女人,在河边大声地喊着话,无所顾忌地说着自己的老公和孩子。村庄里是没有秘密的,谁家的事,大家都知道,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大家都胡乱地开着玩笑,胡乱地唠着,于是,河面上便泛起了浪花般的笑声。
在河流的拐弯处,有一处深潭,河流在拐弯的时候,将水也留在了那里,积成了一个很大很深的潭,这里,便成了村里人的一个天然的澡塘。白天,这里是男人的天下,晚上,这里便是女人们的去处,夏日的午后,一过十二点,太阳把河水晒暖,闲着的男人们便下了河,在河里畅快地泡个澡,天天泡,日子久了,不会游泳的也会了。受大人们的影响,那些男孩子们小小年纪都学会了游泳,一到暑假,天天就在河里泡着,逮鱼,摸泥鳅,打水闷子,把一湾河水搅得没个歇的时候。
白天,河湾是男人的世界,晚上,便成了女人的天下,一吃过晚饭,姑嫂呀,姐妹呀,娘儿俩呀,还有一些相好的小姐妹们便相约着下了河,河湾的上面是一堵高坡,对面有一大片坡地,离公路尚远,正在一个背湾处,因而女人来这里洗澡是不会走光的。但是女人多警惕,生怕被男人偷看占了便宜,一边洗还一边观望,偶有人影晃动,便大喊,不要过来啊,这里有人洗澡,走远点儿,都自觉啦。因此,多半情况下,别人都没有机会靠近河湾,女人一来到这里,这里便成了女人的天下。
村庄的日子,一年四季都是河流陪伴着度过的,村里的人一年四季忙得热火朝天,河流一年四季哗哗地流。
村庄里,哪里死了个人,哪家娶了个新媳妇,谁家生了个小娃娃,谁家夫妻昨晚打架了,河水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河水的欢喜和悲伤与村里的人息息相关。
某一年,河湾里发生了一件事,令村里的人一直心痛,也令河水一直心痛,这是在这个河湾里发生的最让人不堪回首的一件事。
那是夏天的一个中午,一群孩子午后又来到了河湾处,个个脱光了身子,赤条条地跳进了河里,七八个人在河里嬉戏着,打闹着,玩得好不欢实。可是西边方向降雨,浑浊的河水如黄河浪般自上流而下,水头翻滚,直扑村庄,孩子们正在河里,猝不及防,有孩子眼力尖,眼见水头直扑下来,便赶快喊着,水头来了,快跑啊,腿脚快的孩子跑了,大一些的孩子也跑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没有跑及,被凶猛的浪头打走,几个漩涡,再也不见人影,只见滚滚泥浆从村庄前涛涛而过。听说有孩子被卷走了,人们都从屋里蜂拥而出,一路沿河追寻过去,三队追到二队,二队追到一队,都没有追到,最后在溶洞下面的河边发现了孩子的尸体,孩子浑身被石头碰得稀烂,早已呛水而死,孩子被用席子卷回来,村人都流下了泪水。
因为孩子的丧生,好久没有人再到河湾里洗澡。
又一年的夏天来临,河水依然明朗荡漾着,那些男人还是忍不住,又下河了,男人敢下河了,女人也敢下河了,河里又热闹起来。
河道很宽,两边有好多的沙地,就近的人种上一些红薯和花生,这些作物比较适合在泥沙地种,长得饱满且好打理,挖出来,都干干净净的,省去了许多的收拾的麻烦。每次我们这些小孩子在河邊玩的时候,少不了会偷偷地扒上几个,主人看见或者知道了,也不骂人,要吃可以,不能糟踏,经主人这样一说,我们也不好意思,就算嘴馋,偷吃一回两回也就罢了,不好三番五次。
通往河边的路旁有一棵柿子树,高高大大,有几十年的树龄,我小时候,它那么高大,现在还是那么高大。
这是一棵火果柿子,熟了的柿子像火一样鲜艳,因此我们叫它“火果柿子”,火果柿子只有杏那么大,但是水分特殊多,特别甜,每到柿子熟了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就会在树下放一个竹竿,想吃柿子的人可以从树上摘几个,坐在河边慢慢地吃,我们小姐妹们在打猪草的时候,总忘不了摘些吃,每次总是几个大的姐姐去夹,我们在树下接着,她们夹够我们吃的了,我们就用挎篮装上,拿到河边,剥去皮,有滋有味地吃起来,吃完了,才又背起我们的挎篮去打猪草。
那时,要吃肉,家家都得自己养猪,因此,打猪草便成了每一家孩子必须做的事。河边的草总是长得好,长得旺盛,水灵灵的,一窝一窝,地边、河边、石头窝里,都有绿油油的肥草。这些草吸引着我们,隔几天便会走上一遭,一茬割了,一茬很快又会长起来。水草总是很茂盛,也让我们这些孩子爱极了这地方,这一河上下,好像就是一个天然的草场,不长庄稼,草却是长得奇美。在这里,我还认识了很多药材,鱼腥草、水芹菜、水薄荷,还有金银花等等,长在河边的草药,多有去火去热之功效,它们自然生,自然长,一年一茬,你采它,它长,你不采它,它照样生长。村里的乡医,多在适时的时候,将它们采一些回去,晒干,制成药,等村里人有需要的时候好用。
河边还长着另外一种药,茵陈,不知为什么,这种药特别爱长在沙地里,一到春天,满地都是。有药商专门收购这种药材,说是能治什么肝炎,有药商来收购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河边,将那些茵陈小心翼翼地采下,一棵不漏,等晾晒好后,送药商处,换了钱,买上几根皮筋或者一些学习用品,比如说本子啦,圆珠笔啦,或者几粒水果糖。手捧着这些东西,甭提多高兴了,这可都是用自己的劳动和辛苦换来的,原来,自己也是可以挣钱的,一股自豪感在心里升腾。
这条河一直没有桥,天最冷的时候,人们没法蹚水而过,便在河面上架几根圆木,用铁丝一捆,作为临时的桥,供人们过往。这种桥人走得多了,铁丝老松,铁丝一松,人走在上面,就踩不稳,老晃悠,年轻人无所谓,老人和孩子经过的时候,就有点儿让人担心,有心人见了,就再用铁丝捆住,这种桥一直能走到第二年春天,春夏交接之际,一河春水,木桥便再无踪影,它被水冲走了,冲散了,冲到哪个背湾的地方去了,人们不再理会。天气暖和了,水不寒凉,人可以蹚水而过,有桥没桥都无所谓,就算是再架上一座圆木桥,过不了三天两早上,照样会被水冲走。遇上实在不能过河的女人和老人,多会被人背着过去。
村庄的庄稼总是长势很好,绿油油的,很旺盛,绿油油的麦田,绿油油的玉米林,绿油油的大豆,绿油油的红薯和花生,还有那房前屋后绿油油的果树,有杏、有桃、有苹果、有梨,还有葡萄和木瓜。在我眼里,村庄就两个颜色,一个是生长时的扑天盖地的绿色,一个是收获时候遍地的金黄,再一个,就是春天里姹紫嫣红的各色的花儿。因此,村庄在我的眼里总是健壮丰硕的,总是生机勃勃风情万种的。
某一日,传说村里要修桥,并且是上下两座同时修,村人欢天喜地。几个月后,桥被建起,两座水泥桥,结束了河上一直无桥的历史。于是,河流有了一种庄重感和威严感,好像一个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男人。于是,从河里经过的人少了,来来往往的人都走桥面,走在平整的水泥桥上,如走在平地,脚不带水,走水泥桥,便成了一种新的习惯。
慢慢的,村里安上了自来水,各家各户相继买了洗衣机,人们不必再下河挑水,也不必再下河洗衣服,家家又安装了淋浴器,洗澡也可以在家里洗了,不用害怕被水冲走,也不用害怕被人偷窥。河便变得冷寂了,有时几天没一个人来,偶尔有来河边的,是采药之人,想来河边找一些鱼腥草之类泄火的凉性药。于是,河流一下子老了,再无往日的朝气与活力了,它独自慢慢地流着,它的高兴,没人知道,它的悲伤,也没人知道。
奇怪的是,没有人频频而至的河流,也少了那些成群结队的鱼儿,有人说环境污染造成的,有人说鱼儿们离开了这条河流,去别的地方了。现在的人都争相去城里发展,不肯待在农村,鱼儿估计也跟人一样,到城边的河里寻求热闹去了。听到这种说法,我就在想,农村现在已经污染,难道城市就没有污染吗?鱼儿突然到了城市里,能适应那儿的环境吗?我在心里嘀咕着。
河流没变,河流所流的方向也没变,河流旁边的公路也没有变,只是村庄变了,村庄不再种庄稼,村庄成了别的功能型建设区,村庄的人也已经迁徙。我想,这应该是河流变老的原因,人一悲伤就会苍老,不是说“一夜白头”吗,都是愁的。
其实现在我也是没有资格谈论村庄的,因为我也是一个离开了土地和村庄的人,只是对村庄有着经久不息无法抑制的怀念!
徐祯霞:女,笔名秦扬、徐祯燮,陕西省柞水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刊发于《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美文》《散文百家》《延河》《山东文学》《小品文选刊》《海外文摘》《百花园》《知音》《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四十余次获奖。出版散文集《烟雨中的美丽》和《生命是一朵盛开的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