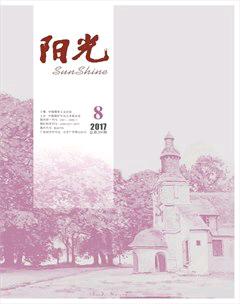看幸福放羊
宫林
出了号子,东生没有去看卧床的老娘,而是先到河湾里看羊群。
羊群的主人叫幸福,三十出头。她不是城郊人,偏远乡下嫁来的。白白胖胖,走路时脚下安弹簧,踏得地面“噔噔”作响。而且身材匀称,不像生过两个孩子。乌黑的刘海下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用村民的话说,俩大眼,双眼皮儿,一看就是个聪明人。只可惜,她连十以内的加减法都不会,喂了好几年羊,却不晓得有多少只,更不晓得卖了多少钱。别人明明知道这个,见她赶着羊群出村回村,总会有意挑她腔:“幸福呀,你放了多少只羊呀?”
她一炸羊鞭,脆响脆响的,用鞭梢指指前头散发着膻气的羊群,说就恁多,一个不少。
虽不识数,但她心里刻着呢,丢一只,就在河湾处又炸鞭又学着母羊的叫声呼喊,非得找到不行。有次,月亮上来了,男人西亮贩完狗回家,一掀锅,球光光的,便打她手机,她哭了,羊丢了一只,她在等它回来以后才能一块儿回家。西亮骑车赶过去,没到河湾,便听到了喊羊的声音。西亮看见白色的羊群齐刷刷地卧在河滩上。而幸福喊羊的声音匀穏匀穏的:“咩咩,快回来!咩咩,快回来!”有点儿像母亲喊吃饭的孩子,急又不急的。
西亮赶羊回家,叫她明天问问另外那两个放羊的,可能丢失的羊羔跑到人家羊堆里去了。她跟在西亮和羊群的后面,偶尔会炸一下鞭。村口“趴趴屋”的几位老人正在月光下聊天,问怎么才回来。西亮说,这个熊货丢了一只羊,找羊呢。幸福赶紧说,你不会打我吧?几位老人说,西亮,千万别打她了,她这群羊能给你挣好多钱哩,比你天天收狗挣的多吧。
这时几条狗开始朝西亮狂叫。只要西亮经过这儿,狗们首先朝他狂叫不止,追着他的破电动车。电动车后焊有个铁笼子,一次能装四五条狗。笼上有狗毛与狗屎,老远都能闻见腥臭味。那些老人损趣他,还是你的面子足,狗都夹道欢迎。村长再牛,开着小车,狗连瞅他都不瞅。西亮有点儿得意,下车让老人们烟,老人们说,赶紧走吧,笼子太难闻……狗一叫,羊们有点儿怕,停下来往后退,退到西亮后面,退到幸福跟前,圍着她“咩咩”乱叫,幸福叫西亮先走。西亮一走,狗就住了声。幸福炸了脆响的鞭花,羊群重新列队,整整齐齐,踩着半路的腥膻进了村……
别看挨着城,她很少去。除了偶尔给孩子送点儿钱。俩孩子上的都是私立学校,吃住在校,一周回来一趟。
他们家里,进城最多的不是西亮,是老柴。老柴是西亮的哥哥,瘫子,天天开着电动三轮进城卖些小东西。或者联合几个兄弟,在某个城乡交叉的路口拦车要钱。
东生便是栽在了老柴手里。住了一周号子。
这一架打得不值,算是彻底败北。
说出来都嫌丢人……竟然败给了瘫子老柴,而且败进了号子里,住了黑屋子。更令他不堪回首的是,自己确实连汗毛都没有挨他一下子,却让他诬告了,还说打掉了一颗牙。
都是为了可怜的幸福啊!
在号子里,他主要想两个女人,老娘与幸福。老娘是满头白发,卧床不起。而幸福则一头青丝,总是走动,没有闲着过。农忙时,她干活,比男人西亮都在行。麦收时,在毒毒的太阳下,她一个人既扬场又打落子,放下上下运动的木锨,拿起左右运动的扫帚。一会儿,一大单子的麦子,给她收拾干净了。麦糠飞出到单子外边的地上,她再将这些麦粒子用木锨摊开,抹平。最后赤脚上去,蹚出一行行的沟沟来,以便麦子能更好的通风,受光,晒得快。干这种活时,她不急不躁,不喝一口水,只是偶尔停下来,擦一擦脸上和身上的汗——她不戴胸罩,擦汗时,总爱一手撩开衣襟,另一只手伸了毛巾进去。路过的人,不光能看见她白瓷瓷的肚皮,还能看见她饱满的乳房,暗红如麦粒颜色的乳豆……别的女人会开她一句玩笑,幸福你是擦汗还是晒奶子啊?她笑笑,合合衣襟。若是男人经过,忍不住扔下烟,再捡起来,多留一会儿的目的,是看她的奶子。
就连村长都说,西亮这小子,打光棍多年,算是等着了,瞧半吊子的皮、肉、奶子,样样都是上等品。妇女主任嗔骂村长流氓的同时,也会说,可惜西亮恁多年光跟狗找交道,只记得对付狗,却忘记了对待这个上等品啊!
应该说,这个村子几百号男人,只有城里回来的东生关心她。
他们两家有点儿远亲。东生喊她表姐。虽这么称呼,却弄不清源头。就是东生娘也说不清。每当幸福过来看她时,她总是先皱鼻子。幸福身上的羊膻味太浓,刺鼻子,又热烘烘的。卧床以后的她性情古怪,总爱嘟唆人,只要见人过来,便叫他干这干那。东生觉得,娘可能是躺得太烦了,又下不了床,对活蹦乱跳的人羡慕嫉妒恨。
唯独幸福过来,娘不太使唤她。
幸福很主动,问:“姑,我给你换换褥子吧?”
“刚换过。”
幸福说:“我抱你出去晒晒太阳吧?”
“不了,阳光晒得睁不开眼。”
幸福又问:“我给你倒杯茶吧?”
“不了,喝多了尿多,都尿床褥上了。”
幸福仍问:“我帮你翻翻身吧?”
“你累不累呀?”
幸福眨眨眼说:“光放羊,又不干活儿,我累啥呀?不累。”
床上的老太太指指门外,说:“你把我院子扫扫吧,扫完了,用肥皂洗洗手脸。”幸福乖乖地出了屋,到外打扫。屋子里的羊膻味立马消失了,显出了湿湿的凉意来。她刚扫了几下,“唰唰”的声音又惊动了老太太,她又喊她,幸福,别扫了,洗洗手脸进来吧。幸福很听话,将扫帚放在墙边,到水池边洗手脸。盆架上有半块香皂,她抓起来,在手上,脸上,脖子里抹了一遍,再进屋来。老太太闻不见了羊膻味,闻见了香皂味。同时也感到屋子里有了一股暖意。她扬扬头,叫幸福给她倒杯茶,少放点儿白糖。
等儿子东生回来,她马上叫他给自己翻身。东生说,幸福能帮你翻。老太太有点儿生气地拍了一下床帮说,我叫你呢,你翅膀硬了,不理我了。东生赶紧笑着过来,说翅膀再硬都不中,你在床上,我便折了翅膀,飞不出村子了。老太太翻过了身,昂着头说,你别折了翅膀,我还指望你驮着我出去看戏呢。
幸福笑嘻嘻地接话,我驮我驮,我有劲儿。东生兄弟在城里,没干过活儿。我比他有劲儿,你想听戏时,喊我一声吧。
老太太咧咧嘴,无声地笑了笑。
那一刻,屋子里就他们三个人,倒真像是一家人。
东生说,幸福,你帮俺做饭吧,我不会蒸馒头,老娘又不喜欢吃买的馒头。幸福答应得很爽快。挽挽袖子就想进厨房。但老太太不同意,止住了她。老太太说,东生呀,你也太滑了,你不就伺候我俩月吗,怎么就雇了幸福做饭?她撵幸福回家。
黄昏的光亮浮在空空的院子里,鸟雀归了巢,院子的槐树上和屋檐上有不少鸟雀在喳喳叫着。邻家的炊烟味儿飘进了院子,飘到老太太的床前来。老太太命令东生,你不要用电锅做,要烧地锅,不然咱家的地锅可要生锈了,一生锈,就会烂的……东生苦笑一下,低声说,我恨不得马上砸烂它,没了它,就不用烧可恶的地锅了,就能名正言顺地用电锅做饭了。他最不喜欢一边烧锅一边做饭,一会儿忙锅里,一会儿忙灶窝。这老太太处处跟他过不去。
等老太太吃完了饭,他给她擦了嘴巴上的剩汁。他会笑笑说,娘呀,我觉得不是在伺候你,而是在劳改场里。老太太说,不想伺候,现在就回城去,不就几块钱的车票吗?你堂堂大老板,开着商店,不会连车票都掏不起吧……
他无言以对。
他既然干了叫娘最憎恶的事情,现在也不怕“劳改”了。老实说,他早就有与妻子离婚的想法,并不是被丽丽勾引以后才离的。还好,丽丽走了,没有同他结婚,这也叫他舒了口气,如果真结了婚,那可就证实了人家的猜测。现在,按照姊妹们的商议,轮班回来伺候老娘,每人两个月,姊妹六人,刚好一年一轮。他回来了,孩子不用担心,在寄宿学校上学。商店的事有点儿挂心,总不能关门歇业,因为房租要照交的。他实在想不起谁能帮他打理,才给丽丽打电话,叫她回来,帮两个月的忙,还好,丽丽回来了。
想起一年前,娘领着前妻,在商店门口大骂丽丽的场面,他仍有点儿心惊肉跳,觉得太亏欠了丽丽。他想过了,这两个月里,商店赚多赚少,他一概不问,全由丽丽当家作主,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在号子的七天里,偶尔还觉出一丝摆脱了老娘的解脱感。想得最多的是幸福怎么办,西亮和老柴打没打她,她还放羊不放?
毕竟是开春,草长莺飞的季节来了。先前答应过的,每年这一段要领丽丽去郊外放风筝,今年要食言了。手机也没有,不知道她打了多少电话。
在绿草如茵的河滩上,他没看见那片白色羊群时,心里忐忑不安了。他东张西望,竖起了耳朵,想听到那脆响的鞭花,仍旧没有。完了,幸福是放不成羊了!西亮和老柴这俩混蛋不让她放羊了。她不放羊,干什么呢?很有可能跟村里的同龄女人一样,翻过刚刚开修的八十米宽的外环路,到城里打工去了。打什么工?无非是保洁、洗碗刷盘子、踩机动三轮运人,或者去洗脚城里伺候客人去了。村子的土地多被征去,又是农闲季节,她们想挣钱,也只有干这些营生,当然,也有人会厉害些,到歌厅当伴唱,甚至卖肉……幸福是干不了这些的——因为她不识数,不能数钱。
河滩的青草地上空无一人,旁边有个隆隆作响的挖土机从河底往上面挖土。河边小路上有几辆三轮车正在拉土。不用问,那是村里人家盖楼房垫宅基呢——这二年谁家也不盖平房了,全是一色儿的楼房,少则两层,多则三层四层。村长甚至将村外的一片干塘填平,准备盖三幢六层家属楼,卖给那些乡下进城来的人们。这当然是非法建筑,房产证肯定是办不出来的。村长自己也说,只有一个房产证,他只能跟买方签份协议。他说,有我在,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住下去。这儿距城近,买方的孩子跨过外环路,就能进城读书了。虽一路之隔,这儿的房子比城里的便宜许多。城里一套要二十多万,村长卖的只有十来万,还是划算。
当然,也只有村长敢这么干。村里的其他人只能是盖两层三层的,将屋子租出去,而不是卖出去。村子一下子有了膨胀的感觉,村街上一天到晚人流车流不断,声音嘈杂,犹如赶集上店。老娘也因此不愿到街上来,那么多陌生的面孔,那么杂的声音,那么呛人的浮尘味,她受不了。盯着挖土机扬扬落落的“手臂”,听着它“呜呜”的叫声,看着运土三轮车的跑动,东生有点儿茫然。河滩上有不少青草,青草上有不少蝴蝶,岸边的油菜花也怒放着,散发着刺鼻的腻香。黄花好看,腻香却不好闻。难道是幸福不喜这种腻香,改到其他地方放羊去了?但这儿没有废地呀,这儿的土地多数被征用了,让政府作为行政新区了。剩下的可是让种田人无比珍爱、恨不得将一亩地翻成两亩地来多种些麦子和油菜,就连树木的间缝里都有人种了油菜。除了河滩,真的没有了放羊的草地了。庄稼都没处长了,何况草。
只好回家。
到了家门口,才突然想到,这七天里,老娘的日子怎么过的?谁照顾她呢?当然,有可能是大姐,她是乡下人,没有城里人的精明,很厚道。二姐就不行了,在城里开了几年饭馆,越来越不实在,见了人总是先哭穷,说自己赚个累,一年到头,挣不到几个散碎银子。言外之意,谁都明白,你们千万别找我借钱噢!
至于大哥,怕老婆的窝囊废,每天除了接送一双孙子上学下学,便是做饭,洗衣,干些女人干的事情。平时不经女人同意,他连回来看看老娘都不敢,一点儿男人味都没有。还总是笑呵呵的。
二哥一家倒是提前进入了小康,但他们在外省,鞭长莫及。
三姐家在省城,她在一家工厂当会计,很会算计。排班伺候老娘这事,就是她提出来的。她伺候老娘是在跨年度的腊月与正月。她倒是回来过两次,但她太忙,不能亲临床前擦屎刮尿,只好出资,让大姐代劳,她给大姐发工资。
想一想,老娘这一卧床,像收风筝一样,将姊妹们一个个收到了病榻前热和热和,也不错。
这几年他只顾忙自己的生意,很少进家。以前,娘还是很疼自己的,老疙瘩长老疙瘩短的叫他。但这一回,娘变了,对他已经不那么和霭可亲了。刚开始几天,他以为她病得心烦,在床上闷得心烦。每天上午阳光好的时候,抱她在院子里晒会儿暖儿。这个时候,娘总是闭着眼睛,倚靠在墙根儿的轮椅上,头也不动,眼皮也不眨。他呢,在这个宽敞而寂静的院子里没事干。偶尔,店里那边,丽丽会打来电话。他接电话时,以為娘在睡梦中呢,免不了跟丽丽打情骂俏。谁知娘并没有睡着。她会冷不丁地用手杖击打一下墙根儿,刺耳的响声一停,她会骂一句:“狐狸精……”
他吓了一哆嗦,娘在骂丽丽。他想解释一下,娘又闭上了眼睛,缩在阳光里。
后来,再有丽丽电话,他赶紧出门去,到娘听不到的地方去接听。
他会到村口的商店那儿看人家打麻将,听人家聊天。他会看见幸福赶羊出门,回家。也听到人家关于她的议论——
人家说幸福跟村里一个单身汉二娃子在河滩边的玉米地里睡觉。这事叫西亮知道了,晚上将她衣服扒个净光,用皮带抽她,审问她。她不怕西亮的打骂,但她怕瘫子老柴,老柴的手比西亮狠,只要拧她两次,她就招供。老柴总拧她的肚皮。
西亮问:“为啥跟那货睡?”
她说:“我可怜他。”
西亮问:“他有啥可怜的?”
她说:“他四十多了,没睡过女人。”
西亮问:“他给你钱了吗?”
她说:“我没要。”
“为啥不要,便宜那家伙?”
“我是可怜他。我不卖肉。”
…… ……
别人边议论边笑,场面轻松自在,将此作为笑谈。但东生却不如此。他心里又揪又痛的。似乎那瘫子老柴的脏手拧住了自己的心。对了,他见过老柴的手,因为推轮椅和经常用高粱梢子编条帚、经常挖菜的缘故,一层黑皮,关节如同核桃壳。那双手长年没有歇着过,像铡锭、像老虎钳子一般有力。有时,他在热闹的村口跟人开玩笑,趁人不防,一把抓住人家的肚皮,抓得对方哇哇直叫,蹦着跳着都挣不脱,直到求饶才会松手。这时肚皮上已经青一块紫一块了。
老柴跟着幸福一家过活,每天他回来,端着幸福做好的饭菜吃。按说他该感激幸福才对,不该在西亮揍她时火上浇油,应该劝劝他,为幸福讲讲情。但这货从不这样。村口的老人说,他也就敢欺负幸福那个二百五吧,换了别的媳妇,早将他赶走了。别说吃饭,连凉水都不会叫他喝一口……
东生并没去惹老柴,他只是揍了西亮。那天西亮正在收拾幸福。大冷天里,他仍然扒去她的衣服,叫她跪在地板上,审问她为啥弄丢了一只半大的公羊。这只公羊有二十斤大小。因为丽丽来河滩玩耍时,听见了她的鞭声,看见了她的羊群,便向东生提要求,大冷天,给你照顾生意不容易,你总该有所表示吧。东生抱抱她柔软的肩头,说宝贝,我为了你,家破人亡了。老娘天天给我脸子看,我小心伺候她,她还发脾气,你说吧,表示什么,我豁出去了,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丽丽指了指那片羊群,说那些羊可是吃草长大的,不是喂饲料与添加剂长大的,应该是放心肉,你能不能给我买一只来?
他一口答应。
当他领着丽丽来到幸福跟前时,幸福站起来,静静地看她几分钟,然后对东生说,表弟,丽丽多漂亮啊!丽丽惊奇了一下,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可是第一次来这儿啊,村里的人都没见过我。
“你怎么认识我?”
“我就是认识。”她说着又炸了一下鞭,河那边的两只羊往这边靠了靠。它们虽在河滩里,但总是爬上河堤,吃人家的麦苗。大冬天,麦苗当然可以吃,人家也不管,到春天麦苗返青时,人家就不让吃了。河堤上的几只羊心有不甘地回来了。东生也奇怪。丽丽没有来过村里,幸福又从不到城里,她俩根本没有见过面,她怎么认得丽丽呢?
“你们看那只红头羊怎么样?”幸福用鞭梢指指羊群说,“二娃子说了,恁多的羊中,那只红头羊最好,是变种羊,肉最好。”
东生知道那个二娃子。因为家穷,他连女人都找不上。爹娘两个病秧子拖着他。他呢,除了种地,平时跟外村的建筑队一块儿建房子。他说城里人太狡猾,很少去城里干活儿。他挣的钱几乎全都给爹娘买药了。爹死之后,娘仍在吃药打针。二娃子多年前跟人去内蒙古放过羊,吃过不少羊肉,当然明白什么样的是好羊了。他平时放了工,骑车回来,也喜欢到河滩看看羊群。那只羊鞭是他为幸福做的,还教她炸鞭花。他总说,放羊这活儿,是天下最好的活儿。人家问他,你怎么不弄几个放呀?他说长得慢,换钱慢呀,不如盖房子来钱快。如果他不太需要钱了,也会买几只羊来放。羊是好东西,喂着省事,从不生病。
那只半大的红头羊正在撒欢,用刚刚拱出来的角儿去抵旁边的一个大羊,那大羊并不反击,而是躲着它,它仍不罢休,又去抵另外的羊。周围的几只羊都不安生了,都在躲它。无疑,它成了小霸王。
“我把那羊送给你吧?”幸福笑着对丽丽说。
不等她接话茬儿,东生就大包大揽了,连连对幸福点头,又问幸福要多少钱。幸福看着他笑笑,不说价钱。丽丽用胳膊肘碰碰东生,说她的目光太纯洁了,简直像幼儿园孩子的那种。
东生马上想起来了,幸福一不识数,二呢,也不认得钱,她怎么能说出价钱呢?但他明白,她说送给丽丽一只羊,那一定要做到的。谁都知道她一根筋,还是那种似透气又不怎么透气的一根筋。
果然,她从草袋里掏出一截绳子。她一蹦下了河滩。冬天的水并未结冰,草也不怎么茂盛。幸福眨眼工夫便将绳子套在了红头羊的脖子上,那只羊自由惯了,忽然被套了脖子,给人牵着走,当然不服,又蹦又挣的,不愿跟着幸福走。实在挣不脱了,它便去抵幸福的腿。幸福放羊多年,收拾过不少这样赖痞的公羊。她并没有费多大的劲儿,便将红头羊牵到了丽丽身边。近距离一看,红头羊的头并不太红,属于那种咖啡色,只红了头,耳朵都是白的。这只羊见面前多了两个人,马上又蹦起来,一头抵在了东生的小腿上。抵得他“哎哟”一声,差点儿倒下。
幸福将它往小树上一拴,举鞭就打,不是打别的地方,东生看得清清楚楚,鞭梢旋了一个花儿,像火苗一样,钻在了它的裆里。那只羊“咩咩”大叫,仅仅三下,那只羊一下子卧在了地上,“咩咩”叫着,声声凄厉,目光也和善可怜起来了,动也不敢再动。幸福指指它,说怎不蹦了,怎不抵了,服了吧……东生马上想起人家讲的,西亮平时自己在家,是不敢朝幸福动手的。有一次他打幸福,让幸福一把抓到了裆中物,疼得直叫姑奶奶。只有瘫子回来,他有了帮手,才敢修理她。幸福能用鞭子準确无误地打中红头羊的蛋子,红头羊的蛋子不光有后腿夹着,还有尾巴护着,不好打中的。那么,她若想击打西亮的,可是要容易得多。
那只红头羊乖乖地让丽丽牵了去。东生给她钱,她不要,笑着说,咱不摸这玩意儿,咱看着跟坟前烧的阴币差不多。东生说西亮问起来,少了一只羊怎么办呢?她说这是我喂的羊,我当家,放心吧。东生只好说声表姐,我记下了你的情。如果这事西亮找你麻烦,我去解释。她又笑笑,洁白的牙齿,粉红的牙花,真的叫人想到了幼儿园。她用鞭子在空中悠了悠,说放心吧,他不敢。
这次,也确实没有什么事,西亮与瘫子像不知道似的,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但是,恰恰正是在放羊问题上,引起了摩擦,让东生进去了。
如今在机器隆隆的河滩处,东生有点儿惆怅。幸福会去哪儿?难道西亮与瘫子将羊群全部卖掉,叫她进城洗碗端盘子去了?
他吸了一根烟,也不靠向那边挖土运土的人。他看见麦苗已经返青,在风中摇曳着,发出微微的聲响,散着淡淡的气息。青色的麦苗之上,有些低飞的鸟雀,却见不到什么人。远处的河岸上,油菜花黄黄的,一簇一簇,点缀在绿色的背景里。这画面很熟悉,只是少了那群洁白的咩咩乱叫的羊,少了一个炸响羊鞭的女人。
他有点儿不好意思的进了村。蹲了七天,毕竟那是蹲号子,不是去当官,不是什么好事。见了乡亲们,有点儿湿脸,他们会怎么看待自己呢?因此,他怕村口的人。
他绕过村口,径直来到了老娘的院子里——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老娘,有点儿不好意思。离开的这几天,谁帮自己伺候脾气古怪的老娘呢?这个问题,在号子里他也想过一两次,但很快强制自己不要多想,车到山前必有路,何况老娘除了他,还有五个子女呢!
当他看见大姐在院子里洗衣服,才放了心。大姐是姊妹之中最纯朴的人,最好的替补队员。他喊声大姐。大姐抹抹额上的汗,一绺白发随汗水耷到了眉梢边。大姐笑笑,回来了,快进屋喝杯茶吧。他鼻子酸酸的。
刚进屋,娘便从床头扬起头来,虎着脸说,今上午就该出来了,为啥都黄昏了才回来,是不是拐到你那商店,看其他人去了?
他没有辩驳,老娘没说他去看“狐狸精”已经不错了。他赶紧倒杯水,递到老娘床头,说叫您老操心了,我没事。
大姐搭完了衣服,进屋来。娘指指她,叫她回家去。大姐有点儿犹豫,低声说兄弟刚回来,我再待一晚吧。娘提高声音,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叫你走就走,家里还有孙子孙女要你照顾呢。快,把柜上的牛奶搬一件,香蕉拿点儿,回家去。老疙瘩不是蹲进去七天吗,他得补上,你记住时间,不到别来接班……
老娘的口气又冷又硬,有点儿不近人情,但他没有顶撞。默默坐在茶几前喝水。然后便是点了烟,静静地吸。院里屋里一片寂静。空气比在号子里还压抑。静止的空气里游荡着浓郁的中药味儿。
晚饭时,娘床头的手机响了,是二姐的电话。他们虽然打给母亲,但她却只说了两句,叫他接听,二姐曾经到号子里看过他,送过去几只烧鸡、几条烟。电话没有什么重要内容,只是寒暄。
他喂娘吃饭时,大哥抱了孙子过来了,也是问他号子里受苦没有之类,又说瘫子那小子该揍,你做得对,村里人都向着你,说没打死他算便宜了。他想辩白,张张嘴,又停下了。看来自己真的将瘫子打伤了,这事是板上钉钉,挣不脱了。
大哥一走,他在院子里狠狠踢了一下大槐树,骂了声老柴王八蛋,老子输给了你。
老娘在屋里咳嗽了几声,他进去。娘说你拿老槐树撒什么气,有本事再跟瘫子干一场去。你小子还不服气呀?不叫你蹲号子,咱院里可就热闹了,全是他们那些人,有几十号,瞎子瘸子,把院子里屙的尿的,扫了两天还臭烘烘的。这回你逞了能,长了见识吧?这世上,什么人都不能得罪,是神都有三分雨。你可以瞧不起老柴,但你惹不起他……
正说着,幸福进来了。身上带着羊膻味儿,将中药味儿压了下去。幸福朝他笑笑,牙齿依旧那样的白。有了这股羊膻气,证明她还在放羊。她问娘吃药没有。
“你到哪儿放羊去了?”他问她。
“这回好了,到新区那儿,有一大片麦地,人家正毁麦子,开啥子广场的,用挖土机挖坑,有不少人去栽树,全是外边运来的大树。俺几个把羊赶进去,羊吃麦苗,没人管。”
“还有这等好事?”他问,“把返青的麦子毁了。”
“真的。”幸福用手指指村东方向说,“在新区前边。”
他明白是新开的行政区,离村子不远,原先城里的行政单位全都搬了过来,一家挨一家,排列有序。中间是县委县政府的综合大楼,有十六层高。但他没注意过让幸福放羊的大片麦田在哪儿。
幸福是来刷碗的。她过来,跟娘说上几句,马上到厨房里去。干完就走。
等她走后,娘叫他到床前坐下,问他:“你为啥送羊给那个……她?”
还好,又没说狐狸精。
“是幸福送她的。我给钱,她不要。”他回答。
“真是这样吗?”娘的口气很冲。
他吸了两口烟。烟雾像纱,隔在他与老娘之间,老娘的脸变得有些模糊。这样子比她凶巴巴的好一点儿。
“你知道吗?每年幸福都因为丢羊挨打。”娘的口气柔软下去。
他点点头。如果不是这样,他也进不了号子——
那天晚上,西亮与老柴又合伙扒了幸福的衣服。倒不是因为她送丽丽红头羊的事,而是因为她在春节时送给二娃子一只羊。二娃子舍不得杀了吃,而是偷偷卖掉了。这事让天天赶集的瘫子知道了,告诉了西亮。但那几天孩子们回来了,他们俩一个初中,一个小学。快快乐乐在院子里放着散炮,有时跟在妈妈左右,像保镖。
过罢“二月二”,年味儿消失了。村子里不再热闹,外出打工的外出了,上学的孩子开学了。年馍年菜基本吃完了。最后是供桌上的“枣山”——一个大花馍已经干得“嘣嘣”响,也从供桌上拿下来,用凉水浸一浸,再用锅馏一馏,在“二月二”这一天彻底吃掉它,算是给这个“年”画上了句号。这个“枣山”有讲究,之所以能摆在供桌的正中央,财神、菩萨像都摆在它的旁边,这是为了个纪念。这儿的人全是由山西枣林庄搬迁过来的。敬“枣山”就是不忘根,不忘本。“枣山”有大有小,大则有二尺宽高,小则也有一尺半宽高。不管旁边敬不敬财神、菩萨,“枣山”上面都要放钱的,是真钱,一百或五十元不等。放在“枣山”顶上,不到“二月二”吃“枣山”时不能拿下来。收了那钱,吃完“枣山”,算是过罢了年。
一过罢年,各种禁忌全都取消。整个正月里压抑的脏话脏行为也可以开闸了。
西亮与瘫子老柴一商量,那天上午,西亮不出去收狗,老柴也不赶集,等幸福去羊圈开栏赶羊时,西亮从背后冷不防抱住了她,摔倒在地。老柴扔过来一根羊绳,西亮顺利地捆上了幸福的双手,这次由于先捆了双手,幸福的上衣没法脱去。西亮只脱掉了她的裤子。等他脱她的裤衩时,被老柴拦住了。老柴说,留住那层遮羞布,省得人家再嚼舌头。西亮同意。因为他也听到了外人的议论,说你西亮打幸福,怎么也不为过分,但老柴可是大伯哥,大伯哥看弟媳的光身子,又拧弟媳的肚子,这算什么呢?
幸福不服地挣着,骂着,有本事把姑奶奶剥个净光,把姑奶奶拉到街上去。姑奶奶把羊送了人,还跟人睡了,想咋着就咋着吧,我等着这一刻呢!
春风料峭,冻得她有点儿抖,两条白腿动个不停,想冲出院门,都让西亮阻拦回来了。她用脚踢西亮,老柴拿起她的羊鞭击打她的腿。她跳着躲着,叫骂着。瘫子呀,我做好饭,你不回来就没有吃过,你太没有人情了。瘫子摇着轮椅,说一码归一码。你送羊给人,吃里扒外,还偷男人,没有妇德,就该收拾一下,给你点儿记性……
那天刚好娘叫他去叫幸福来家,为娘剪剪头发。阳光很好,娘的情绪不错,早饭后主动要求到外边晒晒太阳。
结果他摁不住怒火,给了西亮两拳,将他鼻子打流血了。当瘫子用鞭子抽他时,他好像踢了他一脚,将轮椅踢倒了……他救了幸福,却惹了事……现在想想,蹲这七天号子,也算教训了西亮兄弟。至少西亮以后不敢再怎么幸福了。他不敢,瘫子就不会帮他忙了。也值了!
这天天也清气也朗,除了隆隆的机器声有点儿讨厌,其他的什么都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娘有了好心情,让他抱自己出来,坐在院子里晒暖。干干的槐树上有几只麻雀在喳喳叫着,不时踩下一小段干死的树枝来,摔向地面,发了“啪啪”的响声。
娘看着干干的槐树,一点儿也不皱眉头,看得入神。
他在旁边,问:“要不要将麻雀赶走?”
她说:“没那个响儿,还显不出静呢。你走吧,别忘了中午回来做饭。”
他如释重负地出了家门。在村口,他停了下来,主动向那几个老人敬烟。那几位老人笑着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没有事吧?也有人说西亮兄弟光干些常人拿不出手的事,丢人都丢出几十里了。这一回,可惊动了乡里,来了几个妇女干部,由村长和妇女主任领着,问了西亮和老柴,边问边记在本子上。还让他们摁了手印。她们还送给幸福一条太空被……村民说,他们以后再不敢欺负幸福了。
东生翻过村东头的八十米大宽道,走向新区。新区的各条路都是又宽又直,上面行人也不多。他在路边走着,看着前方的那座高大威武的行政大楼。他看到,大宽道边,已经有了几处公交车站牌。站牌是黄底红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了它,这儿一下子像城市了。
行政大楼的南边有条大路,路边有不少冬青林、松林和香樟林,在阳光里散发着冷冷的清香。这些路边的绿化带有些密不透风,让人看不清路南边的情况。不过,路南已经设定为广场,没有一幢房子了。
过了宽敞的大马路,他从绿化带的一个小缝隙中钻了过去,到了南边的广场上。哇噻,真的豁然开朗。一眼望到南边的河边,全是麦地,麦地上有不少的红色挖土机,正在起起落落地挖地坑。地坑里尚未种上树。這一片天地,以前他没注意过,做广场可是太好了。三百亩地,只多不少。
他看见了麦地里的羊群——已经不是一片,而是好多片,白色的羊隐在绿色里啃麦苗,有的隐在挖出的土堆后边。形不成什么规模,仅仅成为点缀。
不用问,幸福的几十只羊就在这片广场里。
他坐在路边,点上根烟慢慢吸,目光静静洒向前方,左前方,右前方。眼前有点儿茫然。挖土机的声音盖住了人声、羊声,让他觉得这片广阔的田地上长的不是麦苗,而是隆隆作响的机器……不过,羊可以吃个够了,这些麦苗已经毁了,没人再管再问,羊可以尽情享用。当然,也只能是享用这一回。说不定一月后,这儿全栽上了树,地面也被硬化,只许人来散步,不许羊来吃草了。
他不再寻找幸福的身影了,吸完烟,朝家走去。
宫 林:本名张功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