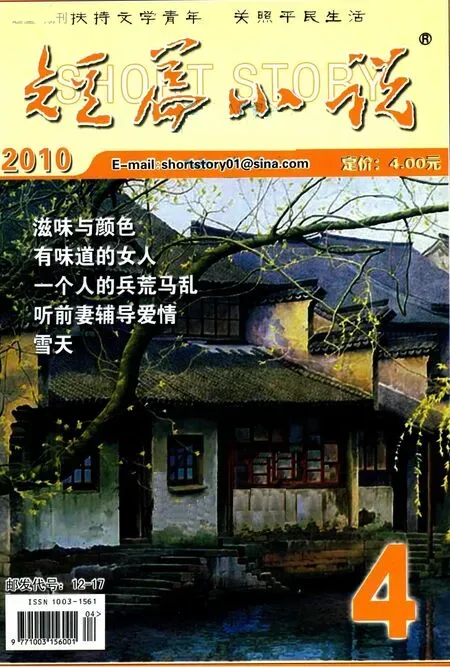两株杂草
◎北 草
两株杂草
◎北 草
刘凤侠,曾用笔名北草、柳絮、剪剪风。作品散见《思维与智慧》《上海故事》《意林》《短篇小说》《金山》《天池小小说》《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合肥日报》《太行日报》等。小说《指甲爱情》获“金麻雀”小说大赛三等奖。

1
粮库的门楣上长了两棵草,像比赛一样,腰杆笔直,分叉众多,不停地向高里长去。风一吹,就不停地晃动,颇有向谁示威的劲头。赵二出门进门看到这两棵草,心里就有些堵得慌。
门楣上怎么能长草呢?哪像人家。赵二嘟囔着,回头张望。他的眼光从不远处的两棵高大的松树,落到几米开外的塌陷的粮囤上去。犹疑了半晌,叹了口气,他终于想起当年的那把梯子随着粮库的解体早就不在了。他剜了一眼门楣上的两棵草,意识到以自己六十岁的过于僵硬的腿脚,是奈何不了那两棵高高在上的一直跟他故意作对的草的。赵二拖着微驼的背影走出门去,门楣上的草就在风里更起劲地摇摆,有几片枯叶趁机飘到了赵二的背上,赵二浑然不知。
赵二回顾自己六十岁的生命,如果说要感谢的话,那么他首要感谢的是自己的父母,是他们给了自己肉体凡胎,让他领略了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其次要感谢的是粮库。赵二的父亲是粮库职工,赵二从小就在粮库玩耍。等到父亲老了,赵二来接班,一干就是二十六年。赵二走过的最大的地方就是粮库,赵二的梦里出现最多的地方也是粮库,甚至他认为自己的血液里如今流淌的都是花生大豆打出来的油。那些黄灿灿的油把他的血管都填满了,在他的身体内四通八达。
赵二起先不在粮库住。他住在粮库附近的一个小屯子里。他每天早晨起来要站到院子的最高处向粮库的方向望两眼。有时候能望得到,那是冬天,树叶都落光了,房顶上压着一层皑皑的白雪。他的视线利剑一样穿过房屋,准确地捕捉到粮库的大粮仓。粮仓上也压着雪,像一个被谁咬掉了一半的发面馒头。赵二知道,这一场雪让粮仓塌陷得更厉害了,那仓顶有一大半没了,总得修葺一下才好呀。而大多时候赵二只是徒劳地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任凭他睁大了眼睛,将脖子努力地向高处抻着,也望不到粮库一丁点的影子。因为冬天过了,草木重又长出了叶芽,小村子被一片绿荫覆盖,把赵二的粮库隔在一汪巨大的绿海之外。
赵二的老伴向春很不满意赵二的痴傻行为,她屡次提醒赵二,粮库解散了,黄铺了,别再傻呆呆地想你的粮库了。向春每次都说“你的粮库”,这让赵二冰凉的心多少有了些慰藉。对啊,我的粮库,黄铺了也不能否认那是我的粮库。赵二的语气里明显暴露了他的得意。臭美吧,你的粮库,现在是家雀的粮库,耗子的粮库,蒿草落叶的粮库!向春这么一说,赵二的情绪就蔫耷下去,眼睛里刚闪耀起来的一簇火苗“噗”一下灭了。鳖羔子!赵二心烦意乱地骂了一声,一矮身进了屋子。向春一愣神,但马上意会到赵二不是骂她,就不管那么多,从粮仓抽出一支苞米,嘴里咕咕咕唤着,奔着乱成一锅粥的鸡圈去了。
2
2006年的春天无论怎么说都不能从赵二的生命中抹去,如今赵二想起来还愿意一遍遍地回味,那股高兴劲就好像他当初接替了他爸的工作成了小镇粮库一名正式的职工一样。怎么说呢,赵二觉得有些东西是谁的就是谁的,别人争着抢着也没用。他买了粮库的房子就是这样。粮库原来的主任说,粮库临街的房子可以卖掉一部分,粮库的职工有优先购买权。赵二一没托关系,二没使什么歪点子,他只是兴致勃勃地去主任那里报了名。半个月后,主任说,赵二,去交款吧,粮库的房子有你一套了。
赵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买到了粮库的四间大瓦房。瓦房的东窗对着粮库的五个粮仓,那里的粮食堆成了山,挂了链条的传输机日夜歌唱,不是把装满了苞米的麻袋运到粮仓里,就是把粮仓里的苞米运出来,几辆大卡车泊在院子里,整装待发。当赵二推开瓦房的东窗,他看到的就是这一幕忙碌的景象,在他的生命中像不朽的流水,弹奏着悦耳的音符,似乎从没有远去。
向春爆发了自嫁给赵二以来最大的一次脾气。她气愤地夺过了赵二的酒盅,你傻了吗?你是真傻了吗?咱们住着好端端的四间瓦房,你又去买四间瓦房,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啪”地一声,向春和赵二都听到了玻璃爆裂的声音,玻璃碴子迸溅一地,半杯酒润泽了地面。赵二张了张嘴,喉头蠕动着,做什么,你说——做什么,那是我的粮库,我怎么不——能去住。他因为太过激动话语有些不利索。向春是乡镇医院的医生,她知道赵二有高血压、高血脂,轻易不能激动,所以她的火气也只发了一半就降了下去,好吧,你去住吧,守着你的粮仓看它怎么塌陷下去。
秋天新苞米入了仓,赵二一家就搬到了粮库居住。老房子贱卖给了村子里一个同姓兄弟。赵二用了一春一夏将粮库的瓦房装修妥当,纯白的塑钢门窗,屋顶铺上了红色琉璃瓦,从外观看上去颇为气派。一间门脸对着街口,上面挂着“赵小小牙室”烫金牌匾,那是赵二儿子的名字。另三间做了住房,正门对着粮库大院。十几步开外是腰身浑圆的粮仓。
至此,赵二觉得自己的人生梦想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他守住了粮库,又可以与熟悉的粮库朝夕相伴,再做一回粮库的主人。
3
住进了粮库的赵二对房子周围做了一次大手术,在他看来这很有必要。
他先对房子南侧的乱石做了一番清理。这些乱石都是粮食加工厂房倒塌的墙壁。厂房的机器早就没有了,房顶年久失修,塌陷了一大半,夏天接雨,冬天积雪,乱石横七竖八地堆砌着。赵小小是粮库的陌生来客,他看着赵二里里外外清理乱石的身影,颇有疑问。这就是曾经的粮库?你们就在这样的厂房里粉粮食?瞎说,你爸爸的粮库气派着,这里的加工厂最忙的时候二十四小时作业,粉好的粮食不用马车,都是用卡车拉走的。赵二尽力比划着,他的脑海里反复回想着机器轰鸣的声音,那是多么美妙的乐曲。他想让儿子也听到。但是赵小小却很不耐烦地转身了,爸,我要去做牙模了。
尽管赵二努力地将自己世界里的那扇门打开,期望赵小小,这个他唯一的骨血能够花点时间走进去,像他一样能够听一听那么美妙的机器的轰鸣,但显然赵小小有自己的世界。他的世界是各种各样的牙齿。学习了三年的牙医,回到小镇做了一名梦寐以求的牙科医生。不能否认,赵小小的努力和执著,这是一个一直向着梦想奔跑的孩子。只是他的梦想与赵二的梦想不在一个点上,也永无交叉的可能。
当赵二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不再强求赵小小听他的故事。他只埋身为粮库做手术,一些大大小小的他认为很有必要的手术。他用了一个星期时间清理掉了粉粮房周围的乱石和杂草,粉粮房还残留着一堵半墙壁,半个屋顶,虽然样子丑陋,但总算耐看了一些。赵二又以无微不至的耐心将当年留作宿舍用的一排平房修理了一遍。呼扇的门扇钉上了,破碎的窗户玻璃换掉,装上新的。忙乎完这些,冬天的第一场雪就紧随而至。
是在一个黄昏,赵二隔着一米远打量着被成功做了手术的那排平房,依稀听到从遮掩不严的窗缝中飘出李天昊和肖宇的笑闹声。李天昊是粗嗓门,笑起来声音憨憨地,似乎震得窗扇都跟着晃动。赵二也忍不住笑了,他跟李天昊、肖宇在这排平房里住了五年,每逢夜晚,三个不安分的年轻人打打闹闹,也总要到后半夜才肯睡去。
赵二的眼睛有些湿润,抬手擦了擦眼睛,忽然看到一朵雪花落到了手背上,才意识到下雪了。他扬起脖颈看着天空,哦,不知何时,天地之间已经变成雪花的舞台,那洁白的小精灵一朵接一朵地盛开、舞蹈着,一朵接一朵地绣到了平房顶上、粮仓裸露的枯草上,一朵接一朵的,没完没了。
李天昊的死是赵二三年前才听说的。一场车祸。而赵二只要想起李天昊,还执著地认定他们——赵二、李天昊、肖宇仍住在粮库的平房里,他们没完没了地笑闹着,他们的夜晚跟粮库堆成山的粮食,跟小镇夜空密密麻麻的繁星相陪伴,那段日子依旧新鲜,就像昨天发生的一个样。赵二不知道肖宇去了哪里。粮库解体了,肖宇就离开了小镇,肖宇说要去外面闯一闯。而如果肖宇活着,跟赵二一样,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
我六十岁了吗?赵二至今不敢承认自己的年纪,就像赵二不敢爬上粮仓一样,这两样都是他的禁忌。
4
爬粮仓是赵二擅长的本领。
其实也不能算什么本领,粮库职工年轻一点的都要爬粮仓。赵二只不过动作能麻利一点,跟李天昊相比,他用十秒钟就爬上了粮仓,李天昊身材魁梧,动作却迟钝,爬起来就比赵二慢了好多拍。
粮库职工爬粮仓用的都是木梯子。两个扶手,二十三个横档,赵二记得清清楚楚。赵二每次爬上去,并不直接猫身进粮仓,而是愿意坐在梯子上向下张望。因为高处阳光刺眼,他总要眯着眼睛先看一会儿铺满了粮库地面的玉米,那些玉米黄灿灿的像铺上了无数张地毯,又像落了一地耀眼的金子。赵二看到李天昊和肖宇都拿着特制的锄板埋头忙碌,将没摊开的玉米一锄一锄铲下去,平整均匀了,好使每一粒种子都能接受到阳光的照射。而到了傍晚,粮仓巨大的影子在地面拉得越来越长的时候,他们又要忙着把粮食收集起来,装进麻袋里。一年的大部分日子,赵二他们就陷身在这样的重复里,晒粮食,收粮食;收粮食,晒粮食。粮仓空了,自有新的粮食运进来。至于晒好的粮食都运去了哪里,这不是赵二关心的事。总之,不是扔进锅里,就是倒进肚里,粮食嘛,命运总是唯一的。
不像赵二。赵二爬梯子的目的就不是唯一的。他除了查看粮仓里的粮食有没有被老鼠偷吃,有没有淋雨发霉,更隐晦的目的是偷看一个姑娘。这件事他跟李天昊也没提到。粮库的南边有一堵长十几米的高墙,姑娘家就住在墙外。姑娘每天傍晚会坐在自家房后打毛衣,红色的毛线经过她的手宛如有了生命,一蹦一跳地自动排队站到袖子里,站到不断加长的腰身里。赵二呆呆地看着,常常忘记了自己爬粮仓是要干活的。往往是李天昊的粗嗓门不合时宜地从粮仓底部传了过来,赵二才不情愿地挪动着身子,钻进粮仓里。
晚上,赵二就做起了红毛衣的梦。他看到姑娘翻过高墙,羞答答地把织好的红毛衣交到自己手上,还没等赵二说声谢谢,姑娘又翻过高墙,刹那间不见了。赵二醒了,他发现了自己怀里果真搂着一件衣服,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月光一看,原来是李天昊的工作服。
赵二爱爬粮仓的秘密没有隐瞒多久,就被李天昊和肖宇发现了。从此,这个梯子不得安宁。一到傍晚,不是赵二,就是李天昊,再不就是肖宇,以爬梯子查看粮食为由,接二连三地登高工作。有时候为了抢到梯子,三个人秘密躲到粮仓后面,划拳排出爬粮仓的顺序。要是哪个人在粮仓上多呆了一会儿,晚上睡觉总会遭到另两个人的联合攻击,不是掀了被子,就是扒掉裤衩。那样的夜晚疯疯闹闹,每个人的心里却都盛满了不能言说的甜蜜和芬芳。
5
三个年轻人的梦是在一个秋季的阴雨天被粉碎掉的。他们同时听到了南墙外高亢震耳的喇叭声,是喜乐。粮库老职工说,老刘家要打发大女儿了。那一整天都下着雨,赵二的心里发了霉,长了草。阴雨天粮库职工就自动休息,赵二索性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一床棉被裹紧身体,又找了两团棉花塞进耳朵。即便这样,那连绵不断的喜乐还是贼一样溜进赵二的耳朵。赵二的眼前一会儿是红毛衣,一会儿是刘家大女儿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赵二想爬上粮仓看一眼老刘家的大女儿,但很快又否定自己的想法。他绝望地告诉自己,看一眼又怎么样呢?她要结婚了,做别的男人的新娘了。
这一天李天昊和肖宇也不好过。三个人之间好像有一层窗户纸,谁都不说是为了什么闷闷不乐,但谁都知道那不言而喻的原因。有老职工去老刘家喝了喜酒,回来当着大家面说,真是女大一枝花呀,这丫头我看着长大,如今出落得整个村子数一数二的美了。这句不疼不痒的话无疑往三个年轻人的心里又投进了一颗极具杀伤力的炸弹。那天夜晚,谁都没说一句话,好似都在蒙头大睡,但是以往连成一片的鼾声直到天亮也没有在平板房内响起来。
赵二一如既往地运送粮食,摊开,晾晒,装麻袋,动作依旧麻利,只是从此以后只要谁让他爬粮仓看看粮食,他总会找这样那样的借口推脱掉。时间长了,爬粮仓这个工作自然不再落到赵二头上,反正粮库年轻人多得是,随便支使哪个年轻人都可以来做这件事。
直到粮库黄了,赵二再没有爬过粮仓。几十年间,他娶了媳妇,生了儿子,有了自己的家,但对粮库却越来越依赖。有些事情可以忘掉,比如那个姑娘。她嫁到了哪里,丈夫对她怎么样,生养了几个孩子,赵二也陆续听到一些。但也只是听听而已,因为不会怎么样。她是赵二生命中的一个插曲,一个小小的部分,她不是主流。主流是粮库院内这些粮仓,这一排撒满了他和李天昊、肖宇欢声笑语的老平房,是整夜机器轰鸣不停的粉粮房。当然还有,他们握着锄板追赶偷吃粮食的麻雀的日子。那些日子真美好,赵二像兔子一样撒欢,有时就躺在粮食堆上睡大觉,李天昊偷偷地把粮食埋到他身上,只露出赵二那张被太阳晒黑了的脸。这些事情是到死也忘不掉的,是用刀潜移默化地刻到了赵二的骨子里的。赵二就是这么觉得的。
6
对粮库院落的手术赵二自认为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虽然无法恢复原貌,但至少从旧物的残留中能依稀辨出当年的影子,这对赵二来说就很满足了。自从住进来以后,赵二是不允许粮库的一寸土地长上杂草。长了草,地面发潮,就无法晒粮食,所以他大部分时间花在清理粮库的土地上。赵二坚信粮库只能做粮库,总有一天这里还会人车繁忙,大批的粮食运送进来,传送带轰响不停,把成车的粮食重新装进修葺一新的粮仓里。然后他要郑重地在每一个粮仓上贴一个横批,上面写着他最喜欢的四个大字,五谷丰登。
赵小小的牙科生意做得不错,赵小小修牙收费低,手艺也得到小镇人的夸奖。但赵小小却不止一次对赵二说,他要去城市里做牙医,他的梦想不能止步在小镇。赵二是不同意的,就像当年向春不同意赵二买下粮库的房子一样。向春因为考虑到丈夫的身体,最终做了妥协,而赵二却坚决地以一个家长的身份通告赵小小,粮库是你爷爷的根,是你爸爸的根,我们的根也就是你的根,所以你不能离开小镇,不能离开粮库。
因为父子的意见向左,所以每天傍晚吃过饭后,你总会看到这样的情形——赵小小搬个凳子坐在临街的门外,跟附近的邻居唠着闲嗑。而赵二要么在粮库的院子里踱步,弯腰拔掉又探出地面的一棵草;要么坐在粉粮房的碎石堆上,眯着眼,好似睡着了一样,任夕阳慢慢抚摸着他苍老的皮肤。等到最后一丝余晖收尽,赵二又猛地睁开眼,打量十几步远的粮囤,看着它在地面铺下巨大的阴影,整个人一动不动,浑然暮色中的一尊雕塑。
而只有赵二自己知道,每当这个时候,鸟雀归林了,车辆也不聒噪了,他总能听见历史的回声像浪潮一样一漾一漾地拍上岸来。他听到爬上粮仓的李天昊悄声喊他,赵二,我告诉你,她又换了一身衣服,她的头发瀑布一样披在肩上,赵二,赵二,你上来看——
7
自从赵二发现了门楣上那两棵草后就坐不住了。那两棵草长了多久了?快有一人高了,可恶的草籽怎么能落到那个地方,那可是一个人的头顶啊,头顶长草意味着什么?尽管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其他邻居,但赵二这一次决定要独自做一件大事,做一把梯子,像当年一样长,一样高的梯子。只有这样的梯子才能顺顺当当地攀上门楣,拔掉那两棵不择土壤,胡乱生长的草。而且做梯子的重要性还在于,一旦以后门楣再长草呢,有了梯子,就杜绝了草患。
当赵二又一次拖着微驼的背影走出大门,就在心里坚定了这样的信念,非做一把梯子不可了。
这是赵二住进粮库的第三个年头,六十岁的赵二开始做一把梯子。他不懂木工活,做不来捶捶打打的事,但他可以准备原料。赵二的库房里堆着几根木头,四米多长,大腿粗细。只是堆放着,有些年头了,当初也不知做什么好,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赵二很喜悦,他甚至意识到这几根木头就是为一把梯子而生的,而梯子是用来拔掉生长在粮库的杂草的。由此可见,一把梯子,几根木头对粮库的重建凸显了非常重大的意义。理清了这样的思路后,赵二的心情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澎湃激昂起来。
他没有喊赵小小,一个人弓着身子搬动滚圆的木头。他只能抱住一头尽力往外拖,他低着头,双手用着蛮力,步伐交错着缓缓倒退。恍惚间,他看到自己在拖着一把梯子,那把梯子有两根横木,二十三根横档,他要把梯子拖到粮仓下面,他要爬上粮仓的高处。这一次他要闻一闻粮食的芳香,三十多年前的粮食,那香味跟今天一定是不同的吧。
向春喊丈夫吃饭,在粮库里找了一圈,最终在仓房里发现了昏迷的赵二。他呈跪卧的姿势,头部趴在一根木头上,两条长长的涎水顺着嘴角淌了下来。是在去小城的中途,医生说不必再向前开了。于是救护车又原路返回,车子从粮库的门楣下经过时,握着父亲的手的赵小小忽然吃惊地喊着,我爸爸又动了。赵小小感觉赵二的手指在活动。但经过医生验证,赵二已经去了,赵小小的发现来自于幻觉。
我爸爸搬木头做什么?赵小小嚎啕大哭起来,如果不搬木头,他就不会猝死,不会丢下我们。赵小小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赵二的怪异行为。父子俩最终没能在思想上达成和解。
赵二的离世促成了赵小小离开小镇的念头,向春则无条件支持儿子。粮库临街的房子因为地段好,很快卖掉了。赵小小走得很决绝,再没有什么能动摇他离开小镇的决心。只是在临走时的那天上午,他无意间朝粮库的门楣望了望,他看到了两株草在风里疯狂地摇摆。他忽然记起他的父亲曾不止一次呆呆地站在门侧,朝门楣上张望。
父亲看什么呢?不就是两株越长越高的杂草吗?有什么好看的。不能理解他。这是赵小小离开小镇时说的最后一番话。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