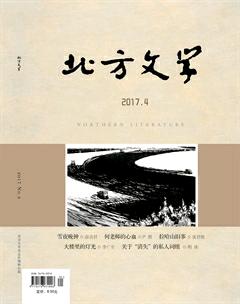与黄鼠狼为邻
王瑛
妈,妈。我三步两步蹿进厨房。
王大娘家的鸡全被咬死了,扔得满院子都是,王大爷正骂黄鼠狼呢。
早晚的事。妈一点也不惊讶,仍然往■■响的锅里贴玉米面大饼子。
我得看看咱家的鸡。我往外跑。
咱家的鸡没事。脑后传来妈的话。
我把鸡窝门打开,一只两只……公鸡母鸡精神抖擞地钻出来抖翅膀、撒欢,八只鸡一个没少。我心里高兴,把手背到后面做鸡状,撵得鸡满院子飞。
王大娘与我家只隔一米宽的小胡同,两个人迎面走来必须得侧身,还有一个排水沟,走的人非常少。王大爷个子不高,不苟言笑。王大娘个子高,绷着脸有点凶。她家可干净了,邻居的孩子们走东家串西家却很少去她家。她家的姐姐叫可心,一笑露出一颗小虎牙,白白的国字脸,细细的眉眼,又高又瘦,可耐看呢。我天天都能听到她一面剁鸡食,一面唱歌儿。
忽然有几天没有她的动静了,野菜腐烂的味儿从她家院子飘过来,鸡也饿得咕咕叫。后院的胡大娘踮着小脚来借鞋样儿,我去炕琴的簸箩里找,她跟妈说着闲话。
原来可心姐是要来的,王大爷王大妈不生育,求人从外地抱来的,她亲哥哥来找她了。
可心姐肯定不能跟她哥走,她长得多像王大爷呀!
大人说话小孩少插嘴。妈斥责我。
生的没有养的亲。胡大娘嘟囔了一句,■巴■巴走了。
果然,第二天可心姐又剁起鸡食来,只是她的歌声里有了一丝心事。她家的墙上多了一张她和哥哥的照片,头挨头很亲密。
一天早晨,我在院子里压水,听见王大爷骂:
该死的黄鼠狼,让你咬死我家的鸡,我剥了你的皮,吃你的肉。
一会儿,他家的障子上挂着一张黄毛的皮,血淋淋的好吓人!我从他家门口走,紧贴着他家的障子根儿,腥臊味儿吸引了很多人来看。
前几天他家半夜鸡叫,王大爷打着手电筒起来一看,有两只鸡被咬死了。他便在鸡窝门外下了老鼠夹子,夹住一只黄鼠狼。
鄰居们议论纷纷,说绝户办事就是绝。妈说黄鼠狼是有灵性的,不会善罢甘休的。
王大爷家的鸡没了,可心姐的歌也听不见了,怅怅的我在院子里没精打采地锯木头。木头垛上面的木头都是粗粗的,弟弟跑出去玩了,我一个人抱不动。我从底下挑细的往外拽,刚拽到一半儿,嗖!一只黄黄的黑嘴巴蹿出来,眨眼不见了。
妈呀!我扔下木头跑进屋。
我看见黄鼠狼了,就在木头垛下。
妈赶紧跑出来,把露半截的木头拽出来,走到木头垛前踹几脚,一根木头掉下去堵住了空儿。
以后从上面拿,不要从底下抽。那是它的家,它看中咱家把家安在这,不是坏事,不要嚷嚷,不要打扰它。
我记住了妈的话,再也不上木头垛上蹦跳了,也不让弟弟妹妹、邻居家的孩子上去踩。每次锯木头都是轻轻地拿,怕惊扰它。
暑假到了,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妹妹,邀着表妹去土砬子老舅家。老舅一个人住着两间草房,房前的一大片果树林是我们的最爱。沙果、苹果、李子缀满枝头。午饭后,我们钻进果林,边吃边玩儿,边玩儿边摘。
大姐,你看,大黄猫!小妹指着障子。
这只猫有点怪,头上顶着牛粪玩儿。表妹嘻嘻着。
这是黄鼠狼,装人呢!老舅捡起一块土坷垃扔了过去。站在障子上头顶牛粪的黄鼠狼一下子被砸了下去。我心一紧,赶紧跑过去,牛粪摔得粉碎,不见黄鼠狼的踪影。
还好,没打死。我心里轻松着。
晚上,老舅去生产队下象棋,我们插上门躺在炕上讲故事。突然,门被谁剧烈地撞着。我吓得赶紧闭了灯。没声了,一会儿又响起来,房子像是要被推倒了。我一边搂一个,大气不敢喘。好不容易盼回来了老舅,我们湿淋淋地从被窝里出来。老舅听完了我们吱吱喳喳的叙说,去灶坑里撮了一锹灰撒到门口。
睡吧!没事了。老舅刚躺下,门又被撞起来。老舅下地推开门,什么也没有。回来刚躺下,又撞门。开门看,还是没看见任何东西。反反复复一直折腾到天亮。没有动静了,我们也惊魂未定地睡着了。
老舅起来我们也跟着出去,门口的灶灰上都是爪子印。昨晚不知有多少只黄鼠狼在撞门,仿佛一只大象,房子马上就要撞倒了。
草草吃过早饭,我们逃之夭夭。妈看着妹妹抱着大面袋子底下的一捧沙果,听着我战战兢兢的讲述。妈说老舅“虎”。她听老姨说,老舅家隔壁的艳芬姑姑家,冬天包的冻饺子放在仓房的水缸上,傍晚放进去,早晨去收,上面一层细沙子。仓房是泥坯墙油毡纸盖,不知沙子从哪来的。艳芬的爸就是鸡被叼走下鼠夹,夹死了四五只黄鼠狼全挂在障子上,可■人了。
我家要搬走了。这片家属房拆迁建休闲广场。家里收拾东西的那天傍晚,我看见大大小小十几只黄鼠狼从木头垛底下钻出来向西去了,黄黄的一片融入了夕阳。院子里的鸡、鸭、兔子、猪、狗刹那间安静下来,目送相安无事的邻居。屋檐下的燕子也探头探脑的,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选自《白桦林》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