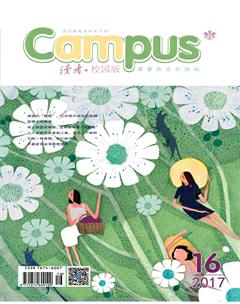在清晨,早餐店
吴涵彧
看梁实秋的《雅舍谈吃》,里头有六必居的酱菜、正阳楼香飘万里的烤羊肉,还有某某学者家中祖传的秘制狮子头——又香又糯,衬了嫩绿的葱花。又看汪曾祺的《食事》,更加亲民些,少见什么斋什么阁的,多是些昆明街边的小茶馆。但我总是很好奇:他们的早餐吃什么?
我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爸妈起床晚了,边趿着拖鞋在卫生间和卧室间奔走,边冒着一腮帮的泡沫咕咕哝哝地说:“今天没空做早饭了,喏,10块钱,自己出去吃吧!”我拼命掩饰喜色,只等他们重重关门前的最后一句“记得带钥匙”。这种隐秘的快乐是不能给大人看见的,他们一看到你的笑容,仿佛就看到一整个藏着小心思的大阴谋,接着便毫无理由地残忍地剥夺它。他们自己鲜有纯粹而无逻辑的快乐,也一并不信孩子有,这是什么道理?
礼拜天的早晨,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楼下,每一棵树都绿得闪闪发光,每一粒尘埃都在舞蹈,叶子在空中的弧度像是真的要飞起来。我站在一处树荫下,抬头看在树影间变幻的阳光,心里涌起一波又一波的情绪。到现在,我才在赫伯特笔下的托斯卡纳那里找到答案,他说:阳光下没有死亡,也没有终点。
小时候的快乐是我心里唯一配得上“物美价廉”这个词的东西,那么轻而易举,却比成为大人后的任何一次快乐都纯粹、热烈。一个太阳不期而至的阴天、自5岁那年就消失却再度出现的玻璃球、卫生评分为C的小店里热腾腾的早饭,都写着大大的“快乐”二字,还加了下划线。现在我依然很年轻,甚至是同龄人中趋向幼稚的一类,却忽然觉得快乐变得奢侈了,像南方的雪,想看一场,要心心念念好多天,且许多时候仍是一场虚妄。
我爱跑到外头吃早餐,却又不爱走远,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光顾小区门口的小店。那是我眼中的“家族企业”:一对双胞胎姐妹负责煮汤粉;瘦得像根芦苇秆的妹夫炒粉;姐夫不上班的时候常来擦桌子收盘子——圆柱一样的身体在桌子间灵活地走动着。过年的时候,一家人会包一辆小金杯车,带80岁的母亲出去玩。
以上,当然不可能是老板娘边用漏勺晃晃悠悠烫着粉,边絮絮叨叨同一个10岁的小女孩扯的家常。这是去早餐店最奇妙的感受之一,每一碗粉都像一块拼图碎片,经年累月,不需要语言,只要一个眼神,就完完整整地把另一个人的生活拼凑完全,呈现在面前。我同她們的交流仅限于“来一碗……老板,付钱”,却暗暗触摸着另一个家庭、另一种生活的脉络。譬如,常去的矮个儿阿姨的小店,以前会开到午夜,最近却常提前打烊,因为要去接儿子下晚自习;还有校门口的抄手店,里头的阿姨总叫我给她初二的女儿讲讲学习方法,而且她一定会免了我吃年糕的钱。
我还喜欢到熟悉的早餐店时,老板提前帮喊出的“多香菜,不要虾米,少辣,对吧”;也喜欢家有高三生的阿姨的低声关照“先帮那个高二的小姑娘上粉,人家功课很紧张的”;有时也爱去新开张的早餐店,桌子清爽得可以摊开写作业,老板娘总是含着初来乍到的羞涩,迟疑道:“味道还好吗?”
身为一个味觉迟钝者,我对早餐口感的要求向来低得离谱,只是贪恋那个过程而已。在礼拜天明媚异常的阳光下,大步地向外面的世界走,近乎新奇地探索他人的生活,拼凑上一块新的图像。在一阵默契后,胃被缓慢而坚定地占领,于是满足地回家,等待着全新美好的一天的画幅,在眼前徐徐展开。
如今,偏僻的小区逐渐热闹起来,附近开了一家全国连锁的早餐店。我也去了一次,取号,排队,点餐,付钱,吃完。柜台后的收银员就是收银员——不是为小孩忙得焦头烂额的妈妈,也不是奉养着耄耋老母的女儿。她们兢兢业业,从不闲聊,即使非要说话时,也是轻声细语、点到为止。洗碗、擦桌子的大妈往往动作麻利、隐于后厨,嘴巴像是缝了线。煮粉的阿姨们在厚厚的玻璃窗后,戴白色口罩,麻利而专注地将一碗碗粉、面递出,始终敛眉垂眼。她们明明很有效率,分工明确,我却不甚习惯。于是,第一次变成了最后一次,我的脚步再也不曾在那里停驻。
大抵还没有跟上这个时代高速发展的步伐,不适应井然有序的程序,我慢一步,踯躅在烟火气萦绕的小径上。这里有些泥泞,却也有着可爱的热闹。
在清晨,我依旧去熟悉的那几家早餐店,头顶是阳光,捧在手中的除了晃动的钥匙,还有满心的欢喜。(指导老师:吴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