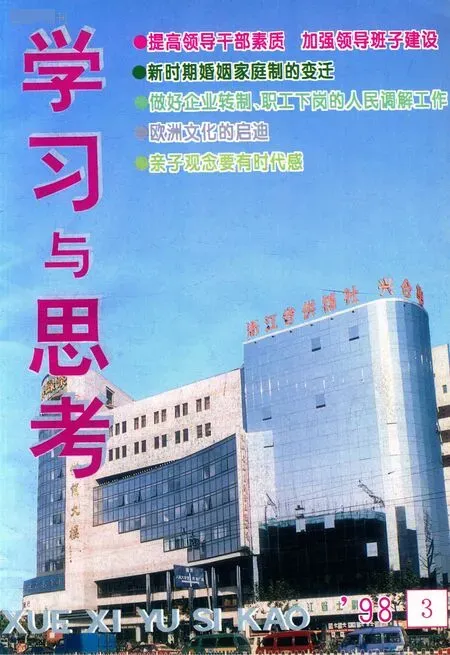论马克思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白 冬 冬
论马克思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白 冬 冬
马克思的理论包罗万象,法治思想是其理论体系一个重要的侧面。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社会契约论成为西方法治思想基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继承与批判自古希腊以降的自然法学派法律二元论的基础上,吸收了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部分,超越了康德的抽象理性与抽象的人的理论范畴,把现实的人作为法治的主体,提出了实践而非康德的纯粹理想抑或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运动是达致人类法治社会理想图景的不二选择。
马克思 法治思想 自然法学 康德 黑格尔
作者白冬冬,男,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54)。
马克思的法治思想,是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但其法治思想并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社会契约论成为西方政治和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德国古典哲学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最高峰,这都对马克思的法治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围绕人的实践本质批判继承了古典自然法学派法律二元论的理论传统,吸收了康德以人的权利和自由为核心的理性法治观,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学思想及其方法论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实现了法治思想的伟大变革。
一、古典自然法学派: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法律的理论武器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学思想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欧鲁菲米·太渥教授把马克思的法律观念称为法律自然主义。不过,马克思的法律观念不同于古典自然法学派以抽象的自然法则或者理性作为自然法的根本特征,也不认为自然法是一成不变,普遍适用于一切人和一切时间,毋宁是“将实在法的本质和正当性建立在生产方式核心的深层结构之中,而且这种以深层结构来判断实在法的适当性”①[美]欧鲁菲米·太渥:《法律自然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杨静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马克思对古希腊文化赞叹道:“希腊和罗马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极高‘历史文明’的国家。”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古典自然法学派实在法与自然法二元对立的思想也起源于古希腊哲学。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自然理性的概念,并认为宇宙的进程也是由规律所支配,“事物的这一秩序不是任何神或人所创造的,它过去一直是、现在是、将来也永久是永生之火,按照定则而燃烧,又按照定则而熄灭”②[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页。。普罗泰戈拉将经验的人作为评价万物的尺度,向价值相对主义迈进。伊壁鸠鲁则更加激进,成为彻底的怀疑论者,否认自然界存在公正。希比亚认为,事物的本性是真正的自然法,与错误的、人造的世俗法律是对立的。晚年柏拉图提出了“法治”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应该服从那引起具有永久性质的东西,它就是理性的命令,我们称之为法律。”③[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页。柏拉图虽然不信任法律,因为法律无法精准把握对每一个人来说最公正的东西,无力为每一个人生产至善。但是他从未否认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立,也从未放弃对正义的探讨。只是他把对立放置于在他所谓的真实存在且永久不变的法理念论中,把正义问题转为对国家的考察,在这一点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黑格尔的国家学说。
亚里士多德是自然法学派的真正鼻祖,也是法治理论的真正开创者。他把柏拉图的“理念”和自然概念联系起来,首次提出了自然法和实在法的概念:“城邦的法分为自然的和法律的(实证的)。自然的是这样一种法,它到处有着相同的有效性,不取决于对人来说是好还是坏。法律的则指,其内容远处是偶然的,但一旦由制定法律所确认,便有着确定的内容。”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与其自然法理论密切关联的是他提出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治论题。亚里士多德完成了政治学从哲学中的分离,他关于法律和政治的洞见至今依然闪耀着光辉,其法治思想已经超越其所在的时代,深刻影响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们。
(二)近代的自然法学思想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古罗马的西塞罗都坚持着这种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立。中世纪的欧洲是神学的世界,但是经院哲学家们依然没有放弃这种法律二元论的主张,而是将神的意志添置于其中。阿奎那提出的永恒法、神法、自然法、人法的“四分法”,是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近代以后,欧洲经历了从神权到人权的巨大转变,自然法学不像古代那样依附于自然哲学生存,也不再从“上帝的启示”去阐释自然法,而是从人的本质理性出发,探讨一种人文主义的自然法,并形成全新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滥觞于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格劳秀斯为自然法的存在提供了先天的和后天的两种证明,扩大了自然法的范围,推导出了自然法的准则,使自然法理论更加系统。更为难得的是,格劳秀斯突破了中世纪以来神学的桎梏,指明了自然法可以独立于神学而存在,这一突破使自然法具有了世俗化的可能。稍晚于格劳秀斯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否定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人天生具有社会性的政治性的看法,也不认为现实中存在所谓的自然状态。霍布斯的理论贡献在于彻底摆脱了神学的影响,以功利主义原则将自然法建立在世俗的人的理性之上,对和平和秩序的强调也是他不同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特色。洛克自然法思想也是以自然状态作为自然法理论的逻辑起点,不过与霍布斯不同,洛克意义上的自然状态常常给人们这样的印象,人们自由平等,和睦生活,人们按照理性生活在一起,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这些天赋的自然权利。但是这种自然状态难以持续,因为任何人都是自己事情的法官,都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利,缺少一个约束性的规则因而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因之人们让渡出部分权利给社会,通过社会契约协议建立政府,从而进入政治社会。洛克明确提出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法治思想,即权力必须分立、国家必须以法律来统治,已颁布的法律必须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洛克的思想不但深刻影响着英国的政治实践,就连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制定的宪法都吸收了洛克的思想,可谓影响深远。
(三)卢梭的影响
古典自然法学派中对马克思影响最深的是近代古典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卢梭,并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卢梭第一个对洛克和霍布斯开创的个人主义政治哲学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只有每个人通过社会契约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托付给集体,以集体的力量保护每一个人,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状态。社会契约塑造了国家这一具有意志能力的人格,它让参加集体的每个人实现意欲的东西,就必须把所有人的特殊意志变成一个统一的普遍意志,这就是“公意”,法律本身就是“公意”的产物。个人只有参加社会共同体之后才能成为“公民”,马克思早在1843年写作《论犹太人问题》时就接受了卢梭的“公民”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终结了发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其次,卢梭人民主权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的法治思想。卢梭通过社会契约将原子化的个人变成公民,将国家的合法性从神、君主和贵族手中夺取过来放置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赋予了政治社会道德性。这种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主权成了一切权力的来源。最后,马克思继承并超越了卢梭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卢梭发现了人类不平等起源于私有财产,并且这种不平等根植于私产的取得过程中,富人为了保护私产建立社会契约、制定法律,给这种不平等披上合法性的外衣。这意味着贫困并非不可改变,也并非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与政治法律密切相关,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就是贫困的帮凶和守护者。马克思在研究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问题时也深刻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这一批判不仅揭露了基于个人自利和资本积累原则的现代财产关系的不义性,而且为构想未来全新社会共同体昭示了方向。
二、康德的理性法治:马克思的理想法治图景
相对黑格尔,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学界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实则,从马克思著作中时而插入的几笔可以看出,他对康德哲学同对黑格尔哲学一样熟悉。康德以其三大批判为基石创建的批判哲学体系,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实现了欧洲乃至整个人类哲学史上的一次巨大转变。晚年的康德突破了三大批判关注的知、行、意的理性哲学范畴,把目光移向了以人的权利与自由如何可能为主干的政治哲学的范畴之中。恩格斯曾赞誉康德哲学掀起了德国哲学革命的新篇章。
(一)自由:康德法治思想的逻辑起点
在经验论与唯理论处于绝境而无法自救之时,康德开始了对形而上学的反思与批判。康德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张扬人的主体性,回答人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之后,如何从因果必然性的束缚下解放的深刻问题。康德指出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唯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此即自由性。第二种则认为 “没有什么自由,世界上一切都只是按照自然律发生的”。①[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按照康德对于“二律背反”的解释,这两种观点是没有绝对正确的,只能说是两种观点都有道理。由此就形成了康德哲学著名的二元论:一面是可知的自然因果世界,而另一面则是不可知的自由世界。而康德道德哲学名著《实践理性批判》即依此展开。康德认为真正的自由必须能够加以普遍化,此即其黄金命令,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立法原则并指导行动。
但先验自由与具体的个人利益的实现依然相去甚远,因此从实践上证成自由的实在性变成了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意志的自由是自由的当然要求,只有实现了意志的自由,才能算是真正的自由,因而为个人理性所掌握的意志自由便构成了自由的实践基础。理性在实践中所确立的法则不仅能够指导认识,而且可以引导行动。因为理性本身是自由的,所以我们的行为也是自由的。如果理性受到某种外力的限制,那么他所确立的原则就不足以成为我们行动的根据而从根本上丧失了自由,因而这些原则本身与自由发生矛盾便丧失了合法性。由此康德法治思想的理论核心——自由便得以证明。但是,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的满足不为理性法则所决定的低级生理需求,相反欲求得自由则需要彻底地摆脱原始欲望的诱惑而遵守道德法则。康德指出,自由“所需要的只是理性,以便责成意志,而不是哄骗意志去实施这些行为”②[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李秋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康德认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权利是法学家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如果法学家们的回答仅仅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这样就不能解释法律是否正义,所以这个任务必须要由哲学家来完成。康德认为权利“可以理解为全部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③[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30-31页。。这个基于先验理性确立的自由意志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的权利,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它首先明确了自由并不是意志本身而是“行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停留在先验理性的层面上,只有在有意识的活动中人的自由才能够得以体现。即使有了行为也未必形成权利,如果那种行为缺乏意志的自由。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特别强调自由分为三种:第一种即所谓“主观的……个体执意”,即我们常说的“任性的自由”④[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这种自由即对应前述缺乏意志的自由。它虽然是客观存在,甚至是司空见惯的。但我们却不能来否认意志自由的原则。因为“承认经验的命题是一回事,而把这个命题作为理解的原则,并把它作为普遍识别自由意志(有别于任意专断的行动)的标志,又是另外一回事”⑤[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30-31页。。康德还进一步提出两种更为高级的自由,即“客观的、按照原则的”自由以及“既是先天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自由”。在康德看来“任性的自由”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自由必须把客观规范扬弃(借用一个黑格尔的术语)到自身内,最后成为一种包容主观的客观自由,即所谓“既是先天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自由”⑥[德]康德:《历史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其次,权利是基于道德主体的责任而获得的在普遍争议原则支配之下的法律上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在普遍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使自己的意志同他人的意志相协调而获得的。康德认为,在这里他只是用这样的公设来界定权利的概念,并没有其他的意图。把这条原则作为这样的公设,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理解其中的内涵。康德认为,如果我的行为并不妨害他人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损于我的自由的行为都不构成权利。他进一步说明,这种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仅仅是对外在的行为的要求,而不考虑内在的动机,后者属于伦理学调整的对象,是义务的科学。对于侵害自由的行为,我们是可以予以制止的。因为行使的妨害别人自由的行为不构成权利,在法理上是错误的,对错误行为的阻止是为了保护权利的行使。因而在实质上与权利的本质诉求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的义务对于法律义务的优先性,相反权利对于道德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法律的义务天然地具有道德义务的本质属性,它不但可以像道德义务那样通过权利与义务相互性维持社会的秩序状态,而且在指导一般人的行为方面具有道德义务无法比拟的明确性。
(二)纯粹理性:康德法治思想的先天保障
纯粹理性是自由的唯一保障。按照康德的说法,权利的原则是“哲学上的并且是有系统的知识”,因此不可能是经验的,亦即不可能从经验中抽象出来,它只能诉诸于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可以视为原则的能力,就此而论,它是实践原则的渊源。因此,可以把纯粹理性看成是一种制定法规的能力”①[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13页。。理性是天然的禀赋,可以正确地引导我们的认识与行动,引导我们认识权利的最高法则。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康德要求扬弃那种纯粹主观的“任性自由”而达到某种兼具主客观的自由。而这种过渡其实就要靠理性来完成,此即康德所谓“实践理性”。晚年的康德一再强调他的法治理论属于纯粹理性的范畴,这种先验的理性构成了法治的前提,国家与法皆由理性来决定。
那么经验是否具有相同或者是类似的功能呢?康德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他看来,人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人是理性的存在,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另一方面人也是自然的存在,是感性世界的成员,服从自然法则,因而极其可能受到基于动物本能冲动而产生的影响。他把仅仅由感官、刺激和经验所决定的行为称为“兽性的选择”,这种选择与没有智识的动物界相通,是不能够达到认知权利的最高法则的要求的,然而却会成为法治的原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纯粹理性是最高权利法则的全部,也不是说纯粹理性可以离开实际的工作而独立存在,即使可能,这种存在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纯粹理性既“缺乏构建法规的质料”,又“并非必然地与客观和普遍的原因相一致”,②[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13页。但这并不能作为实际工作与纯粹理性背离的借口。实际工作不但必须遵守由纯粹理性推演出来的权利的最高法则,而且有义务以之为指导建构出不可改变的永恒的辅助原则体系,使之能够服务于实际工作,完成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三)实践理性:康德法治思想的实施通途
康德的法哲学如果仅仅停留在思辨理性与自然状态的层面上,那么他为之不懈努力的实现人在经验世界中自由的终极目标将无从实现,历史也会裹足不前。因为基于人的自然天性不可能实现完全纯粹的道德目标而将自由从思维转化为经验实在。服从自然法则的人类在诸多诱惑面前显得如此软弱和无理智,从而诱发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解决已经远非内在约束所能规制,如果没有一种外在的力量来裁判和遏制这种非理性的冲突,人类的自由将无从谈起。这个时候人类的理性便发出绝对的道德定言命令,要求自然状态的人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进入社会状态以实现自身的自由。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眼中的人文世界深受卢梭的影响,在国家起源上实际上吸收了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
尽管两人在国家的存在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是康德的思想显然更富洞见,康德将世界区分为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必然性不同,人文世界中的个人生而自由,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卢梭对人类作恶、堕落和腐化忧心忡忡,声言只有一群天使般的人民才可以制定完美的法律。康德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却更加深刻,他认为如果人文世界中的个人只能为善,那么一切政治法律的规范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相反,正是这种可以作恶的自由,成为人文世界中的思想元点,也是人类历史中不可获取的根本性东西。作为欲求的恶是个体性与主观性的存在,两者共同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古典自然法学家的“自然状态”理论。康德认为,一个违背道德绝对命令的“坏人”能否成为一个好公民并非一个道德命题,而是一个宪制问题。“好的宪制,不能指望出自道德性,反倒是可以指望,一个民族在好的宪制下,能有好的道德状况。”①[德]康德:《历史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6页。因此,他认为的最高目标便是建立法治社会,脱离粗野自然状态进入法律秩序下的文明状态,让“恶”向善充分发展。
三、辩证法治——黑格尔对马克思法治思想的影响
(一)辩证法:继承与超越
黑格尔对马克思法治思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根本性的,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8页。。即使在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建立了自己成熟的理论体系之后,马克思依然毫不讳言:“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海德格尔说:“没有黑格尔,马克思不可能改变世界。”④[法] 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毋庸讳言,以马克思法治思想为主题的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黑格尔的学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作为研究方法之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直接渊薮。黑格尔从思想开始,进而自然,最后结束于精神。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从自然到思想。此外,黑格尔发扬近代以来的自由学说,阐释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都认为自由是克服一种受限制和束缚的社会制度,但是黑格尔的自由是在理性分析中实现的,马克思的自由只有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变革才能实现,是现实的具体自由。
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为马克思法治思想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将理性与现实复归同一,因为黑格尔所言的概念首先是被思想所把握的事物的存在的方式,而不仅是思维的存在方式。“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本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⑤[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0页。辩证运动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思想运动,而是事物本身的运动方式。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本质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是马克思的法治思想乃至整个哲学的主要理论特色,无疑也是源自黑格尔。
黑格尔的辩证法充满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让马克思感到并不满意。“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的批判,也是对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的扬弃。
(二)辩证自由与实践自由
黑格尔的自由观对马克思的影响,在于自由的实现途径——克服对受限制和束缚的状态。在黑格尔的理论中,自由的发展无疑也是辩证发展的过程,自由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任性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受限制,是“绝对抽象或普遍性的那无界限的无限性”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16、17、10页。。第二个层次是限制,即“通过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特殊的东西,自我进入一般的定在。这就是自我有限性和特殊化的绝对环节”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16、17、10页。。他把限制作为自由的一部分,是对任性自由的一种扬弃,也是自由主体性的表达,在这种表达中赋予自由以实在的内容。第三个层次是意志,它是“两个环节的统一,是经过自身反思而返回普遍性的特殊性——即单一性。这是自我的自我规定”④[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16、17、10页。。三个层次是循环的辩证运动,后一个层次对前一个层次的扬弃推进了自由的发展,是一个否定自己又回到自身的过程。黑格尔的自由观是对欧洲自由主义传统的静止的自由观的深刻批判,因为在他看来以社会契约为理论基石的传统自由主义伪造了个人、国家的本质,也伪造了自由的本质。由此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探讨了自由和法的关系问题。黑格尔说:“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⑤[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16、17、10页。在黑格尔法哲学包括的抽象的法、道德和伦理三个环节当中都包含特种的法或权利,都是不同形式上和阶段上是体现的自由:抽象法的阶段是抽象的形式自由,在道德阶段是主观的自由,在伦理阶段意志自由得到充分的实现,但是这种伦理生活只有在“国家”才能最终实现。
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自由的形式,但是在自由的主体、自由的实现途径和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上超越了黑格尔法哲学。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具体的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自由的主体,自由作为自由本身的主体毫无意义。自由的实现不是在精神领域,而是在认识客观必然性基础上的客观世界的改造,以上两点不难理解。关键在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上,马克思否认黑格尔法的理念是自由的观点,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世界批判了资本主义法治,对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它不是资产阶级标榜的权利、公平和自由,在无产者依然受到物的支配和统治的世界里,法律“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页。,这种法律对无产者来说只能是桎梏,绝非黑格尔所说的是客观精神的实现环节。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新的人的联合体中,个人获得了实现全面自由的手段,才会实现真正的自由。
马克思的法治思想是在借鉴人类法治思想优秀成果基础上形成的璀璨明珠,它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丰富的理论内涵。自然法学派经历了数千年沉淀,是法学史上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远的法学流派,虽然不同的思想家对于自然法的本质和分类见解不同,但是共同的二元论法律观将国家制定的实在法与自然法分离开来,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资产阶级法律的理论武器。康德将人以及人的理性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以大写的人为归宿的法治思想深刻影响着马克思的思考,而他的理性法治为其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法治图景。不过抽象的理想在马克思看来并不能将人类从此岸摆渡到彼岸,唯有借助并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依靠现实的人的实践,才能构建起人类法治社会的理想愿景。
责任编辑:凌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