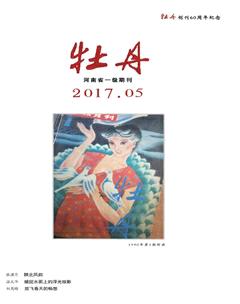“夹缝”中生存
戴世红
《被撞破了的脸孔》是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的第一部寓言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被送到看守所。监房好比一个小社会,犯人的等级秩序类似社会的尊卑之分,而监房中不同等级地位的犯人,最终所表现出的姿态同时也暗示着社会的变化,由此表达作者心中最深的渴望。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很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其实,《被撞破了的脸孔》中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座“铁屋子”以及这座“铁屋子”里的人们。
《被撞破了的脸孔》是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和小说诗学、小说观念有独特的和富于开拓性的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端木蕻良开始了自己的流亡作家之路,作为一个深爱故土的知识分子,他深深牵挂着苦难重重的东北大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災难沉重的父老乡亲,他一直期望国民党政府能够早日收复国土,解救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的家乡父老,然而面对侵略者的不断挑衅,国民党却步步退让,迟迟不下抗日的决心,甚至还不断镇压民众的爱国行动,对文艺界也实行了“宣传管制”。《被撞破了的脸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小说中的“我”,一个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的学生,被关押到一个昏暗、狭窄、肮脏的监房里。这个牢房里一共关押了十四个人,他们以一种奇怪的逻辑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秩序,而我”的到来又给他们增添了“仆人”。“我”被派往的“辰字第十一号监房”只是数万监房中的一座,是一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落,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夹缝。然而,在这样的夹缝中,这十四个人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俨然形成了一个小社会。“我”的到来不是为他们增加变态的乐趣,而是通过反抗尝试推翻他们的“统治”秩序,揭开他们背后真实的面纱,将他们虚假的一面暴露于人前,带动和激励他人反抗,争取尊严和自由。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并依据在监房中的身份将其分为三类,展示不同类型人物在小说中不同的生存境遇,以及突出随着小说的发展生存境遇发生变化的真正用意。
一、不堪一击的“上等”生存
早在东汉时,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以表品第人物,即以人的品行为主,将人分九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在评判人物时逐渐将品行化为次要,而以财富、权势为主要标准,舍本逐末。这种现象在《被撞破了的脸孔》中清晰可见。
王老头,监房东边一行七人的头目,因贪财谋杀十一条人命,是整个监房的“皇帝”,也是“脸孔”的主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监狱是改造的地方,而王老头这样的人,谋财害命而坐牢,五年的监狱时光反而将他“改造”得更为贪婪无耻。他抓住犯人减刑的心理,利用中国司法的黑暗,谋取利益,竟凭借这种方法赚了十万回到家里,甚至一辈子不想出监狱,永远在监狱里作威作福。他是监房里最为典型的“上等人”。从“我”踏入监房门开始,便对王老头那“糊满专横、自私、残忍和欺诈”的脸孔印象深刻,而监房里每一次发起对“我”的欺凌“活动”都源于王老头。对于利益的重视,使得他始终盯紧我这个把国家给闹坏了的穷学生。因此,他跟“我”说话的语气始终带着激愤、粗蛮、不耐烦,甚至狠毒。而王老头对待“我”的这种态度却与另一位“上等人”——张科长形成了反差。张科长是西边一行的头目,“从前看守所的科员,因为行贿下狱,势力照耀一切,河南矮子也得惧他几分”。按排行来讲,“我”是属于西行的,张科长则算是我的“直属上司”,但是他对“我”的刁难不多。不过,张科长表面看起来“高冷”,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当“统治阶级”要求小地主“孝顺”的时候,张科长却假仁假义地以少要了三十而强调自己懂得怜惜人、不能刻敲人,收买人心,虚假伪善。
王老头和张科长均为辰字第十一号监房的“上等人”,一个自私跋扈,一个虚假伪善,当他们面对反抗的时候,真实嘴脸便显露无疑。终于,“我”挥出了那关键的一拳,用以反抗“上等人”的刻薄。挨打的王老头由原来的威武、专横变成了老态、无赖,原本应当咆哮、报复的他选择不作为。而处于同一阶层的张科长则选择了维持均势,明哲保身。“一刹那以前,这张脸孔充满了势利、庄严和不可侵犯的威稜。他全般的感情,简直就是一个帝王的符号!但此刻就如一切都被那反叛的一击所撞破,无边的魔法都从那紫肿犯人窟窿里风化了!”所谓的“上等人”,其实只是靠一种技巧和资格在尊贵的边缘垂死挣扎,到了真正展示“上等”的威力时,便不堪一击。
二、左右逢源的“中间”生存
老一辈人常说,做人做事得会动嘴,即为人处世要学会圆滑,才会有更好的发展。话粗理不粗。但是,成为一个圆滑的老实人并不容易。更多的人将圆滑表现为对“上等人”的阿谀奉承,对“下等人”的侮辱嘲笑,彻彻底底地使圆滑沦为爬上高位的助力工具。《被撞破了的脸孔》中口吃、秃头等人便深谙此道。
口吃,小说中没有交代入狱的原因,但是对他在监房的表现描述得很明显。他“巴结那张脸孔最卖力气,所以被派在第三位,以便随时侍候”。一语言之,即口吃是靠对“统治阶级”的吹捧、奉承换来如今的地位。在东行,居于口吃之下的是秃头,入狱原因不详。秃头的地位在“脚上的镣铐,已经磨得贼光”的礼大爷之上,可见他必定有着维持自己地位的手段。口吃和秃头两个人共同形成了“统治阶级”的随从,对“统治阶级”唯命是从,帮“统治阶级”欺负新人,懂得看脸色行事。他们为科长卷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谄媚之脸暴露无遗。但这样的谄媚之人只能同甘,难以共苦。当王老头遭遇反抗的时候,他们只是以口头形式的“老,老,老了”“老头子有内功”的无力辩解加以解围,实际毫无意义。他们至少尝试着为“皇帝”的无所为辩解,而其他人只是袖手旁观,甚至以看戏的心态好奇这场闹剧的结局。小地主因殴打大美公司的收账员吃了官司,因为是一块肥肉,所以被“统治阶级”看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花钱买地位。小地主屈服于王老头的淫威,对老王头也有几分奉承和恭维,所以当王老头被推翻,他反而感到满足,似乎农夫和“我”帮他报仇了。小掌柜也是如此,被王老头叫了一声,便一声不敢再响了。可是,当王老头陷入窘境时,他便幸灾乐祸地眯着眼小觑他,小人之志毕露。
口吃之流,将圆滑演绎成软弱无能的小人之辈。没有足够的资历成为“统治阶级”,又不愿意与马桶为邻,所以在十一号监房中,“中间”人物的处境显得十分尴尬。在受欺负的同时又与马桶为邻和花钱消灾两种生活方式中,他们选择了后者,选择了自己力所能及并乐意享受的一项。对他们而言,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他们懂得谄媚讨好,权衡利弊,不主动惹祸上身,也绝不随意插手别人的事,尤其是“统治阶级”。凭借这样的小聪明,他们无论是在这个小小的监房,还是在社会中,都不会让自己吃亏,也不会混得太惨,但也不会有大出息。
三、奋起反抗的“下等”生存
人分上中下三等,有上等人和中等人,便自然會有下等人。然而,“上等”与“下等”的尊卑之分是否仍局限于“上下”二字的判定呢?答案是否定的。鲁迅先生在《三闲集·通信》中就曾明确表示过他的态度:“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鲁迅的态度也正是端木在这篇小说所要展现的内容。
“我”,一个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关押的学生,由于是监房“新人”,无权无势,又不是“牢混子”,从一进门开始便受到了各种刁难和刻薄:“蜘蛛似的委他(少掌柜)的脚下”休息;身份地位仅高于马桶;“他”是代表我的专用词,这里指手画脚的讲我时都用‘他指代;受到王老头“皮又痒得慌”的目光恐吓……在这里,“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理想,甚至连尊严也任人践踏。而“我”唯一发现的希望是小天井那一块斗大的天光,那应该是“我”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第一次看见光,仿佛照进“我”黑暗生活中的一缕阳光,带给“我”一点希望,值得“我”反复回念、享受。然而,当王老头用拙劣的演技恐吓“我”,破坏了“我”安静的回念和期待时,它瞬间触及了“我”道德和心理的双重底线,促使了“我”爆发性的反抗:“掴地一拳清脆可听地打下去,他的跄踉的头便很沉重地磕在地板上了,额头上立刻青紫了老大一块!”“我”的反抗是突然的,没有任何预兆。但是,“我”这突然的反抗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下等人”——农夫,当“我们的皇帝”热心指导,接连出声恐吓时,脸色被吓得惨白,表现出恐惧模样看着“我”的是农夫。农夫,因交不上粮入狱,他是唯一一个在“我”进监房之后对“我”表现友好的犯人,并时时提醒“我”这个监房中的“生存技能”。农夫是有反抗之心的,“什么时候我们能不受他们的扣刻?”“我们这样忍苦受饿还得奴打奴做!”,对于王老头们的扣刻和自己的卑微,农夫有抱怨,也有恨铁不成钢的遗憾。因此,当“我”的反抗没有引起王老头的反击,农夫便似乎看破了王老头的虚张声势,却又有所忌惮。但是,他最后与王老头进行的“一场好斗”,掘出了活生生的真实。
无论是论监房中的等级秩序,还是论社会地位,“我”和农夫都属于“下等人”。当然,除了他们之外,也有像白痴、小扒手等“下等人”,但是只有“我”和农夫是真正撞破或者亲手击破王老头“假面”的反抗者,也是胜利者。“啛,你干打雷,不下雨(虚张声势),算嘛劲呢”,道出了“上等人”虚伪的假面和垂死挣扎的真实现状。而原本受尽欺辱的“下等人”在反抗下,像一堆被人遗忘的干草突然遇到火苗,开始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
一个小小的监房,承载的却是一个大社会。端木蕻良将现实社会的黑暗浓缩到一个监房中,构成了一幅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群像图。“统治阶级”王老头之辈、“忍辱偷生”的口吃之流、勇于抗争的农夫和“我”,监房中的犯人们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统治阶级”的专横、贪婪使人气愤,但被压迫者敢怒不敢言,只能顺从苟且地生活着,让作者“怒其不争”,这是近代中国被压迫、被欺辱的社会现状和人民现状。而“我”和农夫反抗的胜利以及强权者的不堪一击,又让人民看到了希望和信心。端木蕻良强烈而又曲笔地表达了自己“反抗必然获胜”的政治信念和抗日救亡的坚定决心,对国民党当局的官僚专制作风和畏敌如虎的软弱无能进行了有力批判。所以,《被撞破了的脸孔》就是一篇充满自信的战斗檄文,在那个特定时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扬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