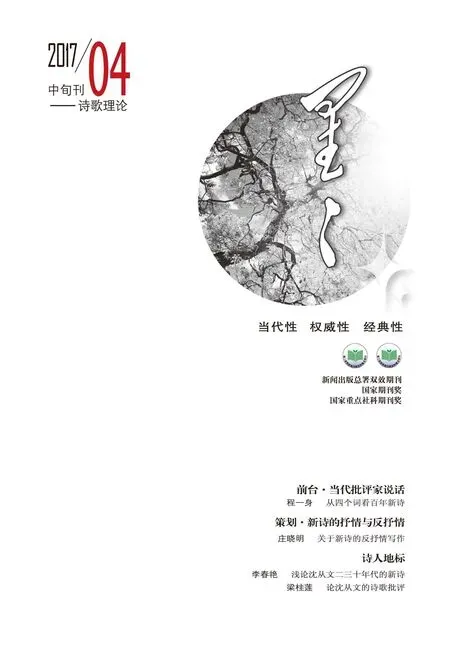现代诗: 接受终端的前瞻
陈仲义
现代诗: 接受终端的前瞻
陈仲义
一
现代诗的星空,辉光散漫,款款情传。仰望者或渴骥奔泉或默想潜思,领会也好纠结也罢,常伴着少语、不语或噎语。当敏触的心扉打开之后,才发现原先貌似简单的“接收”场域,不啻变成刘姥姥的“大观园”,走进去,出不来。一如现代新诗文本的诞生,处处充满着坎坷、暗道、迷宫,往往让人在许多时候继续着无语、失语或难语。
“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毕竟为我们开列现代诗歌接受的应对处方,哪怕有些“药引”过猛。但人们一改此前“作者中心”、“文本中心”主义,从新的视角开始对“读者”投入巨大关注与热情,从中也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本研究试图对上述“舶来品”做一次“中式调理”,在“任督”两脉做点“小周天”的打通工作,则幸莫大焉。
一般来说,古典诗歌因长期积淀呈现出稳定的规范,其接受状态也因此取得普遍认同,分歧不太大。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接受主体的地位前所未有地突出,特别迎合中国新诗——自由、率真、随意的秉性,从而激发、带动多元受众,铺展相对性接受路经,乃至在极端上,让绝对的相对主义汜滥开来,使新诗的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鉴赏解读、批评阐释、定性评估,走向一种大起大落的“纷乱”。而新诗的尖端部位——现代诗接受这一难磕的命题,一个本来还处于疏影半掩、似醒非睡的 “马蜂窝”,突然被捅了一把,随之带出一大堆闹哄哄的蛰刺来,一群人一边揉捏着肿胀的脑门,一边进入不讨好的聚讼中。
二
现代诗学研究涉及三个领域:发生学、文本学、接受学。发生学涉及个体作者的潜意识世界、情感文库、感觉系统、想象工程、语言运作,迄今仍处于完全私人化的“黑箱”状态,可谓一个文本孕育着一个鬼魂;文本学涉及如何将鬼魂的经验、体验、以特有的诗语完成外化定型,它构建客观实在的符号王国,以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及价值指向,为大部分研究者的目标;而接受学涉及群体的“个人趣味”与“共通感”交集一体的阐释最大化,可谓一个文本能变现一千个哈姆雷特,属于那种比个体“黑箱”没那么混沌神秘却也无法丈量边界的“黑洞”。
本研究圈定在第三个领域。文本发生与定型多属个体行为,多是个人意识活动与言说的外化结果,文本定型具有“雷打不动”的确定性。而文本接受面对的是永无止息的“喧哗”,有个人趣味的聚散,有共通感的趋同、有相似家族的“约法”,更有背叛、逆袭,篡改的种种变数,故文本接受与文本定型一直存在深刻的二律背反。文本定型(意图、含义)的客观性与文本接受的主观性(阐释、追索),存在着永恒的无边与有界的“对抗”。纾解这一难题,我们聚焦在最后的四个环节:
敝帚自珍,再唠叨几句——
接受前提:“阐释共同体”。
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为接受的大趋势,必然带来无序的负面。要抑制接受过于主观随意,提倡 “阐释共同体”作为前提条件,看来乃是目前实施纾解的最佳选择。通过“家族相似”的对话争辩,共享接受温床的“通约性”,削弱个别成员对文本意义的独断裁决,努力趋归共识性“苟同”。经过无数冲突、平整,无论在枝节细末或总体宏观,经由“共同体”的过滤,总会留存相对共识的理解,而相对共识的理解,多少总能弭平个体差异带来的鸿沟。在泥沙俱下的情势下,进行自洽性寻找与选择,至少在最小公约数方面不致完全落空。作为一种相对确定性的“控制机制”,阐释共同体(品级共同体)发挥阻止过分主观、随意、无节制接受功能。 一方面让阐释的自由落到读者身上;另一方面又以某种相对确定的意义作为“有界”制约,为现代诗的接受提供基本保障。
接受平衡:“哑铃”图式。
虽然有接受的前提保障,但文本的客观性与接受的主观性永远是矛盾的焦点。如果把双方比作哑铃的两端,且具有此消彼长的特性,那么从横截面看,左右两环各代表自足性与开放性的一方,连接双方中间的“把柄”,便是具有贯穿调节功能的张力。欲取得这种辩证的平衡,自然得看双方的“膨胀系数”,即文本结构的自足性越丰沛,张力通道撑得越开,流量越大,接受越丰富,接受效应越高。反之亦然。接受一方偏弱,张力的通道受阻,流量偏少,文本增值的可能性受损,接受效应偏差。若从纵向上看,左右两环则变成接近重叠的“同心圆”:一般而言,内环密度恰当(如文本紧致、含蓄、适度晦涩),容易让外环(接受)随之撑大、放大、扩大;内环密度较小(如文本稀松、清楚、过于明白),容易让外环随之缩水。在内环(文本)不变的条件下,内外环的动态关系主要呈现为三种情状——内外环基本重叠:意味着文本客观性与接受主观性大抵“持平”;外环小于内环:意味着文本的客观性偏向“闭合”,接受主观性呈现“缩水”;外环大于内环: 意味着文本客观性偏向“发酵”,接受主观性愈加“溢出”。哑铃模式的建立,应该说,是对此前文本中心主义的相对“抑制”、对接受主体开放性相对“宽容”,至少双方有望接近“平分秋色”的同价地位。此消彼长的博弈拉锯,反应了文本客观性与接受主观性的动态平衡。乐观地看,这一图示不仅适用于现代诗,或许还可扩展到其他文类。
接受的“四动” 响应:
现代诗接受的直接与感性征象,是心理层面的响应。接受心理响应可用一个“动”字来涵盖。心灵有所触动,不管强烈与否,只要出现“动”——“有所动”——“能够动”,就取得诗歌接受的许可证。传统的“感动”作为一个重要的接受响应,其实已渐渐适应不了时代变数。现代诗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感动,还可能带给你智性层面上的悸动,带给你精神意识上的震撼,也可能只带给你纯生理上的快感,或语言上的惊动。由是,将好诗接受的“一动”,增补为接受的“四动”“交响”,同时形成多元“配对”是可行的。“四动”在本质上是整体性与交互性的。有时也可进一步“分解”,做出相应转化——情感历险中的“感动”,属于人性隐秘幽微之发见;精神历险中的“撼动”,属于经验体验之发见;思维历险中的“挑动”,属于智慧灵性之发见;语言历险中的“惊动”,属于陌生化言说之发见。它们是诗美规范与诗美形式对应于心理上的型构,符合文本接受的开放性趋势,也是审美接受体验的生动“表征”与“依据”。
接受坐标与品级梯度:
尽管艺术接受具有无可违抗的模糊性,我们还是乐意尝试用宽泛性的“建模”来表达对“无边有界”坐标的推行。接受坐标的纵向轴列,指示着文本的客观性。其生成性体现为文本的形式化结构,由文本内部主要素(诗质·诗语·诗形)合成,相对独立,也相对恒定;横向轴列则以“心动”(感动·撼动·挑动·惊动)标示接受响应度,从而形成在生成性标高投射下,围绕“心动”的品级梯度,并在横向轴列上呈现品级的五种梯度:居中的“心动”对应于较好的诗,那是带有特点、有亮点的好诗;“心动”犹如钢琴键盘上的“中央C”,愈是右移,愈是朝向有所发见的好诗,直至最靠右端的“大动”“恒动”,则接近于恒久常新的经典文本。而居中左移的,愈向左移愈趋向接受响应的“微动”及至“无动”,那便是毫无特点的、一般化的庸诗、差诗;再继续左移到端点,则是劣诗非诗。它对应于古人在艺术裁定上长期积累的“五品”(无品、下品、中品、上品、极品)。人们可在这一把内化的 “游标卡尺”之间移动,应对着文本的接受现实。
三
标签着本次现代诗接受的“专列”,因属于头一遭运行,路况不熟,过山穿洞,迂回往复,大有直线曲走,弯道蹒跚。但屈指算来,挂靠的车厢还算不少:接受的中西比较,接受的古今差异、接受的风险评估,从有效、无效到接受的两大入径,再到细化响应、品级坐标……洋洋三十万字,似乎有点模样。然而,十来节或空疏或淤积的车厢,充其量也只能算作简要的“引论”,每个车厢,完全可以在将来,再开出自己长长的“专列”。包括附编里貌似外围性接受——有关翻译教育传播的讨论,都指向接受的广袤天地,有着说无尽的话头。
勉为其难的司炉,说实在的,真不希望在本质主义观念支配下,一直把控传统的、整一性的美学把手,沿着规范轨道,寻觅那些学科化的景观——一幕幕有序地迎面而来,一幅幅渐次掠窗而去;而是不时张惶左右,在接受的无尽“隧道”里面,疑虑理想化的愿景究竟怎么回事,思量真有那么一条接受的“规律”路线有迹可寻?事实上是,在残存的本质主义观念与接受的无边博弈中,摇摇晃晃、高一脚低一脚地试探着,经常是遵循“兴味”的方向,投身于“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欣悦与漫游,而罔顾其他。或许这样做,比起理性的“目标性”追获,美味几分?而对于广大乘客来说,不管是眺望、冥思、闲聊、默想,打开更多可能性天地,比明确的答案不是来得有意思多吗?
回想新诗进步之神速、接受之变数,可谓“叹为观止”。当初《尝试集》第一版扣除旧式诗词、“半言半文”,及翻译“水货”,真正够格称得上白话新诗的,大约只剩14首。[1]而周作人《小河》被誉为“新诗中第一首杰作”,放眼当下,初学者与之持平的当不在少数,可以想见当年新诗出道之嫩。而演变至今,其高端部分——现代诗的接受,则是另一番深壑险谷,一言难尽。面对掀雷决电的进展与千叼百难的接受,现代诗这一“尤物”的确经常让人无所适从,如坐云雾。即便如此,在全书基础上,笔者仍不妨对未来的接受前景也做点谬悠之测吧。
可能一 :走向文本接受的“规范”。
新诗的价值,已然不再像从前那样听命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话语)的主宰,也不完全由内容直接获取,而是泰半要经由自身的形式化美学来确证。故而强调、突出形式对内容的转化,意味着对诗美规范的追求,也意味着对某些随意、放任、尤其是非诗元素的禁令;而形式化的规范对于只以分行为标示的自由体式,也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不言自证,诗美规范是诗歌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诗歌经验的升华,是诗歌生生不息的魂灵。正是“诗美”及其唇齿相依的形式化存在,才使得诗歌成为人类精神永不消失的瑰宝。诗美规范既有永恒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流变性。虽然各个时期的诗美规范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每个时期都会淘洗出具有生命力的诗歌经验汇入到总规范的建构之中。规范意味着稳定、秩序、尺度、甚至标准。那么最终,一旦文本学规范与接受学规范建立起来,我们就有可能在诗美规范的指引下,大体确立文本性“标高”,即生成性主导下相对稳定的文本价值指向——具体呈现为张力调节下的某些可公度的诗美“指数”,形成较统一的尺度。当现代诗经过道尽途殚的折腾,完成自身诗美规范的型构,我们或许可以说,新诗的高级形态——现代诗到底成熟了,现代诗的最终会如同古诗那样,以稳定的规范,步入常态化的接受轨道。
可能二 :永远处在追新求变的“途中”。
然而,“一切艺术创造革新,都是为了逃脱圈套,达到自由的澄明,进入一种新的规范。可是在挣脱了旧的圈套,创造新的规范以后,真正的诗人又感到这仍然是圈套,难以忍受新的遮蔽。”[2]这种前仆后继的挣脱,是因为“在所有文体中,诗是最容易折旧的”(洪烛);它“天然地充满着元写作的特征”(颜炼军),同时也洋溢着“元接受”的诱惑。由此带来的分化、蜕变,使得现代诗本体属性一直充满“泛化”状态,同时导致现代诗美形式规范一直处于离散的、尚难凝聚之中。而“人们却总是‘急于’给予新诗一个指认、一种确定,仿佛非如此不能安身立命。正是这种所谓‘反者道之动’(《道德经》),使得新诗自由创造的活力与无限的可能性,继续弥漫在‘确定’的轮廓之外。”[3]
百年历史证明,新诗、现代诗自由放任的本性,其超强的野性,不但无法定制 “辔头”,在诗形(形式、体式)、诗涵(内容、意义)、还是诗质(本体性元素)等方面应规蹈矩,反倒释放出它继续追新求异的内驱力,在历险与实验的道路上,它边丢弃边积蓄,边反叛边沉淀,边存活边生成。而以趣味为中心的现代接受主流,教广大受众按照自身感觉,各取所需,各行其是。“交互”的结果,使得新诗、现代诗在规范——反规范——再规范——再反规范的无穷循环中,箕裘相继,酿成新诗、现代诗少规范或无规范的宿命。业内于是得出一种结论:新诗、现代诗一直处于“半途中”。兴许这样的“半途”,才是新诗、现代诗真实的命运写照和根本宿命。也就是说,永远的“半途”,是新诗、现代诗整体接受前景的另一种可能。女诗人阳子发出多数诗人的心声:这个过程必定是一个棱角分明一触即疼、半生不熟一咬就流血的过程。是一个左冲右突的抗争过程,诗歌永远是不可能完成的,写诗就是“诗在写你”的过程。[4]如果这样的说法大抵成立的话,那么现代诗的接受就是永远处在一个“半拉子”工程。
这是肇因于现代性永无止息的变异。现代诗“一旦进入现代性的序列之中,就会不断地从自身获得规定性,这种自我确认的力量是由不断自我更新来完成的,这是一种现代历史想象力的要求。”[5]在它推进过程中,现代诗就范为一种“专制性幻想”和“否定性范畴”(胡戈·弗里德里希),同时依赖“不断运动的逻辑”(米沃什)成为“一套标榜新异的认识装置”(胡桑)。由此派生出先锋性、探索性、实验性,便制造出难以消停的“永动机”。尽管瓦雷里在《诗人笔记》中告诫人们,不可追求标新立异,早上的独创当天晚上就被复制;而且在早上越是触目新奇,晚上就会益发难以忍受。然而,在现代性的“推搡”下,谁也无法禁止现代诗变动不居的本性和由此本体带来接受的巨大骚动。
可能三:文本自足性与接受开放性的统一。
上述两种接受现状与前景,各有各的道理,同时凭着各自理由加剧双方的对峙,作为稳定与骚动的两极,它集中暴露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审美接受中心论的一元化与多元取向的矛盾。本研究更愿意秉持第三条道路,主张文本自足性与接受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作为客体的诗歌文本,它具有自立、自洽的自足性与客观性。好比眼前这一个茶杯,再怎么样怪异,我们还得承认它具有某些本体属性与功能,它是可供喝茶的、可供喝酒的、可供喝奶的、甚至还可转换为一种可供插花的瓶子—— 一种不至于远离杯子本体、本性、本质太远的接纳器皿。从这种残留的本质主义观念出发,笔者坚持客体拥有某些基本属性,正是这样的基本属性决定客体的存在与价值。也因此,诗歌文本具有相对客观标准。
而从接受终端的效果看,文本历经年所,遭遇不同语境,积压各种潜能,包括正读、误读、异读、臆读,伴随歧解、扭曲、蒙蔽,以及放大、夸张,使得文本在接受中面临超强开放性。继续类比眼前这一个杯子,在各种情状的接受视域下,杯子可能变得面目全非了。比如在梦幻、初恋、潜意识、错乱、癫痫、迷狂、毒瘾、分裂症、或微醺的“醉眼”下,杯子被“变形”了:或被看成酒瓶、看成乳房、看成鸽子、看成石头、看成手雷、看成灯泡、乃至看成尿壶,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杯子部分或完全脱逸出它原在的本体而成为“它者”。在艺术世界里,你怎么能一口咬定是眼睛发生“老花”?是心灵出现错误?你反而要宽大为怀地包容所有言之有据的阐发。
这就是客体自足与接受变数的巨大落差,也是目前导致新诗、现代诗尺度混乱的内在缘由。尽管“读者中心”有上升势头,一再削弱作者中心的“一言九鼎”,但过分倾斜的尽头不利于“有界”的纠偏。如果再度回溯到老康德的“鉴赏判断”上——老康德其实没有过时,鉴赏判断直指客观化的主观,很早就在“源头”上为审美开具了更为接近“真理”的路条——即审美从个别性、愉悦性、非功利,走向普遍共通感。但是康德在获得共通感的结论后无法再走下去。最棘手的问题还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巨大的个体差异性不断在瓦解共通感。所以在碎片化语境下,窃以为,还是很有必要倡导“共同体”,不论阐释还是品级——让文本与个人趣味、文本与共通感有个基本约定。这样,在找不出更好“方案”时,可以顾及接受的出发点,又可锁定落脚地。
如何将文本的客观性与接受的主观性统一起来,是接受的最大焦点和难点。一味坚持诗歌本质主义的“大一统”规范,虽有助于葆有新诗、现代诗审美的客观性,却遮蔽了个体接受差异的强大事实;全力遵循个人“趣味中心主义”引领,朝向无边的开放,则可能加剧原本就失范的相对主义,使新诗、现代诗趋于更加无序的混乱。本研究尝试用品级共同体(品级坐标)与五种品级梯度,来“缓解”接受的巨大差异。但愿这是一个开始。
四
再多再好的理论,都得用之于实践。新诗、现代诗接受领域关涉了太多具体的实践问题,关涉太多主观性问题。新诗、现代诗接受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良性的生态环境(普及、推广、筛选、甄别、经典化)形成,在良性循环中推进“好诗主义”。人们的接受,总是朴素、自然地集中在对“好诗”的翘望中。但吊诡的是,容易说出口的“好诗”两字,其实很难被一致性地选中。早在几十年前,九叶派诗人唐湜就告诫大家说,“好诗,潜伏在字里行间的流质永远不能被人啜干,好诗的理解与感受或二者的凝合永远不会完全,……连他自己也只能朦胧或茫然地凝视,却不能轻易地说已经把握了永恒或全般”。[6]怎样从无边无际的浅水与深水里捕捞到好鱼,做出令人信服的鉴别,既葆有学科的“选美”高度,又不失普及层面的众望所归?在在是一种挑战。无意从“本本”出发,体大周虑地完成“方正”式教科书书写,改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和方式出发,关注接受中的海流、气象、风浪、潮汐,尤其探讨接受者手中细微的操作手段:垂钓、叉刺,拖网、电击、围堰。希冀在忙碌的季节与盐味的南风里,谛听到那起伏的鱼汛……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诗歌审美接受研究》(14FZW005)之结语
注 释
[1] 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1922年第1期。
[2] 孙绍振:《论新诗的第一个十年》,《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3] 秦晓宇:《共此诗歌时刻》,《读书》,2014年第2期。
[4] 阳子:《编后记》,新死亡诗派年刊·《诗》,总22卷,2015.12.27。
[5] 胡桑:《蘸取当下的晦暗:关于当代诗与现代性》,诗刊社公共号,http://oicwx.com/detail/425112,2015.6.23。
[6] 唐湜:《严肃的星辰们》,《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