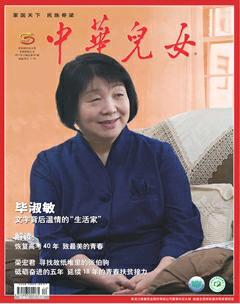陶海粟:我和我的同学们
有人说,七七级的学生是一届空前绝后的大学生,的确如此。我们北京大学经济系七七级的两个班,入校时年龄最大的张文祥31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郭京平18岁。换句话说,张文祥高中毕业时,郭京平幼儿园还未毕业。全年级80个同学,只有一个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人上学前都是厂矿职工、机关干部、现役军人、中小学教师或下乡知青,大家带着满脸的“沧桑”聚到了一起。
同学中不少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在基层摸爬滚打,与数理化久违了十年,加之报名之后只有一个来月的复习时间,又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大多经历了一个点灯熬油、悬梁刺股的拼命阶段。例如焦天立说,他用了十二天自学了全部高中数学,那些日子夜里睡梦中都在背数学公式和做题。易纲那时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高考当天早上4点钟爬起来,和大师傅一起给大伙儿做了饭之后才去赶考。
1978年的那个春天,人民刚刚从噩梦中醒来。从刚刚打开一个缝隙的国门望出去,人们惊异地发现,原来我们准备去拯救的、人民受苦受难的西方世界,竟然早已和我们拉开了一个难忘其项背的距离。荒废了十年学业的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到钟表那滴答滴答的逼人声音在催促着、鞭策着。入学后刚发下课表,看到党史和哲学等公共必修课时,一些“老字辈”的同学(没有一定之规,大体上25岁以上的都被年轻一些的在姓氏之前冠以“老”字)动了心思,商量后集体向系里提出:这些东西我们早在基层时就自学过了,我们请求对我们进行测试,通过后允许我们免修这些课程。这在当时对于习惯了按部就班教学的老师们来说,真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不过当时我们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石世奇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支持了我们的要求,公共课教哲学的徐明老师虽然开始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对这些“特殊的”学生实行特殊的办法。后来徐明老师出了哲学考题,正式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闭卷考试。部分同学果然通过了考试,得以免修这门按规定要修两个学期的课程,争取到了一些宝贵的自由时间以加快学习的脚步。
自此之后,经济系这届学生不断在各方面显示着超越常规、自主求新的特色。第一个学期结束了,大家在暑假之后返校,两个班联合召开了家乡见闻交流会,大家把在暑期中进行社会调查的成果进行交流,讲得有声有色。邓英淘从一进校就“神出鬼没”,经常去外系听课,对经济系自己的课程,从不追求高分,勉强及格了就行。“追随”他去外系听课的,还有徐笑波、徐未曼等。
入校后刚第二个学期,虽然我们的经济学功底还乏善可陈,但这些早在基层有过长期磨练、又密切关注着国事的同学们,感到有话想说,想“指点江山”。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经商量之后决定办一个年级同学自己的经济学刊物,取名为《学友》,第二个学年一开学就创刊了。一开始是油印,大家在“文革”中印传单的手艺派上了用场,后来从第三期开始得到系里支持,改为打印。全年级80个同学基本上都以各种形式参与了《学友》的工作。吴稼祥是我们班级的诗人,写了创刊号“编者的话”;李少民在部队时就是画家,自然做了美工。从创刊到1981年毕业前把《学友》出版工作交付给七八级,全年级共有六十多人次在这个刊物上发稿。有丘小雄比较债券发行的利弊得失、刘海林分析法律调整经济的有效性、石小敏对“按劳分配”的质疑、张炜率北大学生代表团赴日考察的观感、易纲三年级时赴美留学前对“思想解放”的思考、王敏和刘玉香对苏联经济的看法。何小锋探讨劳务价值的文章和毕井泉调查农业增收增支的文章后来还分别被《经濟研究》和《经济科学》采用。除了这两篇外,经济系七七级同学在校期间写的文章曾先后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毕业前最后一年,几个同学还应商务印书馆的约,翻译出版了一本《当代十二个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