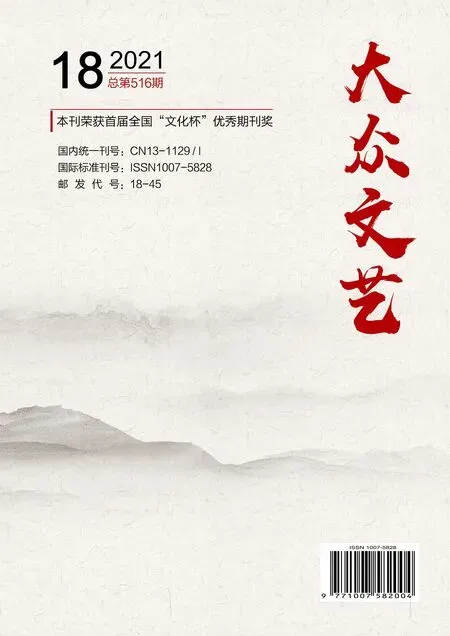虚无的故乡
——论苏童“枫杨树乡”系列小说创作动机
周 巧 (华南师范大学 510631)
虚无的故乡
——论苏童“枫杨树乡”系列小说创作动机
周 巧 (华南师范大学 510631)
苏童笔下的“枫杨树乡”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故乡,是一种对于生命根脉的想象,一种对祖辈文化的探索。塑造“枫杨树乡”这样一个不存在的故乡是源于苏童对于虚构与想象的热情和痴迷,以及对自我灵魂根源的追寻,是一次精神的还乡之旅。
枫杨树乡;“根”的追寻;还乡之旅
苏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是一位凭灵感与才气写作的文人。1987年发表《1934年的逃亡》开始引起文坛注意,自苏童开始创作至今的近30年的时间里,创作了《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之家》、《米》、《河岸》等一系列关于“枫杨树乡”这个虚构故乡的小说,描绘了“枫杨树乡”祖辈们的各种生存状态。而苏童为何要如此大量地描写“枫杨树乡”这一虚构而又独特的文学世界呢?带着这种困惑,笔者在这里对苏童“枫杨树乡”系列小说创作动机进行了一些探索。
作家总是与自己的故乡有着无法割舍的紧密联系。20世纪启蒙文学大师—鲁迅,作品中的“鲁镇”便是他童年生活的回忆与追寻,在鲁镇我们看到了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鲁四老爷,以及在这种吃人思想残害下的祥林嫂的悲惨命运。“鲁镇”是鲁迅对少年生活过的浙江绍兴的生活记忆,更成为他一生的文学资源。莫言在故乡山东高密重建“红高粱家族”,追溯着历史的渊源,重构着民族的精神。如众多作家一样,苏童同样具有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学资源,苏童说:“人们就生活在世界的两侧,城市或者乡村。说到我自己,我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我的身体却在城市的那一侧。”苏童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交接处,因此,城市与乡村都融入了其生命的血脉。苏童世界的两侧:一侧是“枫杨树”的故乡,是苏童根据自身家族血脉渊源所虚构的故乡。一侧是“香椿树街”的城市,是其真真实实的少年城北地带记忆,从而构造了两个独立的艺术世界。这里暂不讨论苏童文学世界中作为城市代表的“香椿树街”。苏童的祖籍在江苏扬中县三湄乡,但苏童却从来没有在乡村生活过,那里只是遗留着父辈们的生活印迹。由此,我们可知苏童的“枫杨树乡”是一个虚构的并不存在的地理空间。如果说苏童与他所虚构的“枫杨树乡”有什么真真切切的联系,那唯一的便是孕育在苏童血脉中的家族基因。我们不禁会思考那是什么原因促使苏童如此痴迷于表现笔下的“枫杨树”世界呢?
一、“虚构与想象的热情之源”
苏童的作品具有超乎常人的想象力,虚构和创造更是作品不可或缺的写作手法,他有着表达这个世界的强烈愿望,以其个性化的文字颠覆着对生活和历史本身的叙述。正因如此,苏童这种虚构的热情就是“想闯入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从而来表现自己不曾涉及的世界获取文学资源的提升。苏童说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虚构对于他一生的工作至关重要的。虚构必须成为他认知事物的重要手段。”可知苏童自身对虚构手法有着清醒并执着的坚持。因此苏童对“枫杨树乡”这个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故乡的创造正是借助虚构、想象的手法来极力丰富和夯实创作经验和人生历程,从而获得物质与精神上的提升。张学昕说“苏童正是在小说这种虚构的工作中实现着他虚构的梦想和快乐,而且虚构在成为他写作技术的同时也成为他的精神血液,不仅为他个人有限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和艺术思维的广阔空间,也使这文字涉及的历史成为其个人的心灵历史。”这里的“精神血液”就是苏童对故乡文化的一种渴求,是对生命历程中故乡缺失的一种补偿,是作者记忆深处中对于祖辈文化的投射与想象,更是对根深于作者血液的生命程式的追寻。
苏童通过虚构手法创造了“枫杨树乡”这一系列的小说,建立了一个衰败、颓废、晦暗的故乡世界。“苏童最倚重的资本就是想象力,他靠这种内心的力量来结构故事和文本,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他头脑中的产物……他笔下的“枫杨树”故乡就是他虚构的一个精神之乡。对于那个叫杨中的祖籍苏童没有多少概念,只是远远地望过一眼。可是那一眼望不清的小岛正好激发了苏童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出于主观,就多半由情绪来控制而非客观的事实。于是他的文本中就出现了那个神秘的遍布灾难又让‘我’为之魂牵梦绕的枫杨树。”正因采用虚构的手法使“枫杨树乡”中有与女人和狗苟合的“幺叔”、有亲手淹死自己孩子的花影、有对女人和米痴迷变态的伍龙、有永远在无意义逃亡的陈三麦。苏童所塑造的故乡是对真实世界的抽离与变形,是对世俗世界的超越与反叛。正因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产生的距离从而构成一种叙述的自由,可以在更少的限制中发挥着作者的想象。正如苏童自己的观点“兴趣和距离导致我去写,我觉得这样的距离正好激发我的想象力”。“枫杨树乡”正是以想象为激发点使其产生强烈的渴求,渴求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通过对故乡历史与文化的交织来叙述先辈一个个生命的历程。
二、精神的还乡—“根”的追寻
除去想象与虚构的热情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苏童对“根”的追寻,是对自己家族血脉文化的追溯,是一次“精神的还乡”。正如研究者范伟钰说“枫杨树故乡与香椿树街是笔下的两大故乡,他以这两个地域为背景,展开他对过往岁月的独白,妮娓道来,期间穿越城乡之间,最终总以回望的姿态作结,聊以慰藉内心的‘还乡’情结。” “蕴藉内心的还乡情节”就是一次追寻心灵的还乡之路。 纵使这是对祖辈历史记忆的“缝补缀合”但正是作者对“根”的追溯,使其对枫杨树乡的感情如此真切热烈。“枫杨树乡”是其难以逃离的根源与血脉,正如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永远也无法抹杀的潜藏于家族世世代代的生活、文化、历史基因里的物质。一旦提起,都会有着深深的眷念与缱绻之情。如苏童在小说《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描绘的浓郁的故乡感情:“多少次我在梦中飞越遥远的枫杨树故乡,我是否隔着千重山万壑水目睹了那场灾难呢?”这是一种化不开的故乡情结但这样的故乡却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故乡,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是掺杂着个人生命历程与记忆,故乡就是“我”的一部分。而苏童的“枫杨树乡”则是一种脱离“我”的故乡,仅仅作为一种精神追寻。“枫杨树乡”是作者对于祖辈文化的投射与想象,是对根深于作者血液的生命程式的追寻。正如吴雪丽说“苏童的故乡是抽离了‘我’实在的生活经验的想象域,但他虚构的‘枫杨树乡’的故事在失去基本的物化参照之后其携带的‘精神史’却因游离了具体的能指而意蕴丰盈。” 的确如此,苏童运用冷漠但又饱含深情的笔触叙述着出现在“枫杨树乡”一个个执拗的灵魂。他们从出生起就与枫杨树有着永远的牵绊,无论身在何方,干着何事,永远都逃脱不了“枫杨树乡”。与此同时苏童也是对独具阴郁,晦暗的祖辈往事在破败、荒凉、污浊、腐败的南方乡村肆意流散的灵魂的探寻。这是源于作者对血液文化根基的想象,枫杨树村是故乡的姿态。其所描述的南方世界中的生命个体表面是在对“根”的溯源、对城市文明的追寻的矛盾挣扎,而实则是对处在柔软,颓废,迷离南方世界生命个体那游离,漂泊,散乱的灵魂的追寻。祖辈和亲人的灵魂在这样一片满是罂粟味的土地上逃遁,沦落,救赎,接受着命运的惩戒,他们焦灼的躁动正是一种命运无法把握的无可奈何,是一种灵魂无法安放的漂泊。这样的精神还乡也是作者的一种精神漂泊,漂泊到了那个不曾见过的故乡,脱离于大地的故乡。这样的还乡来于虚无,必将终究归于虚无。正如《外乡人父子》中的外乡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却仍如同异乡,故乡即是异乡。当世世代代的枫杨树人都是一个个漂泊的灵魂时,那么作者这个“外乡人”则更不可能在这脱离了大地与历史的故乡实现”精神的还乡”,永远是一个无根灵魂的游走。正如研究者说:“他无法摆脱对虚幻故乡的眷恋,这便构成了苏童小说的一个重要的难以解开的情结:还乡者的梦游。虽然不能把‘枫杨树’和苏童的祖籍画等号,但实际上‘枫杨树’却已经成了作者的精神故乡。”
[1]苏童.《苏童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2]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8,45.
[3]孙丽秀.苏童小说主题论[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13,58.
[4]范炜钰.苏童与托里.莫里森“逃离”主题的比较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13.
[5]吴雪丽.苏童小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4.
[6]赵菲.苏童小说研究综述[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3):13.
周巧,女,1992年2月出生,汉族,硕士,华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