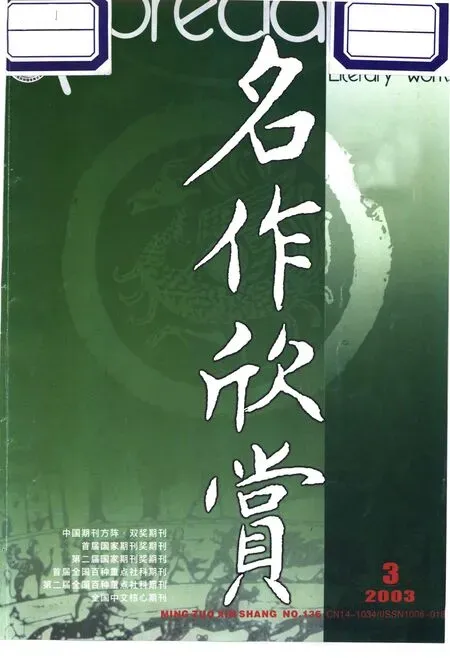雅俗消融视角下的通俗文学再评价
⊙胡 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雅俗消融视角下的通俗文学再评价
⊙胡 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的矛盾与调和一直是20世纪现代文学所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梳理雅俗文学的流变与发展,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互动与互融。
通俗文学 严肃小说 雅俗互融
中国小说本没有什么雅俗之别,清末梁启超等人进行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是启蒙国民的利器,小说创作的社会意识才开始明显加强。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通俗小说和严肃小说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至三四十年代,两者则渐渐走向融合衍生状态。陈平原学者认为:“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对峙与调适,无疑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动力。”不管是对峙还是调适,两者始终并存。
一、雅俗文学的发展流变
小说向来被看作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读物,“是以君子弗为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梁启超等人将欧化的文化哲学思想贯穿于小说创作中,小说创作才有了强烈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功能。鲁迅等人的新小说被称为精英小说或严肃小说,这类小说以西方的文化视角分析中国文学、启发民众。而承接中国本土传统的小说被称作通俗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文学”一直被理解为“新文学”,而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则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只是偶尔被当作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和一个反动派别来谈及。
钱理群等学者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写道:“通俗文学的概念一向比较模糊,是因为它的文学地位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人们强调它属于旧文学或封建文学残余的一面。”近年来,学术界大致给“通俗文学”厘定的定义如下:
中国近现代的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本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自从小说分雅俗之后,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就有了各自的发展路径。就文学的整体结构而言,犹如人体之肢体,有正脉和支脉,这两个系统相互配合。承担着教育民众、启蒙社会大任的新文学是这一时期的正脉,占据文坛主流;为了生存而迎合市场的通俗文学,则可视为支脉,它依附着社会的市场经济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带头将文学变成商品,占据着现代文学的市场。
中国的传统通俗文学在小说这一体裁上发挥得尤为明显。通俗文学中有一批武侠小说,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仁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些小说在当年都曾轰动一时,成就斐然。另外,还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贾玉怨》等,这些也曾风靡一时,销量达到数十万册。鸳蝴派的集大成者是张恨水,他的《啼笑因缘》1930年在《新闻报》上连载后,不久便对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之后的十几年来,这部小说被陆续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各种艺术体裁,因此形成一股持续的“啼笑因缘”热。此时通俗文学的发展已经不容小视。到了20世纪40年代,通俗文学面临着特殊的战时文化境遇,“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而是中华民族在面临生死关头,富有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的中国作家,以文学的形式开展的民族救亡事业”。此期的抗战文学成为主流,雅俗对立方才渐趋消解。
二、婚恋母题视角下通俗文学的雅化
笔者认为雅俗文学的区别在于文本的价值。雅文学指向人生的严肃性,俗文学则指向娱乐性和消遣性;雅文学挑战传统意识,俗文学则屈从世俗意识,没有思想独立性。
本文将借“婚恋母题”小说这一个案,探寻现当代文学史上小说这一体裁是如何一步步由俗入雅的。中国的小说很多都包含着婚恋情节,有的作为文本的主要情节,有的只是充当支线情节,同为婚恋母题,作品的定位却不尽相同,笔者尝试以作品中的雅俗(内容)比例为切入点,对作品的雅俗定位进行细致分析。
(一)主题的雅化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引起了很多文坛中人的瞩目与创作。我们拿丁玲的《韦护》来分析。《韦护》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的恋爱和冲突。韦护一方面坚持着他的社会革命工作,另一方面又迷恋他与丽嘉的美好爱情。文本想揭示的主题是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以及最终革命是如何战胜恋爱的,个人主义是如何向集体主义妥协的。韦护选择离开丽嘉,坚定地奔赴革命的中心广州,文本中虽然也杂糅了不少温情的恋爱细节,但这里对恋爱的叙述只是作为文本整体的润滑剂,“故意加入爱情的调料,显示出相当突出的罗曼蒂克的倾向”,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读者。这样的小说既可以获得一定的市场,又体现出了宏大的严肃的叙事主题。这就是俗为手段,雅为主题。
(二)现代性叙事因素的加入
小说的由俗入雅化在海派小说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最初的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由操新文体而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来写的。从接近市民这一点来看,它们是接续着鸳蝴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再来突围。”主要作家作品有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
海派小说文本中对于恋爱描写的突破之处在于,“恋爱成为海派表现现代人性的试验场和归宿地,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增添了当时理解的‘性自由’的色泽,遂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故事依旧是恋爱中的游戏说,但新感觉派作家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作品便呈现出另一风貌。
首先,现代性空间要素的位移。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飞速发展给海派文学带来新的契机。游乐业、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舞厅、赛马场、夜总会等新式消费场所是海派作品中的一个大的文本背景:“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无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灯,有了高跟鞋儿,也有了钟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这种带着现代性的空间要素本身就带着一种腐朽、异化和批判的味道,作者在描写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物时,又突出他们病态的心理和行为:卖淫、乱伦、暗杀、拜金,“金子大王胡均益躺在地上,太阳那儿一个枪洞,在血的下面,他的脸痛苦的皱着”(《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海派“恋爱”文学就不单单是表现恋爱过程中的二重人格分裂,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半殖民地都市的真实画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对人性的摧残。
其次,现代性思维方式与观念的融入。比如恋爱观念的转变,在传统通俗小说中基本上是男尊女卑、男弃女的模式,但在现代性观念中,女性地位上升,甚至是女性玩弄男性于股掌之中。《苔莉》是叶灵凤的代表作之一,女主人公苔莉赋闲在家带女儿,因寂寞空虚而与堂叔发生婚外情。苔莉大胆追求情爱满足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传统通俗小说中女性形象大抵属于逆来顺受、温婉乖巧型的,她们兢兢业业照顾着整个家庭的生活,不敢逾越半步封建礼教对她们的束缚。而在海派作家笔下,上海的时尚与兼容并蓄让女性长袖善舞,而女性也以她们独特的魅力主宰着自己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和男性平等竞争的机会。
再者,新感觉派重视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因为要表现新上海追求猎奇的繁华风貌和十里洋场的工业化气息,新感觉派作家大胆改变叙事切入的视角,尝试心理的、象征的、新鲜大胆的小说用语和多元化的表达技巧。在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中,恋爱情节使用心理分析小说的感觉(幻觉)描写,如文章里的“我”在送打伞少女回家的途中,“我”感到这少女很像我年轻时的女伴;“我”偶尔看到一家店里站柜台的女子,便仿佛感到对方眼神里的嫉妒和忧郁,因而怀疑那就是我的妻子。小说抛弃传统文学中对恋爱情节真实的描写,将人的主观感觉渗透到客体的描写中去,亦真亦幻、真真假假。
三、雅俗文学的互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研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如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通俗小说史著作,该书介绍了众多通俗作家和作品,保持了较多的历史细节,其所提供的资料和观点为以后的通俗文学研究铺设了基础;80年代中期以来,范伯群教授一直致力于通俗文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他独撰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这两本编著系统地梳理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流变,将通俗文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前一本书被学界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范伯群教授提出的“两个翅膀论”,认为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各为现代文学的一只“翅膀”,二者相互平等,互为依存,改变了现代文学史是严肃文学的“单翅”这一传统观念。与之相应,对通俗文学作家的研究也到了一个以肯定为主导的阶段,如徐德明教授于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十套节目“百家讲坛”中讲解通俗文学的集大成者张恨水(《金粉世家》与家族小说);燕世超《张恨水论》这类专书也开始挖掘通俗文学家的价值。总之,通俗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
近些年,中国通俗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迅猛崛起,展示着强大的推动力,可谓大俗即大雅。通俗文学在雅文化的提炼整合与优化中,变俗为雅,雅文化也在俗文化中注入一些通俗的成分,使之更加贴近群众,靠近雅俗共赏。雅文化的俗化,不是指文化朝着“粗俗化”方向发展,而是一种文化的下移与普及,因俗成雅。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经典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将束之高阁的文学搬上银屏,走进千家万户,老少共赏;本属于上层人士消遣的台球、桥牌等娱乐形式也在悄然改变,逐渐平民化;高深复杂的专业化知识借助漫画或其他明白晓畅的形式,从而普及大众,这些都是当下雅文化俗化的表现。
反之,俗文化的雅化,则是一种变信息为知识的过程,一种文化的上移与精化。例如,孔子的《六经》在当时只是一个通俗的文本,经过后人的整理与阐释才成为经典;宋词原先是流行于歌肆酒店的小夜曲,经过柳永、苏轼等大家的创新才变俗为雅;黄梅戏当初也只是民间小调,经过螺旋式的创编发变,逐渐成为中华国粹;历史上的文字,由最初的象形文字简化到现代的文字,也是一种变俗为雅;历史上的谚语也是对历代经典段子的解构,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话语;甚至钱理群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相对以前文学史,花大量笔墨来描述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俗文化的雅化。
随着时代背景和文学观念的改变,通俗文学在众声喧哗中逐渐兴盛起来,原有的文学观念发生改变,新的文学观念在慢慢诞生,这是时代的发展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在文学上的反映。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同时又高于生活,它可以帮助我们看见继而审视现实背面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生活,既让我们仰视头顶上无穷的星空,又让我们望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它最终追求的是真善美这一来自“人”最本初的情怀,也是最终极的关怀。在当下,我们应该认真审视我们的文学体裁的原始形态,抛开文学精英化的思考模式,回过头去重新解读文学的原典和经典。我们不仅需要文学知识,更需要人文素养。
注释
①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②③⑤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第70页,第247页。
④黄高锋:《文学经典视角下的中国抗战文学评价》,《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1期。
[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
[4]黄力之.“唯洋是从”的西化思维之历史终结[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1).
作 者:
胡 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编 辑:
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