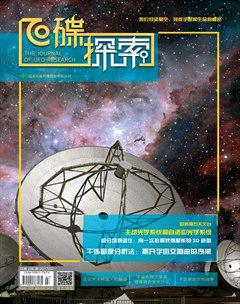子宫里发生的战争
苏珊·萨德丁+晨飞
有什么场景能比母亲给自己的婴儿哺乳更加动人?谁能给爱、亲密和无尽的付出找到更好的偶像?《圣母和圣婴》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符号之一,是有其原因的。
要想看到母亲宽宏大量的精神在逻辑上达到极致,那么就想一想澳大利亚的一种狩蛛属食母蛛。母蜘蛛整个夏天都在捕食昆虫以便把自己养肥,这样到了冬天,她便能让自己的小宝宝从自己的大腿跟关节处吸食血液。小蜘蛛不断地吸食母亲的血,母亲渐渐虚弱,最后小蜘蛛一拥而上,把毒液注入母亲体内,像吞食其他猎物一样将母亲吃掉。
你可能觉得哺乳动物的幼崽哪里能如此残酷无情,绝对闻所未闻。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错了。并非我们的宝宝没有食母蛛那么残忍,而是我们的母亲没有那么慷慨。哺乳动物母亲的付出是有限的,她努力阻止自己的孩子得到过分的要求。孩子们却通过操纵、敲诈和暴力进行反抗。他们的凶残在母亲的子宫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它与经久不衰的母性文化理念不协调。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常常听医生说,子宫内膜是养育胚胎的“最佳环境”。但是生理学很久以来对这一浪漫看法持怀疑态度。
人类子宮内膜里的细胞紧紧地排在一起,围绕子宫内部形成一个堡垒般的护壁。这道护壁里面还有致命的免疫细胞。早在1903年,研究人员就已经观察到胚胎一边“攻击前进”,一边“吞食消化”子宫内膜。1914年,R.W.约翰斯通描述了卵子着床区,称其为“母体细胞和入侵的滋养层细胞之间发生冲突的战线”。战场上“……双方尸横遍野”。
科学家曾试图在子宫外培养老鼠胚胎,他们预期这些胚胎会萎缩,因为它失去了通过进化来滋养胚胎的表层。可是他们吃惊地发现:植入老鼠大脑、睾丸或眼睛的胚胎狂虐无阻。胎盘细胞在周边组织中横冲直撞,杀开一条血路,搜寻动脉以满足吸收营养的欲望。胚胎发育中活跃着的相同基因许多都与癌症有牵连,这绝不是偶然。其实妊娠很像战争,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那么,如果是一场战争,是什么引发的这场战争呢?其中的关键就在这里:你和自己最亲的亲属的基因不完全相同。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这就意味着你们在竞争。而且因为你们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所以最亲的亲属实际上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特里弗斯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力的论文,首次大胆地探索了这个现实的邪恶性。此后的10年里,一位名叫大卫·海格的在职研究生思考了特里弗斯的这些想法,他意识到,哺乳动物母亲的孕育行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利用机会。
海格这样理解:你的母亲的基因对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提供等量的营养,这是符合母亲利益的。但是你的父亲与她可能不会再有更多的孩子。这使得母亲的其他孩子成为你的直接竞争对手,同时也让你的父亲的基因有理由在孕育系统中搏一把。他的基因组会想法操纵你的母亲为你提供更多资源。反过来,你的母亲的基因会想方设法让你的资源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就成了拔河比赛。一些基因陷入沉默,其他基因更加活跃,形成平衡局面。
这一观点引导海格创立了基因组印记理论,解释有些基因如何根据来自你的父亲或母亲而进行不同的表达。用这种理论武装我们自己,就能发现父母之间基因利益的冲突是怎样在他们后代的基因组中继续下去的。
父母双方的基因组都会驱使对方不停地加速分泌强效激素,所以万一一方基因失败,对母亲和胎儿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只要父母的基因型正确地互相平衡,正常发育就能进行。就像一场拔河比赛,如果一方扔掉他那一端,双方都会跌倒。这就是哺乳动物不能无性繁殖以及克隆哺乳动物如此困难的一个原因:哺乳动物的发育需要父母双方基因组错综复杂的协作。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当然,狩蛛属食母蛛的母蜘蛛不用担心这个。她不会有第二次繁殖,所以无须限制自己的后代。但是大多数雌性哺乳动物繁殖不止一次,而且有可能是与不同的雄性动物进行繁殖。仅此事实就造成了父母双方基因组相互对抗。你可以看到贯穿哺乳纲的这场隐秘战争所带来的悲剧后果。然而,哺乳纲中只有一个物种能够达到真正骇人的血腥程度。
这就是我们人。
对多数哺乳动物来说,即使有潜在的冲突,妊娠期间生命还是几乎正常进行的。它们逃避猎食者,捕获猎物,建立家庭,防守领地,与此同时妊娠也进行着。就连分娩也相当安全:它们在分娩过程中可能会表露痛苦或流汗,但这通常是最糟糕的。例外也有。例如,母鬣狗下崽是通过一个不好使的阳物状结构,所以大约18%的小鬣狗会在其母亲第一次分娩时夭折。但就算是鬣狗,妊娠本身也极少有危险。
看看灵长类动物,那情形就不一样了。灵长类胚胎有时会在输卵管而不是子宫内着床。这种情况发生时,胚胎会凶残地挖开一条通道,竭力寻找最丰富的营养源,结果常常是“血腥屠杀”。在类人猿中,情况更危险。这里我们就开始看到也许最凶险的妊娠并发症:子痫前期,其特点是一种神秘的情况,即高血压和尿中的蛋白排放。子痫前期造成全球大约12%的孕产妇死亡。但这还仅仅是我们人类问题的肇始。
在折磨人类的一系列生殖疾病当中,首先可能就是胎盘早剥、妊娠剧吐、孕期糖尿病、胆汁阻塞以及流产……后面还有很多。妇女每次怀孕期间总共有约15%会得上威胁生命的并发症。靠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妇女在没有医疗的条件下,40%以上都活不到绝经期。即使有现代医学的帮助,现在全世界每天仍然大约有800名妇女因妊娠丧命。
所以,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点解不开的谜。这场让子宫变成战区的基础基因冲突在无数物种中萌芽:要让战争爆发,只待母亲与不同父亲生下不同后代便可。但是,这在大自然中是一种常见的繁殖格局,正如我们所见,这不会给其他哺乳动物带来如此多的问题。我们人类为何如此不幸呢?这与我们其他非同寻常的特征有关系吗?比如说我们那无与伦比的大脑发育?
在多数哺乳动物种群中,母亲的血液供给与胎儿保持隔离以保证安全。母亲通过一个过滤组织向胎儿传送营养,这个过程由母亲控制。母亲是一位暴君:她愿意提供什么就只提供什么,这使得她在妊娠期总体上不受父亲一方的操控。
在灵长类动物和老鼠中,那是另外一回事。侵入的胎盘上的细胞一路消化掉子宫内膜的表层,刺穿母亲的动脉壁,一拥而入,把动脉血管改造成适合胎儿的场所。在妊娠期之外,这些动脉微小、扭曲,呈螺旋状分布在子宫壁的深处。入侵的胎盘细胞使这些血管变得麻痹,因而无法收缩,然后给它们注满生长激素,使其体积扩大10倍以获得更多的母血。这类胚胎细胞具有强大的侵略性,它们成群结队,常常会在母亲的余生继续存活,迁移到母亲的肝脏、大脑以及其他器官里。关于母性,有件事几乎没人告诉你:它把女人变成了基因嵌合体。
也许这种巨量的血液供给能解释为何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会比普通哺乳动物的大脑大5倍至10倍。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说,大脑是极为昂贵的器官,其发育大部分在出生前便已完成。要不然胚胎又如何供应这么奢侈的需求呢?
既然妊娠具有侵略性,那么灵长类动物的子宫已进化出提防这一特性的机制就不足为奇了。有些哺乳动物如果胎盘不在子宫壁上破口,它们可以在妊娠的任何阶段流产或者再吸收不想要的胚胎。对灵长类动物来说,如果要这样折腾就会有出血的危险,因为胎盘是从母体增大的、麻痹的动脉系统剥离。一句话,流产很危险,原因就在这里。
这也是为何灵长类动物要想方设法考验胚胎,然后才允许它植入其体内。胚胎被那层紧密包裹子宫内膜的细胞挡在外面,这时候,便发生了一场亲密的激素对话。用海格的话来讲,这场对话就是一次“工作面试”。如果胚胎不能说服母体相信自己是一个完全正常和健康的个体,那么它就会遭到果断驱逐。
那么胚胎是怎样说服母体, 让她相信自己是健康的呢?那就得真诚地展示它的活力和对生命的渴求,也就是说,不遗余力地在子宫内着床。那么母体又是怎样考验这个胚胎的呢?就是讓胚胎的着床任务困难得让人无法相信。胎盘经过演变逐渐具有攻击性和入侵性;与此同时,子宫内膜也逐渐变得强韧和充满敌意。对人类来说,这样对峙的结果便是人类的妊娠成败各半,败者大多数在着床阶段,时间很早,所以母亲竟然都没有察觉自己怀孕。
胚胎发育成为角力。这便造成了灵长类生殖系统的又一个奇特之处——月经。人类有月经,原因很简单:要想摆脱一个不断战斗想活下来的胚胎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子宫内膜的组织有一部分与母体的血流是隔离开的,这样可以保护母亲的血液循环系统不受她还没有决定要留下的胎盘的入侵。但是这也意味着,她自己的激素信号要想在子宫里获得呼应也得经过一番挣扎才行。所以,如果不想冒险破坏子宫内膜组织、与胚胎进行持久战,母体该怎么办呢?她在每次月经后把整个子宫内膜全部抛弃。这样,即使是最具攻击性的胚胎也不得不获得母体同意,才能舒舒服服地待下去。如果没有健康胚胎的那种持续、有活力的激素信号传送,整个系统就会自行毁灭。大约30%的妊娠以此方式终结。
我说过,母体要努力把激素信号传入子宫。其实,一旦胚胎在子宫着床,它就可以完全进入母体组织。这种非对称性意味着两种情况。首先,母亲再也无法控制她给胎儿提供的营养供给——减少营养供给,她对自身组织的供给必然会受影响。我们在幼年灵长类动物身上看到的不同寻常的大脑发育,其关键原因是其对母亲血液毫无限制的获取吗?有趣的是,胚胎入侵的强度确实和大脑发育相互关联。类人猿是大脑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它们受到的母体动脉入侵要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深入、更广泛。人类在所有猿类中大脑最大,其胎盘细胞入侵母体血流的时间甚至比其他类人猿都要早,使得胚胎在早期发育中对氧和营养物的获得达到空前地步。这会是进化带来的一个小小的讽刺:要不是我们这个很大的大脑赋予我们认知和社交能力,我们当中可能有更多的人不会在残忍严苛的人类生殖周期中幸存下去。可以想象,这两个性状可能是同时产生的。但是这种联系仍然是推测。子宫一般不会变成化石,所以胎盘进化的各种细节我们无从得知。
胚胎直接获取母体营养物质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胚胎还可向母体血液中释放自己的激素,以此操控母体,而且它的目的也达到了。当然,母体也通过自己的操控进行对抗。但是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虽然胚胎可以向母亲血液中自由地注入自己的激素,而母亲却无法进入胎儿的循环系统。她被胎盘膜包围起来,这样她的反应就被限制在防御性地调控自己体内的激素水平。
随着孕期继续,胚胎也增加了自己的激素分泌,释放信号增加母亲的血糖和血压,因此也增加了自己的资源供给。胚胎还会增加一种特别激素的分泌,刺激母亲大脑释放出皮质醇,这是主要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抑制了母亲的免疫系统,使其停止攻击胚胎。更为重要的是,皮质醇还升高了她的血压,因此更多的血液涌向胎盘,结果胚胎就可得到更多的营养物质。
母亲也不会任由这个胚胎操控而无所作为。事实上,她先发制人,降低自己的血糖水平。并释放出一种与胚胎激素捆绑在一起的蛋白质,使其失去效果。所以胚胎还得继续增加它的激素分泌。到了8个月大的时候,胎儿预计要花掉每日蛋白质摄入量的25%,以制造这些激素信息来控制母体。那么,母亲对此又如何回应呢?她也增加了自己的激素分泌,用自己的激素降低血压和血糖水平,以对抗胎儿的激素操控。通过所有这些操控和相互报复,大多数情况下胚胎最终都能基本上获得足够的血液和糖分,使其在出生前长得健康丰满。这便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证实了海格所说的父母基因组之间的拔河比赛。只要双方都抓住绳子不松手,谁也不会受伤。
可是,如果出现差错会怎么样?自千禧年到来之后,人类基因组计划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但是其中有很多我们仍然不能理解。但是,通过搜寻基因组印记的标志,即取决于基因从父而来还是从母而来的不同基因表达,研究人员已经能够确定妊娠期和童年期的许多疾病的遗传致病因素。基因组印记以及幕后的母胎大战已经表明它们是造成孕期糖尿病、普拉德- 威利综合征、安格尔曼综合征、小儿肥胖症以及几种癌症的病因。研究人员怀疑,基因组印记可能也是某
些毁灭性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和自闭症)的病因。2000年,伊恩·莫里森及其同事编制了一个基因库,里面有40多个印记基因。这一数字到2005年翻了一番;截至2010年,几乎又翻了一番。识别基因机制本身并不会为治愈这些复杂疾病提供什么疗法,但它是找到一种有效疗法的关键一步。
子痫前期也许是妊娠期疾病中最神秘的一种,它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可以借此研究进化图、遗传图和医疗图如何排列组合。20多年前,海格曾推测该病是由母亲和胎儿之间的交流发生故障所致。1998年,詹妮·格雷夫斯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推测子痫前期的发病原理可能是母系遗传基因印记失败。然而,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才对此过程的产生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
所以,想象一下胚胎凿开一条隧道进入母亲血流的场景。在其他生理状态平等的情况下,妊娠早期的动脉扩张会导致母亲的血压降低。胚胎的激素又通过升高母亲的血压而平衡此效应。
妊娠早期的母体动脉扩张时,就卷入了一些激素。如果这些化学物质失去平衡,母亲的动脉就无法扩张,胎儿就会缺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胎儿有时便会采取更极端的措施:释放毒素破坏并压缩母亲的血管,迫使血压升高。这即使不导致中风,也会有损伤肾脏和肝脏的风险,而这些都是子痫前期的症状。
2009年,研究人员发现母系遗传基因H19与该病有紧密关联。这正与詹妮·格雷夫斯预测的一致。已知H19在胎盘的早期生长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其他一些母系遗传基因和某些父系遗传基因的改变似乎都与该病病因相关。许许多多致病基因还有待人们去发现,但这个故事表明,在进化论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开始理解既残忍又错综复杂的人类孕育过程。
我们人类的巨大脑袋以及痛苦的妊娠过程之间似乎紧密联系;两者至少都是人类的非凡特征。古人创造他们的神话时,有没有想到过这种联系呢?夏娃“吃了智慧之树上的果子”,上帝诅咒她要承受怀孕带来的痛苦,她的故事也许就是古人的一种直觉,以此解释大自然觉得让人类受苦理所应当。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减少妊娠带来的危险和痛苦,唯一的途径就是“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