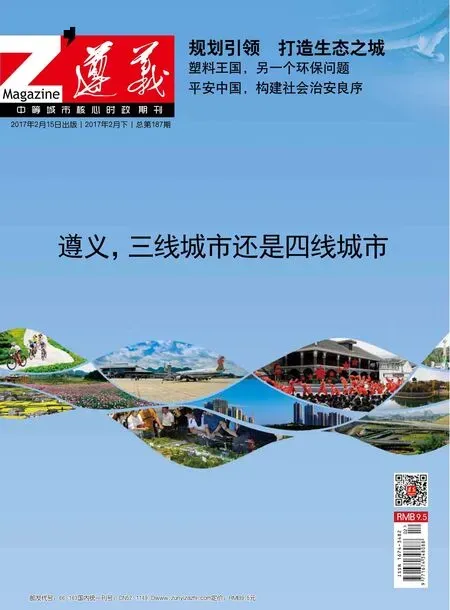塑料王国,另一个环保问题
■丨李 碧
塑料王国,另一个环保问题
■丨李 碧
人类在享受物质消费时,留下的是垃圾和污染。王久良通过拍摄垃圾,来解读繁荣背后的中国,追溯出口垃圾的国家,发现了一个被物质裹挟的世界。垃圾王国也好,“塑料王国”也罢,都是真实写照。以此为镜,才能在创新求变中突破自我,并因之鉴照历史,反思现实和憧憬未来。

曾因《垃圾围城》系列纪录片引发关注的摄影师王久良,历时三年又出新作《塑料王国》。该纪录片披露了各国废旧塑料进口到中国后,被以粗放的方式进行回收处理,继而引发了部分地方环境严重污染的现实。
其实早在去年12月,这部纪录片已经在各类网站、社交媒体传播,其中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等在12月初时采访该片导演并连续刊发相关报道。
2016年11月24日,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这部由中国导演王久良执导的纪录片《塑料王国》在新晋纪录片竞赛单元(First Appearance)获得评委会特别奖。
评委会给《塑料王国》的授奖词中特意提到,“作品具有宏大又专注的献身精神,以贴近常人的故事揭示了一个事关全球的现象。我们在两个家庭谋生发展的故事中发现了自己的身影,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对经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他们那令人心碎的境遇中留下的痕迹。”随着片子获奖后,在国内也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和讨论。微博、豆瓣、各类影评公众号都竭力推荐,豆瓣评分高达9.5,甚至有网友在豆瓣影评中这样评价,“国产电影五星运动”,“人民日报你看,我给国产电影打了五星”。据导演王久良介绍,“从2011年就已经开始做《塑料王国》,到2014年底发布了一个28分钟的媒体版短片,短片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媒体陈述塑料产业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短片大致勾勒出废旧塑料回收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遍布大半个中国,废旧塑料通过各种通路入境,“广西的是通过越南的内陆河进来的。甘肃的是通过内陆,就是所谓的陆上丝绸之路到新疆,再到甘肃。”
“而此次获奖的纪录长片《塑料王国》可以说是一个故事(长达81分钟),产业状况则变成了人物故事的一个大背景。”王久良称,《塑料王国》这部片子,是对“外国垃圾在中国的处理”这一基本事实的深度调查。调查结果最终也会以图文和视频的多种形式对外发布,而不仅仅是为了创作一部纪录长片。这个项目整体来说新闻性很强,但是对于纪录片来说,电影的艺术性也很重要,他也一直遵守其创作准则。
《塑料王国》不是导演王久良第一次拍“垃圾”,2010年他曾拍过一部《垃圾围城》。只不过,《垃圾围城》讲述了北京周边垃圾污染的状况,而《塑料王国》呈现的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塑料垃圾在中国处理的情况。摄影师王久良曾经被故乡田野间遍布的垃圾刺痛过,在文化学者鲍昆的帮助下,他开始了环境领域题材的创作。
垃圾与塑料
2011年到访美国,王久良参观当地的垃圾回收企业,他惊叹于这其中机械化高效的作业方式。但在参观行将结束的时候,负责人指着院子里的一个集装箱说:“那都是运到你们中国的。”金属、玻璃这类垃圾太重,就留在本土处理。而成吨的废旧纸张、塑料,则即将开始越洋之旅。
新的课题由此确定。
当王久良开始搜罗相关信息时,依姐和家人已经在陈峰的废旧塑料加工厂度过了一年的时光,这片沿海地区有30年废旧塑料加工的历史,爆发式的发展则在上世纪90年代,几千家与此有关的企业密布乡镇。
依姐的故乡在四川西南部的群山中,自爷爷那辈从邻省迁居到这里。依姐的父亲自幼成了孤儿,18岁那年就已经有了在外闯荡的经历。
后来他回到故乡成家,接连诞生包括依姐在内的三个儿女,可生活也日渐窘迫。那年家里本就不多的几亩地又遭了雹灾,出外讨生活再次成为了依姐父亲的选择。
不少乡邻都在陈峰工厂的那片区域打工,依姐的父亲也被介绍了过去。尽管不知道将要做些什么,但走得依然坚决,“把房门一锁,带着家里人就离开了。”
在陈峰的院子里,依姐和弟弟们继续着自己的童年。两家人吃住在一起,两家孩子也成了要好的朋友,依姐的弟弟阿泽还由陈峰母亲教会了普通话。
像周围其他院子里一样,都重复着相同的工序,依姐的父母每天分拣着成堆来自异国的垃圾,手边备着个打火机,有时还要点火烧灼,靠飘起的烟雾判断塑料种类。
之后需要机械操作的步骤多由陈峰夫妇进行,被挑选出来可用的废旧塑料经过漂洗后粉碎,继而加热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业使用的颗粒。
拍《塑料王国》时,网上的信息很少,只能自己去实地看。很多时候,没有得到政府机构的支持,像是讨人厌的苍蝇一样,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工作。
他经常被地方政府阻挠,甚至也被抓过,但真正的阻碍力量,真正让他感触特别深的是,这样一个肮脏的环境,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伤害,但他发现,阻碍他的,不仅仅是官方阻力,还有地痞流氓,而是任何一个当地的人,他们变成一伙,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个骨子里的愚昧让我触动非常大。
虽然拍纪录片需要跟他们在一起很长时间,本以为可以建立起很好的情感,但我无法建立起来,说实话我不喜欢里面的每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很痛苦。
对于分拣工人来说,因为废旧塑料里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他们所处的环境真的气味很难闻,影片里有人描述常年闻着都麻木了,闻不出味道了。但更主要的还是危险,垃圾有很多有毒有害甚至腐蚀性的危险品,有个老太太不懂外文,打开一个塑料瓶,其实里面是氢氟酸,结果把关节都烧坏了。有的人抖塑料布,抖了半小时,整个手都脱了一层皮。对于分拣工人来说,碰到有毒腐蚀的东西是经常的事。
对于水洗来说,还对整个产业区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首先是地表水的污染,几乎所有的池塘河流都重度污染,水草都不生了,更别说鱼了,当地人都不敢用地表水浇灌农业,曾经有人用河水浇灌玉米地,结果玉米全死了。
其次是地下水,像河北、山东的废塑料产业中心,人们从十几年前就不喝地下水了,不管有钱没钱,全都自己买水喝。
最后还有空气污染,焚烧废塑料产生巨量的废气,影响了整个区域。有一个采访的女老板在影片里说,我都不敢要孩子,孩子都是在干这活以前要的。我去过几个大型塑料产业基地,当地人都说,我们这儿的癌症挂号是整个地区里出了名的。我曾经问一个阿姨,这边生病的人多不多,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谁家生病了,而是谁家没人生病。
院里两家人
王久良想离以废旧塑料为生的人们更近些,走进他们的生活,看看他们所追求的价值。
在寻找人和故事的过程中,陈峰、依姐两家人并非最初的拍摄对象。王久良已经跟拍隔壁村镇一个厂主一年的时间,厂主靠着废旧塑料加工的生意供养着在读研究生的女儿。
但因为当地“不可抗的因素”,拍摄被迫中止,王久良甚至和厂主无法见面。“一年的时间,别人很难理解这种沮丧。”
初见依姐和陈峰两家人时,并没有拍摄所需的信任。王久良只被允许在厂子外面和依姐的父亲交谈,他被当成了“人贩子”,依姐紧张地盯着父亲背上的小妹妹。
证明自己的身份、解释拍摄的初衷,王久良花了半年时间和两家人熟悉起来。他成了依姐很好的玩伴,陈峰家搬运垃圾的帮手。
对镜头的躲闪慢慢消失,院子里的人们不再避讳将自己与废旧塑料为伴的生活展现出来。
陈峰的儿子举着垃圾堆里的英文图册,大喊着:“这里是美国。”依姐把包装纸上的卡通人物剪下来,再用塑料壳当“键盘”,做成了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而总能找到的塑料注射器,则成了依姐弟弟妹妹们最不愿撒手的玩具。

漫画《围城》(徐骏/图)
垃圾堆里一瓶还没开封的药膏成了陈峰的新发现,他比对着英文说明,在网上查找使用方法,之后把药膏涂抹在妻子因废旧塑料过敏的脚上。
陈峰的妻子中专毕业,曾经也在公司里上班。她很直接地表述着对粉碎塑料时烟尘的反感,如果更早进入这个行当,自己是不会选择怀孕的。
但院子里的日子,依姐家依然延续着新生命的诞生,妈妈在垃圾堆旁生下了自己的第四和第五个孩子。听到婴儿的哭声,赤膊穿着短裤的陈峰兴奋地跑出来观瞧。十天之后,还是在垃圾堆旁,趁着分拣垃圾的间隙,依姐妈妈哺乳着那个还粉嫩的新生儿。
在这个并不体面的环境里,院子里的人们不停歇地劳作,王久良觉得已经失去了探讨废旧塑料产业利弊的意义。“有些话说出来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陈峰一直想买辆轿车,上网一查,废旧塑料生意攒下来的积蓄还不够10万元的车型。后来他倾尽一年加工塑料的积蓄,才买回了一辆二手轿车。
陈峰开车回家的路上,路旁正有人将无法加工的垃圾燃烧,浓烟升腾而上。王久良的镜头拍下了这一幕,他好像看到了一个悖论,在追求美好的同时丧失了美好。
两家人都希望在废旧塑料加工的营生里改变生活,但境遇不同,分歧也由此而来。
一次陈峰大声斥责依姐的父亲,进而动起手来。起因是依姐的父亲在分拣垃圾时不大认真,将可供加工的塑料白白地丢掉了。
“我不可能像你妈妈挑的那么仔细。”依姐的父亲也有着自己的抱怨,在领取报酬时,他还会表达出能多些收入的愿望。
另一纷争则来自依姐的教育问题,面对着王久良的镜头,依姐早早袒露了想回家上学的心愿。在陈峰送自己儿子入学那天,也看出了依姐的心思,想带她一起去学校看看。但这遭到了依姐父亲坚决的阻拦,两个男人吵了起来,陈峰拉起依姐要走,小女孩看着父亲一脸怒色,缩回了自己的步子。
王久良知道陈峰是一片好意,也更理解依姐的爸爸。如果无力完成女儿的心愿却由别人“代劳”,一个父亲的尊严将就此崩塌。那天晚上依姐的父亲哭着闷下口酒,“穷人家的孩子聪明、懂事,就是没上过学,我也没有办法。”
过了一段时间,陈峰还是带依姐去了学校。那天正好是文艺演出的日子,看着台上唱唱跳跳的儿子,陈峰也哭了,依姐的眼里则满是茫然。
随着和王久良越来越亲近,依姐把回家上学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希望能帮着劝劝父亲。每当和父亲说起这个话题时,她开始不住地向王久良使着眼色。
王久良曾希望在自己的镜头下,能出现一个关于依姐上学波折的故事,一年过去,他发现单靠依姐父亲的决断,这个愿望已不大可能实现。
“外出打工后,老家的房子已经破败”“回去了意味着经济压力的增加”,依姐的父亲不缺少返乡艰难的理由。王久良不得已介入到了镜头下的这个故事里。他坚决地说“孩子上学的事没得商量”,并在和制片方商量后决定给依姐的教育提供资助。
在《塑料王国》最后的成片里,没有出现“污染”两个字。王久良相信,当人们看到依姐捧起漂洗塑料的污水洗脸时,一切自会明了。
问题如何解决
片中的场景令人无比纠结,在国外被弃之不用的废旧塑料,进入中国后被以粗放的方式回收处理,结果引发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并最终损害公众的健康。塑料制品的利润率之低与环境污染的代价之大,两者之间无以匹配。然而由于“塑料王国”的巨大产业链条,解决了很多底层人员的生计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从寻求经济指标的地方政府,到为谋生路的从业者,再到追求暴利的地痞流氓,使得寻求改变极其不易,取缔既需要很大的决心,更无以实现从根本上的治理。
即便是作为生产玩具的主要原料,依然无法改变低端产业的现状。“8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中国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真实体现。全国人大代表、攀枝花市市长张剡曾举列说,“一些国外企业买走钛原料,又把高附加值的钛产品卖到中国。我们付出极高的开采成本,得到的却是极低的收益”。2013年,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代工厂为了抢生意,加工利润低到每台2分钱也都肯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别人吃技术,我们靠力气,别人玩资本,我们玩力气,结果我们牺牲了环境,耗费了资源,却获得很少的利润。如果不改变这样的状况,那么在路径依赖之下,中国的发展方式就很难谈得上转型。
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然而在发展质量上,却还是建立在代加工、粗加工和钢筋水泥的基础上。如果“塑料王国”不断延伸其利益链,那么“垃圾围城”的状况就会日益严重,而由此牺牲的环境和健康代价,恐怕将会成为未来前进的最大包袱。时下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引进垃圾和塑料,而是让更多的高铁技术、航天技术、互联网技术和新型技术走出去。
因而创新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当前无以回避的选择。改变“塑料王国”的困局需要有危机意识,更要有创新意识。拍摄这样一部作品,让我们在窥视一个行业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除了心灵的震撼与恐惧之外,更应当内化成奋起直追的行动。事实证明,“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已然难以为继,当我们的空气、水和土壤质量越来越差,环境的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时,自然与环境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然不多。要从根本上消除“塑料王国”的标签,转型和提质是不贰的选择,也是“新常态”最直接的要求。
我们不输出垃圾,但我们也不应引进垃圾,更不该制造垃圾。垃圾王国也好,“塑料王国”也罢,都是真实写照。以此为镜,才能在创新求变中突破自我,并因之鉴照历史,反思现实和憧憬未来。
盘点国外垃圾处理经验
我们无法回避垃圾的出现,它与人类社会发展如影随形。而垃圾越来越多以至围城,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垃圾?“一埋了之”注定难以为继。垃圾处理水平已成为体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其他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都面临着“垃圾围城”的难题,他们的破解应对之道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法国:垃圾回收“两大法宝”。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垃圾越来越让全世界的管理者头疼。如何减轻污染、变废为宝,法国自有“两大法宝”,这就是垃圾回收和低污染处理。
根据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一份报告,法国生活垃圾的回收量呈上升趋势,但仍有提高的空间。为此,一些地方利用经济杠杆鼓励公众少扔垃圾,比如根据垃圾数量收取一定比例费用,多扔垃圾多付费等。另外,法国政府还提倡良好的消费习惯,控制资源浪费,并通过政府干预推动垃圾回收新技术的开发。
对于不可回收的垃圾,法国则采取低污染处理。如位于巴黎郊区伊夫里的垃圾焚烧中心,每年可处理73万吨垃圾,但它的过人之处还不仅在于它的规模,更在于它降低污染的能力和变废为宝的“本领”。为减少污染,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雾需经层层净化才能排放到空气中,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则不仅可为附近家庭供暖,而且可转换成电力,在保证焚烧中心用电“自给自足”的前提下,还可将多余电力卖给法国电力公司。至于焚烧后的废铁和炉渣,它们也会被运到回收中心“废物利用”。
日本:从源头控制垃圾生成量。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东京都23区的人口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但是城市产生的垃圾和最终被填埋处理的垃圾却逐年减少。那么,东京的人口没有减少,而垃圾为何会越来越少呢?
首先,法律约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源头控制住了垃圾的生成量。
日本有较为完善的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如确保社会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还有关于恰当处理废弃物的《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以及《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家电再生利用法》《食品再生利用法》《汽车再生利用法》等。在这些法律约束下,日本国民均按照有关规定,进行“3R”实践,从源头上有效减少了垃圾的生成量。
“3R”是减少、再利用、循环3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核心意思是尽可能不购买和使用容易产生大量垃圾的物品,尽可能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不轻易抛弃,并尽可能使物品再生利用。与此同时,东京都还实行严格的定时、分类投放垃圾的制度,有效控制了垃圾的二次污染。
其次是注重资源回收,使垃圾总量减少。
日本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可再生资源要进行分类回收。除此之外,废旧家具、自行车等被称为粗大垃圾的东西会送入“粗大垃圾破碎设施”,陶瓷、碎玻璃等不可燃垃圾会被送到“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之后,工人首先要将其中的铁、铝等可再利用资源挑选出来,然后才将剩余的垃圾进行焚烧和填埋,这是垃圾总量减少的又一个原因。
韩国:垃圾“减肥”靠收费。韩国从2005年起实行厨余垃圾和一般垃圾分类处理。2010年,一些地方开始对食物垃圾按量收费。
不少家庭主妇为节省垃圾处理费,会先把垃圾中的水漏干再放入袋中。另外,在韩国,盛放厨余垃圾的垃圾袋需居民自行购买。这些成本因素刺激了韩国人为垃圾“减肥”的积极性。
此外,韩国市政管理当局对扔垃圾的时间也有严格规定,小区每周一、三、五晚7时至9时为收垃圾时间。若没有使用规定的袋子或不按规定时间扔垃圾,居民将被处以100万韩元(约合986美元)以下的罚款。
美国:“3R”原则效益多在美国,人们熟知的所谓“3R”原则,也即减少(Reduce)、再利用(Reuse)、回收(Recycle)。除做好垃圾分类外,在美国,还有很多垃圾不能随意丢弃。
要扔旧家具,至少提前一天与指定收取机构电话预约回收日期,届时将旧家具放在家门前,会有专人收取。要扔电子产品,需送到专门回收中心,或预约专人上门回收。要扔电池等有害废物,可以上网找到离家最近的回收点,有时还能从中得到返现,比如每加仑废机油可以获得40美分。
被称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逐渐深入公民的生活。政府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除了在街道两旁设立分类垃圾桶以外,每个社区都定期派专人负责清运各户分类出的垃圾。在纽约,垃圾处理被称为“垃圾管理”。只要在大街上走一趟,就可以看到马路的两旁堆放着一些黑色或深褐色的垃圾集装箱,上面写着:垃圾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