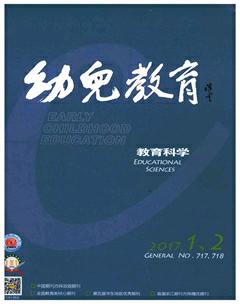幼儿园在儿童保护中的缺位及其改进策略
谢娜++蔡迎旗

【摘要】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儿童享有受保护的权利,其四大责任主体分别为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机构。然而,现实中,一些幼儿园未尽保护之力,甚至还出现虐待儿童事件。针对幼儿园在儿童保护中的缺位现象,研究者认为,可借鉴西方国家相关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尝试从观念影响力、制度约束力、儿童自我保护力、联合监管力等方面入手,真正将儿童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关键词】儿童保护;幼儿园;儿童虐待
【中图分类号】G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7)1/2-0046-05
自20世纪以来,儿童道德地位和法律地位在儿童保护运动中得到迅速提升。然而,虐待儿童事件仍在世界范围内屡禁不止,儿童保护仍是一个在行动中尚未完成的社会使命。近年来,我国儿童遭受虐待的事件频频见诸媒体,已引发了全社会对施虐者的道德谴责和对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审思,但鲜有从幼儿园层面反思如何杜绝此类悲剧发生的研究。
一、“儿童保护”概念的法理解析
我国有关儿童保护的法律,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同时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义务教育法》《婚姻法》《刑法》等法律中。但已有法律并未阐释“儿童保护”的具体含义,因此,有学者依据相关法律对该概念进行了梳理。〔1〕
1.广义的“儿童保护”等同于“儿童权利保护”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条和第3条规定,儿童保护的内容包括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保护和合法权益的保障。其中,合法权益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等。因此,广义的儿童保护即保障儿童所有的权利。
2.狭义的“儿童保护”等同于“保障儿童的受保护权”
《儿童权利公约》首次明确规定儿童享有受保护的权利。该条约第19条第1款就儿童的受保护权作出规定:“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由此可见,狭义的儿童保护是指国家通过司法救济、社会救助和替代性养护等措施,对已受到或可能受到摧残、忽视、虐待、剥削及其他形式伤害的儿童提供的一系列救助和安全保护,以使儿童能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2〕
简言之,儿童保护即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确保儿童获得适当的照顾和监护,确保其免受身体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等伤害。本文所界定的儿童是指幼儿园阶段的学龄前儿童,即3~6岁儿童。本文采用狭义上的儿童保护概念。
二、幼儿园在儿童保护中的职责确立
1.幼儿园与儿童之间在法律上属于监护代理关系
要明确幼儿园具体职责,需厘清幼儿园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法理关系。《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员担任:(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者……”。由此可见,幼儿园并非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监护人必须履行有关未成年人的生存、健康、安全、生活、教育和保护等多方面职责,但仅靠监护人的力量仍无法满足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要求,因此,有必要委托专业人士或社会组织履行保护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確了学校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监护代理关系。该意见第22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这一法律条款,一方面明确了监护职责可以委托给学校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的两种情况,即部分委托和全部委托。由此可见,监护人可将监护职责中适于学校履行的部分委托给学校。学校也因此成为了学生的监护代理人。幼儿园作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是儿童的监护代理人。
2.幼儿园承担儿童保护的监护职责
幼儿园的性质决定了其无法代为管理未成年人财产、提供生存条件、代理未成年人诉讼与赔偿以及保障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与监护人共同居住等监护职责。目前,司法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是学校要承担教育、管理和保护等监护职责。〔3〕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按照责任主体将未成年人保护分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可见,作为学校组成部分的幼儿园,应承担儿童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即在保护儿童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可见,当幼儿园未尽到其应尽的监护职责时,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
三、幼儿园在儿童保护中的缺位表现
根据尤·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幼儿园是直接影响儿童成长的微观系统。然而,现实中,幼儿园未尽儿童保护之责,甚至还出现伤害儿童的事件。本文从近三年来媒体曝光的此类事件中,抽选“浙江温岭某幼儿园老师颜某虐童事件”“河北廊坊某幼儿园多名女童被性侵事件”和“陕西西安幼儿园‘喂药事件”三则案例,对其进行简要分析(详见下表)。
虽然从地域和数量来看,所选三则案例对我国儿童保护的现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但所选案例均发生在幼儿园,受害者均为儿童,受害人数少则12人,多达数百人,施虐时间最长达5年之久,其中涉及身体虐待、情感虐待、忽视等各种方式,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因此,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通过这三个案例,可以探究当前我国幼儿园在儿童保护中的缺位表现。
1.儿童保护权益意识淡漠
从三则案例不难发现,受社会期许承担保护儿童职责的幼儿园,会只因“幼儿不听话”或“保证出勤率”等理由而肆意虐待儿童身心,无视儿童的权益。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均有知情不报者,如“喂药”事件中,全体教师集体失语。且此类事件并非个案,近年来湖北、吉林、兰州等地也相继曝光了“幼儿园喂药”事件。这种集体性冷漠警示我们,儿童的受保护权未得到普遍关注,幼儿园维护儿童权益的意识淡漠。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教师应把保护幼儿生命和促进幼儿健康放在头等重要位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章第21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4〕儿童的身心健康是受法律保护的,幼儿园必须履行保护儿童的法定职责。师幼之间,不仅仅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从儿童权益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首先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儿童权益“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5〕
2.儿童保护的实践行为有偏差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规定:“儿童的最大利益应成为对儿童的教育和指导负有责任的人的指导原则”。此后,其他有关儿童保护的国际公约或国际文件均对此原则作出了回应,如《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适合儿童成长的世界》和《儿童权利公约》等均提出“在所有关于儿童的行动中,将儿童的最高利益作为首要考虑”。
从所选三则案例来看,弱小的儿童更多地被当作必须屈服于成人意志的被动者看待了,他们的需求让步于成人的需求,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优先保护的原则成了纸上空谈。三则案例均揭示出,当幼儿受到侵害时,幼儿园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对受到伤害的儿童给予积极关注和救助。至于儿童保护观念的宣传、方法的普及、制度的建设以及监督指导等方面,幼儿园更是无所作为或少有作为。
3.对儿童自我保护的教育不够
儿童缺乏自我保护和求助的意识与能力,通常,在教师的“威逼利诱”之下,他们也不敢告诉家长自己在幼儿园受到虐待的情况。加之儿童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如果家长不够细心,很难及时发现儿童受虐现象。这些原因的存在导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虐童事件的被发现往往出于偶然。儿童遭受虐待所产生的心理伤害虽说可能会暂时处于内隐状态,但其所带来的身体伤害却是可以显现的。但尽管如此,伤害行为仍持续了“2年”或“5年”之久,这足以说明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诉能力较为薄弱,更反映了幼儿园对儿童自我保护教育的失职。
4.儿童保护制度不健全
三则案例的发生过程中均有知情不报者,甚至出现“喂药”事件中的教师“集体不报”现象。这种有能力制止而不去制止,对儿童遭受生理或心理伤害未做出反应的,都是“忽视儿童”的行为,其实质也是一种虐待儿童的现象。
就目前我国儿童保护的实際情况看,大多属于事后补救型。虐童事件发生后,因为媒体曝光,才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最终导致警方介入。儿童保护体系本身缺乏一个具体可行的处理程序与干预机制,具体表现为:没有明确的主管机构,没有儿童受虐报告制度和儿童保护工作程序,儿童保护的相关法律也不够完善。司法部门对于那些没有造成受虐儿童重伤和死亡的案例“不告不理”,即使报告了也缺乏有效的干预和保护机制。〔6〕 “温岭颜某案”中,虐待儿童次数达百次,严重侵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然而,最终处理结果却只是“行政拘留数日”。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所言:“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虐童罪,无论怎么虐待儿童,都不会是虐待罪,因为虐待罪只适用于家庭。这使得我们在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尤其是虐待幼童犯罪时显得依据不足。”〔7〕
具体到幼儿园,也缺乏专门的儿童保护制度。幼儿园虽可能建立了相关的儿童安全责任制度,但并没有制定相关的监管制度和干预机制。加之我国尚无专管虐童事件的组织或部门,因此,很难实现对学校中儿童保护工作的日常监管。此外,幼儿园往往忽视或无视公众的知情权,对家长的质疑大多会采取拖延、隐瞒方法,从而导致家园合作纽带的断裂,甚至出现社会对幼儿园的信任危机。
四、幼儿园儿童保护的改进策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09年《儿童保护问题进展报告》中指出:“如果没有一个保护儿童的环境,儿童将面临更残酷的生活。” 毫无疑问,如果身陷问题幼儿园或问题家庭,儿童将面临更大风险。因此,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从源头上降低问题的发生率。本研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拟从幼儿园层面提出相关改进策略。
1.面向教师、幼儿和家长普及儿童保护法律知识,提高观念影响力
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因此,只有在观念上达成儿童保护的共识,才可能自觉履行保护儿童的职责,自发产生保护儿童的行为。要让观念深入人心,需要幼儿园有所作为,例如,可针对教师、幼儿和家长,从道德与法的角度,开展儿童权益保护的知识培训或讲座,制定宣传小手册,开展提高儿童自我保护意识的游戏或主题活动等。这些途径能快速提高人们的儿童保护意识。但观念的理解与认同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自我反思与学习。因此,可在教师职前、职后培训中增设儿童保护专题,就怎样识别儿童虐待、如何与儿童保护机构取得联系、幼儿园可采用何种具体措施去保护儿童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开展学习与讨论,从而促使教师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策略,进而提高教师保护儿童的自觉性和能力水平。
此外,要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践行优先保护儿童的观念。有学者建议,可将学前教育中的“保教并重”修改为“保育优先,教育其次”,〔8〕这一观点突显的是儿童保护的重要性。教师在设计和组织所有教育教学活动时,都不应有损儿童身心健康。当儿童出现身体不适或情绪低落状况时,教师要马上推迟或停止原计划的教学活动,设法帮助儿童回到舒适、快乐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幼儿园教育的根本价值。〔9〕
2.建立幼儿园保护制度,加大制度约束力
国外已有的儿童保护制度基本包括四大要素:国家指定的儿童保护机构、强制报告制度、专门针对儿童保护的案件处理程序和替代性的监护制度。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并不存在正式的儿童保护制度”。〔10〕在缺乏国家顶层制度设计的情况下,幼儿园难以构建严格意义上的儿童保护制度。但我们建议,可尽快就儿童保护问题,制定出一套具体可操作的监管制度或幼儿园行为准则,从而增强各方行为约束力。这个儿童保护监管制度应明确规定负责儿童保护事宜的部门及主管、虐待儿童行为的认定标准、事件报告及外界调查介入、问题解决方案、究责程序、奖惩办法等具体内容。此外,幼儿园的儿童保护制度必须公开,既要发挥制度具有的监督作用,又要使相关事件的处理有据可依。关于儿童保护监管制度的建设可适当借鉴美国的强制报告制度。该制度规定,凡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一旦发现有虐待儿童的行为发生,必须进行强制性举报。〔11〕其中规定的义务举报人有保育人员、教师、医生、法律顾问等。如果义务举报人知情不报,也将会被指控为犯罪。虽然我国目前还尚未实行强制报告制度,无法将“知情不报”行为定为犯罪,但幼儿园可以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来鼓励和约束义务举报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