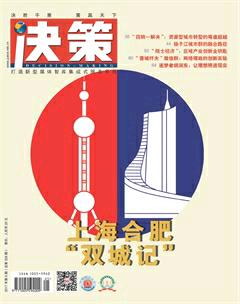国家治理中的时间弹性
杨雪冬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时间管理并非只有统一时间标准,划分工作阶段,明确最后期限等自上而下规定时间的方式,还需要各主体之间进行时间协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时间安排,保持时间管理的弹性。
社会分化和劳动分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在很大意义上,国家治理就是对分化的控制,对分工的协调,以使多元化的社会能够实现有效合作,保持良好秩序。时间管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理应起到协调不同主体的行为,提高行动的一致性,进而形成共同习惯和基本认识的作用。
但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时间管理并非只有统一时间标准,划分工作阶段,明确最后期限等自上而下规定时间的方式,还需要各主体之间进行时间协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时间安排,保持时间管理的弹性,这样才能实现意愿趋近,步调一致,行动整齐。否则,很容易会出现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问题,每个治理主体都制订出有利于自己行为或者符合上级偏好的时间表,但是相互之间缺乏协调。
最近经常出现的“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固然反映了一些部门和官员的不作为,消极懈怠,但也存在客观原因,单向度的时间管理就是原因之一。
这具体体现为:一是一些决策出台快、要求高,下级部门的理解认识能力、执行能力以及拥有的资源与实现的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决策的时间预期与执行的时间预期脱节;二是个别决策变化大,与原有政策没有连续、或者与现有政策系统之间联系弱,也会造成决策的时间预期与实际执行的时间预期脱节;三是中间层级的一些部门为了体现姿态,甚至撇清责任,忙于发通知,转文件,形成了政令信息传达中的“二传手”现象。
显然,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每个治理主体制订的看似精确无误、标准统一的时间表并不会自动生成一个严丝合缝、运转飞快的国家治理时间表,提高国家治理的整体效果,反而会出现时间表之间的脱节,时间分配的失衡以及时间进度上的造假。
正因为如此,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要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干,不能简单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不能纸上谈兵、光说不练。
但要解决时间管理中规范有余、协调和调整不足的问题,还是要回到现代分工这个基本前提下来思考对策。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治与行政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有自己不同的运行逻辑。政治强调忠诚,行政重在执行。而行政系统中各层级各部門,也有自己专门的工作对象,工作职责,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式。
基于此,更应该思考发挥关键少数作用与鼓励差异化探索在提高时间管理效果中如何具体落实。发挥好关键少数以上率下的作用,要更有效地发挥各级部门和官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要承认部门和层级的多样化,在保持政令统一和有效贯彻的前提下,确定具体目标时尊重地方的自主性,评价政策效果时避免衡量标准的单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