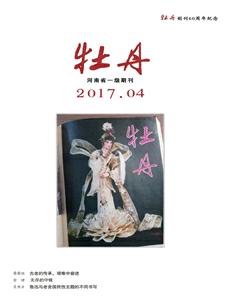鲁迅小说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孙乘风
鲁迅先生在小说《呐喊》《彷徨》中塑造了许多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了他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是“五四”觉醒者形象、妥协的知识分子形象、伪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魯迅笔下的这些形象背后蕴藏着迷失与救赎、疯狂与隐喻等复杂矛盾的心态,还包含着一定的文化逻辑。
鲁迅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但从现代小说而言,不外《呐喊》《彷徨》两部。中国现代小说,从鲁迅这里开始,又在鲁迅这里成熟。鲁迅一共创作了三十余篇小说,其中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包括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小说中,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都是鲁迅所描绘的“病态社会里不幸的人们”,而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不外乎:“一个是‘辛苦麻木的活着,一个是‘辛苦辗转的活着。”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小说《呐喊》《彷徨》中描写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和这些形象背后的文化逻辑。
一、知识分子形象的类型
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是“五四”觉醒者形象、妥协的知识分子形象、伪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一)“五四”觉醒者形象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场思想文化大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是这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锋。鲁迅先生对于知识分子现代性的理解,主要是受西方文艺及哲学思潮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对人的个性的尊重与倡导,对个人的价值、独特性、主体性的重视。鲁迅先生尤其强调人的独立自主性和社会批判性。具体体现在主张向内不依赖任何权势,向外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力量,在真理价值的认同上具备自己的判断水平,并遵循内心的准则自由地行动,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都是“铁屋子”里最先醒来并振臂疾呼的“圣斗士”。《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文著作。《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症的病人,狂人只因在二十年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就被众人认定为异端。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那个旧社会是一定会被推翻的,并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这过程可能会曲折艰难,可能会流血牺牲,但“铁屋子”终将被推倒,知识分子以及国人麻木的心灵都将醒来。
《药》中的夏瑜,是以“鉴湖女侠”秋瑾为原型的民主革命义士。夏瑜的抵抗是对清朝统治者的勇敢抵抗,又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的陈旧传统的摒弃。他为了苍生而捐躯,却不被贫困愚昧的老百姓理解,革命者的鲜血被视为治病的良药,让人唏嘘不已。
《长明灯》中的疯子可谓是狂人的继承人。《长明灯》写于1925年,1925年是中国历史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年代,帝国主义、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几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鲁迅仍“荷戟独彷徨”,在此背景下写下了《长明灯》。疯子住在吉光屯,屯中神庙里有一盏梁武帝时点起的神灯,一熄灭的话吉光屯“就要变海”,大家就要“变泥鳅”,可疯子偏要吹熄。他说:“那盏灯必须吹熄……吹熄,咱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为了阻止“疯子”,阔亭要害他,灰五婶也要骗他,可疯子不怕受迫害、受欺骗,“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
疯子的形象,是“狂人”形象的继承与发展,是鲁迅创造的又一“战斗者”。“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在沉默中爆发,苦苦探索,寻求答案,最终在无路可走的情形下被迫疯狂。鲁迅先生用他的亲身体验演绎了一个个真实的开始觉醒的现代国民形象,他们代表的是不甘于在封建腐朽社会苟且偷安的觉醒者形象,他们的觉醒让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与民族的未来。
(二)妥协的知识分子形象
“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这是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与金心异(钱玄同)的对话,借此表达了鲁迅自己的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也是鲁迅关于“铁屋子”或“家”的经典民族寓言。
起初,鲁迅的立场是踊跃的,金心异的回复也是抱有希冀的态度的:“但是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可能。”实际上,鲁迅的乐观却很短暂——他很快就从“听将令”的“呐喊”坠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彷徨”中去了,从小说集《彷徨》中几部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中可窥见一斑。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纵然知识分子有自身的弊端,比如他们的犹疑不决、消极沉沦、自命清高,但最终的根本原因还是那间“铁屋子”的大环境造成了“五四”现代知识分子的孤独和悲剧命运。
《在酒楼上》,吕纬甫总结自身从“出走”到“回来”的人生经历时,悲痛而自嘲地说,“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好笑”,“我在少年时,瞥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什么地方,给甚么东西来一吓,马上飞走了,可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返回来停在原来的地方,便觉得这其实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意此刻我也飞回来了,不外绕了一点小圈子”。他给小弟迁墓,给已故的顺姑买剪绒花,可他以前也是“敢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致打起来的”人。可现在做的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出现这种变化,究其原因,还是吕纬甫这一类知识分子向封建社会妥协了,仅凭单薄的一己之力是绝无打破“铁屋子”的可能的,而那些先醒来的人,只能在许多人未醒来之前再次消沉下去。
“感觉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不管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如何留恋,与我都没什么干系了。”文中,鲁迅借“我”之口道出了他自己和同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难以言说的悲哀,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和孤独的感觉,是在那个黑暗社会找不到归属感的无奈,他已经失去了“根”,失去了知识分子立足的精神家园。
《孤独者》中魏连殳的遭遇也与吕纬甫极为相似,他从一开始的抵抗世俗、特立独行到最后清醒地苟且偷安,自认为是人生的失败者,甚至与狼共舞,最终安于现状,苟活于世。而他内心的痛苦却始终无法排遣。这似乎都是难以摆脱的宿命,“五四”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都难逃西西弗式周而复始的痛苦劳役的悲剧命运。
《祝福》中也有这样一个妥协的知识分子形象,即小说中的“我”。祥林嫂这样问道,“一个人死了以后,实际上有无灵魂可言?”,“那么,有没有地狱呢?”,“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吗?”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祥林嫂对死后去向的担心。因为如果人真的有灵魂,如果人死之后会到达地狱,如果死后的人都可以见面,她就将会面对被锯为两半的危险,那比她活着还要痛苦与悲惨。所以祥林嫂对这个问题也是感到惶恐不安的。“我”作为一个“新党”,对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回答“不”,但“我”和祥林嫂不是同一阶级的人,对她的想法根本理解不深,所以为了推诿责任,就用“说不清”三个字来回答。
鲁迅小说中那些妥协让步的现代知识分子,多是彷徨于光明与黑暗、文明与古老、新与旧之间的“零余者”。对于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沉重的精神负担往往是对民族文化传统中消极方面的直接继承,他们精神上的伤痛是不可撼动的旧传统力量和新生的社会思潮相互撞击所致的精神变异。他们身上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性格,而且由于民族传统深沉厚重的特点,造成一种超稳定的心理结构,突破这种超稳定的心理结构也就变得困难。
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叛逆,集中地表现在其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态度上。儒教恪守“中庸”之道,着重强调人在协调人与自然、社会与他人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时,面对一切不和谐的因素,首先应该自省、自护和自适,“自省”精神在“中庸”的前提条件下,其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平衡,在主观能动性的心理宁静中消除对立因素。于是,知识分子在“自省”后,或者与世俗同流合污,或者走向自我放逐,都选择了回避问题:吕纬甫做了教书先生,魏连殳回去做官,其实妥协之后,是知识分子折断傲骨,灵肉分离。
(三)是伪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鲁迅在小说中,对封建卫道士进行了深刻的讽刺,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封建卫道士的丑恶嘴脸。
《肥皂》中的四铭就是一个典型的伪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其内心十分龌龊丑恶,表面上却假装儒雅端庄,宣称要捣毁天下一切不道德,要还世间一个朗朗乾坤。他一面宣称要拯救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另一方面却对失去亲人的孝女的美色垂涎三分,光棍调戏孝女的话语,在四铭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并且潜意识地给媳妇买了块香皂,这也是因为淫念在心。当他人成为一个乞丐时,他不是伸出援手也不是反思社会问题,而是像那两个商议着去买肥皂给孝女洗澡的人一样,在他人的疾苦中,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妻子的骂声和周围充满喜剧色彩的笑声,剥下四铭那张道貌岸然的面具,让其内心的黑暗彻底暴露在光明中。
《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是一个只知道花天酒地的文化流氓,这样的人竟然可以成为“贤能女校”的教员。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师长”来到女校的真正的目的是看女同学。可是当自己因为常识的浅陋而使授课失败后,平日里标榜自己是新文化化身的他,思想上的变化很大,这个“教员”感到女校里世风日下,不能与女校学生为伍,于是就不再当教员,直接回家坐到了麻将桌上。这时,他就觉得世风渐渐好了起来,也渐渐安心了。正是因为深受封建文化的毒害,这批封建卫道士对旧中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造成了无形的摧残和伤害。
二、鲁迅小说塑造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背后的文化逻辑
文化逻辑是指一种文化中,以逻辑体系为根本所建立起来的思维体例与认识体例。文化逻辑是文化活动的中枢,制约着文化缔造的历程,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都与背后的文化逻辑有直接关系。鲁迅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背后所隐藏着深层次的文化逻辑,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化意味。
(一)迷失与救赎
鲁迅所塑造的知识分子无不有着他自己的影子,他体会着知识分子的迷惑,感受着他们的沉沦,同时也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鲁迅所塑造的知识分子都在人格与理想的迷失与救赎中彷徨求索。在这些小说人物形象的背后,都渗透着鲁迅自己的生命体验,蕴藏着特定的文化逻辑。
《伤逝》中子君与涓生,他们都是走在“五四”潮头的青年,身上印刻着“五四”的印记,有知识,有理想,有目标,有信念,追求着自己想要的东西。
鲁迅在《伤逝》中写道:“人必须生活着,爱才能有依附。”他们的爱情最终破裂,心灰意冷的子君回到旧家庭中,终于在抑郁中死去,而涓生也在悔恨中度日,无法找到出口。涓生和子君的爱恋是整个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青年男女共同寻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自由、解放的时代悲剧。
鲁迅在小说中写尽了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为他们的迷失卑怯与彷徨颓废深感心痛和悲哀的同时,也表达了“立人”主张。鲁迅的“立人”观有超高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他认为中国要独立自强,首先在于中国的国民要有独立自强的精神意识,而这种意识可能首先发端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鲁迅眼里,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对老百姓的启蒙,一点一点地改变社会,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二)疯狂与隐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鲁迅是作为独树一帜的一朵奇花出现并成熟的。“疯狂”是他小说中的一个特殊领域。鲁迅笔下的“疯狂”不仅仅理解为神志不清的、非理性的一种精神疾病,是疯子,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人,更是一种隐喻型写作,可以把它解释为启迪性感觉的隐喻。通过鲁迅小说中“疯狂”的言语举止和行动,人们可以看到“疯狂”表现为一种偏向:对现有范式的僭越,对现存文化秩序的斗争。鲁迅要用疯狂来揭示出二十世纪初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传统——漫长而隐秘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监控——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革命的悲剧性历史遭遇。
《狂人日记》《长明灯》中对“疯狂”病因、病征给出了文化诊断和医治,“疯狂”的被命名不是一种医理的命名,而是一种文化命名,因为这里的“疯狂”表现的是对现有秩序的对抗、破坏。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被维护旧有制度和礼教的人视为疯子、狂人。这也显示出“疯子”的悲剧性命运,“狂人”和“疯子”都被本身生存的环境排挤、剔除而被迫命名。
查其病因,为其诊断。在“疯狂”被定名背后的文化反思中,有鲁迅文学启蒙的意图,意在引发疗救的注意。虽说鲁迅笔下的“疯子”形象明确表现出神经性疾病的特征,可是就其隐喻意义而言,“疯狂”已经隐藏了20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某种文化现状和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遭遇。鲁迅先生这样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正是鲁迅内心一种期盼与坚守。
启蒙者被命名为“疯子”,以及“疯子”被他们所反抗的现存秩序接受或对他们做一种无害化的处理,已经显示出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情况的清醒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启蒙革命命运悲剧性结局的思考。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正如启蒙先驱者周作人所深刻感受到的:“思想革命是最出力不讨好的事业,只会受大家打骂而不会受到感谢的。做政治运动的人,成功了固然最好不过,即使失败了,至少在同派之中还会受到拥护和感谢。”显然,“瘋狂”主题并非鲁迅无意识的一种选择,而是出于对中国“铁屋子”的现状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之后之选。
三、结语
在鲁迅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应与农民群众不同的独特个体,鲁迅先生描写的是社会上的另一种生活。鲁迅先生的小说展现了特定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不同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全方位地追寻他们的心灵深处。这一切都指向对封建主义毅然决然的反对。这就使得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最具有思想性与先锋性。总之,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描写,是在现代文化逻辑的起点上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追问,是中国文学在思想层面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实际上,鲁迅文中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对现代知识分子具体人物形象以及心理文化认识结构的刻画,和与之相对应的作家主体意识的揭示,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不息、痛苦不止的焦虑心理,能让处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读者常读常新,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
(江苏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