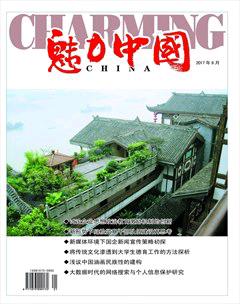互联网与新时代的网络红人
摘要:早在中国互联网兴起的时候 ,第一代的“网络红人”就已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时代的变迁 ,“网红”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趋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网红”文化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对其的文化消费也是与日俱增。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网红”能够流行开来,除了缘于技术层面的互联网的发展与媒介演进外,还与消费者的个人心理需求、议题的社会勾连、受众文化消费与认同的符号逻辑等相关。“网红”文化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有深层的社会学因素影响。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从消费社会学视角出发对“网红”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社会学分析,并探讨“网红”文化消费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互联网;网红;消费;消费文化;消费社会学
1994年4月20日,随着一条64K国际专线的接通,中国的互联网正式到来。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 ]随着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普及程度的提高,网络对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影响也日益凸显。
正如塞尔日 · 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所言,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历史合理性。纵观媒介演变历程,每种媒介形态必然会造就符合该形态的产品,而互联网与自媒体的不断发展催生出一批又一批的网络红人。“网红”现象已经成为极具谈资的社会文化现象,被大众消费着。“网红”的产生离不开媒介的更迭与演进,网络与自媒体的飞速发展为其产生提供了呈现的舞台,但若是仅将“网红”的流行归结互联网的进步与发展未免有失偏颇,因为网红现如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经济形态而存在着,将其置于整体的社会环境中,便不难发现其蕴含的深层的社会意义。
一、“网红”文化及其文化消费
网红,即网络红人的简称。“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他们的走红皆因为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有意或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成为“网络红人”。因此,“网络红人”的产生不是自发的,而是网络媒介环境下,网络红人、网络推手、传统媒体以及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体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
网红”现象不是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文从九十年代末,拥有较高文学素养,以自身的文学作品获得受众追捧的韩寒于安妮宝贝,再到凭借着专业推手团队,靠着噱头、“审丑”而红极一时的芙蓉姐姐和凤姐,直至现如今依托着时代的变化,拥有800万微博粉丝,身价估值3亿元的Papi酱,中国的网红文化发展进入到了网红3.0时代。
作为网红3.0时代的代表人物,Papi酱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16 年 3 月,Papi 酱拿到了由罗辑思维、真格基金、光源资本和星图资本的 1200 万元投资。2016 年 3 月 21 日,逻辑思维公布了其与 Papi 酱的具体合作,即拍卖 Papi 酱视频贴片广告,并有逻辑思维全程策划监制服务。2016 年 4 月 21 日,逻辑思维即将在北京召开“中国新媒体的第一次广告拍卖会”,门票高达 8000 元一张。业内人士预测,Papi 酱估值可能已达到 3 亿,实现了从“低配版苏菲玛索”到“互联网时代的鲁迅”的转变。[ ]
二、“网红”文化消费的因素分析
“网红”文化的本质是一种草根的、浅显的、大众的通俗文化。不同于文字时代的网红,新时代的“网红”文化更多的是对于“肉体”“欲望”等的感官性消费,消费者在其中获得听觉冲击、视觉愉悦等感官享受。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庞大的消费者观看直播的过程中满足的是自身最低层次的、自我的生理需求,是一种单纯的快感消费。除了单纯的出卖自身身体、满足大众性快感的网红,还有许多通过网红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来满足受众审丑、娱乐、窥视、猎奇、吐槽围观等心理需求,。正如费克斯的两种经济理论中对于“文化经济”的阐述,文化经济流通的是意义和快感,显示了消费者的解码差异。由此可见现代的“网红”文化,“网红”个体成为了生产者,“注意力”与“快感”成为了商品,而无数网民则是其消费者,“网红”文化消费的剧增可以视作是庞大的社会群体对于自身初级需求的满足性行为。[ ]
互联网与自媒体的发展使得消费物质实体性逐渐从消费中剥离,在互联网社会中,大众将物质性的消费转向了符号沉浸。“网红”作为网络社会中的流行符号,对其的消费本质上是对于符号的消费,是对“网红”作为符号的事件、内容、议题观点、商品、广告、游戏等实际或虚拟的消费,是消费社会与网络虚拟空间的结合。在互联网中,各种事物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的,网红亦然。网红”对其产品如议题、风格、主张以及自身标签,以文字的、语言的、非语言的、视觉的、听觉的象征符進行编码和意义输出,聚集围观的网民根据各自爱好,在消费中进行解码,以获得快感等需求。
“网红”文化究其根本是一种“亚文化”,如对木子美等的围观消费显然是对主流文化是相违背的,但是其却不乏年轻群体的追捧,而这正是“网红”文化所代表的个性特征,体现且满足了后现代年轻人追求个性的心理,在消费吐槽、恶搞、嘻哈、喧闹、性向、二次元等个性文化中的自我满足。此外的对抗、逆反等心理,也使得部分“网红”文化虽然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悖,却仍有不少拥护者。有统计显示,“网红”的受众中有 73%属于 19 岁以下的青少年,其成长中伴随着本能欲求、心理需要和归属认定,这也恰是其成为“网红”文化消费者的原因所在。
三、“网红”文化消费的影响
“网红”文化能够不断发展,也就说明其作为一种“亚文化”而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一方面,“网红”文化很好地满足了一大批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无论是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的满足,还是众多年轻群体所追求的个性差异,都能通过对“网红”文化的消费得到一定的满足,另一方面,“网红”文化代替了各种社会群体发声,众多“网红”对于社会现象的吐槽与批判,以及由此形成的消费者间的共鸣与网络舆论,必然会对于现实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对于社会上恶性事件的批判,凭借网络传播的即时性与广泛性,必然会引起更大范围内的网络舆论,对于事件的进一步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扩大社会民主。以及巨大的“网红”文化消费所带来的“网红”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的“网红”文化让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当然消费对文化意义的丰富与繁荣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大规模的传播意味着内容被非语境化,内容便失去了“灵韵”,每被复制传播一次,意义就衰减一次。[ ]而随着“网红”文化的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网红”及文化传播内容的生产制造也变得批量、程式化、同质化,这种机械复制的文化形态如批量的网络“女神”,本质与工业产品无异,而这样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发展的能力,成为一种僵化的,刻板性的存在,这样的文化与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被社会大众所抛弃。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带来的是娱乐至死,“网红”文化之中仍存在着大量的低俗文化,而对于低俗文化的过度消费必然会破环“网红”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多量的低俗文化将降低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郑文聪《“网红3.0”时代的特征及受众心理》[J]新媒体研究,2016年第6期
[3]王玉、崔璨、高思佳、钱雪伦《从“网红”到“网红经济”的跨越——以 papi 酱为例
》[J]现代经济信息,2016
[4]夏建中《消费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视角》[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7.10
[5]王宁 《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黄铄翱,江南大学法学院2014级社会工作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