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天堂
羽微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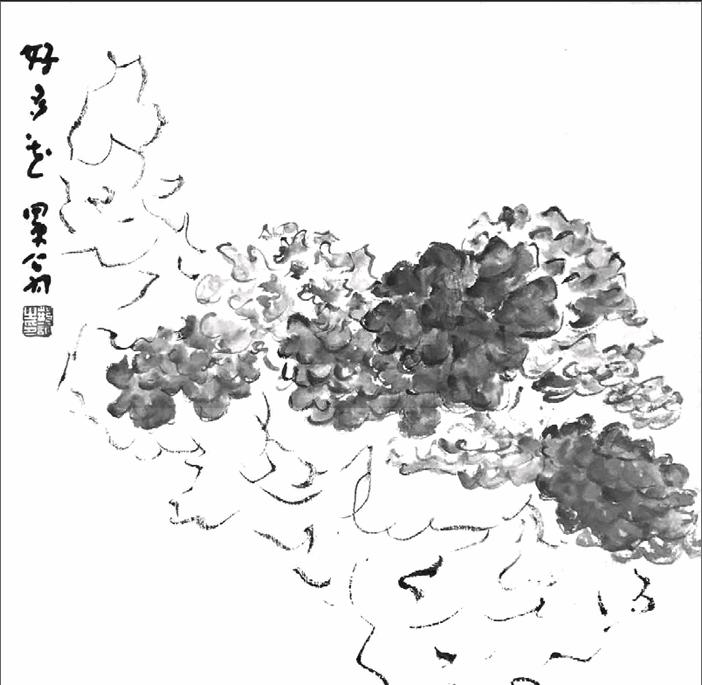
清明节快到了,又是去到父亲坟前,想起他的时候。
我总记起,他躺在那张冰冷的床上,殡仪馆仪仗队吹着哀乐,缓缓地推他进到另一扇门的场景。他们把他的手放出来,扶着床边。看起来就像是送去手术室,他还活着。
我那时差一点就叫起来,要同旁边的哥哥说,我就知道,父亲还是活着的。但很快我又明白,他们是故意这样。他们这样,让父亲像还活着的样子,让我很难过。
就像守灵的那一晚,他安静地躺着。我总以为直到那时他还有着生命,因为他的皮肤,还有他的思想,都似乎在缓慢地收缩,把旁边的空气也往他的身体那里引了过去。我总疑心和期待他会突然动一下,也许是手指,也许是脚趾,也许是眼皮。就像我在小说里,在新闻里,在电视里看到过的那些奇迹。我总疑心和期待当我走出门,回来的时候,人群就会拥过来,告诉我奇迹发生了。但没有。但我那一整晚都这样期待着。
直至殡仪馆仪仗队吹着哀乐,把他缓缓推进那扇门,我还期待着,直至骨灰坛捧出来——但我在梦里不肯接受,我仍然梦到他,在家里的楼梯转角处碰到他。父亲大汗淋漓,腿脚好像不太灵便,我惊讶地问:“啊,爸,你怎么了,你不是?”——我指火化,但我不肯说出那两个字。父亲疲惫地摆着手,摇着头阻止我:“不要说了,不要说。”我也就不再问他,我怕问他。但父亲回来了!我满心欢喜地扶着他的手,要他坐在以往常常坐着的那张竹躺椅上。我因一直期盼他是活着的,所以对于火化,心里总是难过,总有错觉他在火化中受着无比的煎熬才真正死去。
父亲去世后几天,有人在楼下叫我父亲的名字。“余医生,德文,余医生,他在楼下大声地叫。”——父亲退休后,在自家一楼开了间牙科诊室。我和妈妈还有哥哥在二楼,大家都不作声,仿佛父亲会回应。“余医生,余德文。”我的牙很疼。楼下的那个人继续叫。哥哥走出阳台,说余医生不在这里,你先去医院看牙吧。楼下那个人哦哦,终于走开。
那一次的喊人,也让我知道父亲的确是不在了。有人叫他,他不会再有任何回应,他在生时对于顾客总是很热情的。我看了看哥哥,哥哥看了看我。我们没有说什么。
我长着和父亲很像的脸庞,以至于在父亲去世很久后,有一个路人经过我,她停下来,说:“你就是德文的女儿。”我突然听别人提起父亲,心里是悲伤的,但她能从我的脸庞看出我是父亲的女儿,我又有一点儿骄傲。父亲的四个子女,我长得最像他。我虽不能确定父亲最爱谁,但我总归是长得最像父亲的了。
是的,父亲最爱谁呢?我总会想起这个问题。我没有像大姐那样与他共同度患难的岁月。没有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他低着头,指着水缸,悄悄地告诉大姐,如果他这一次没有回来,水缸底下的土里埋着一些钱,拿着去投奔广西的四叔吧。父亲早期的人生非常坎坷,曾被抓入牢中。他因此总疑惑自己的人生。
那么是二姐么?二姐尚年幼,父母已分居,父亲常常歉疚,忍不得对她更怜爱些。大姐常说,如果她的零花钱是五分,那么二姐便是一角。大姐也不妒忌,她比小妹年长七岁,很有长姐为母的成熟了。
那么是哥哥么?哥哥从小性格温顺,懂事,从不顶撞他,也是他唯一的儿子。也许不能说是唯一的,他曾经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在父亲出狱后,他的小儿子已埋在小小的黄土堆下面,旁边还有一个小土堆,是小儿子的年轻母亲。父亲入狱两年,母子饥贫交迫,亦在惊恐中受世上的白眼和冷落。他们等不及再见到生命中的依靠。“棺材都沒有,用草席卷着就埋了”,我只有那一次看到父亲流了泪。我这一辈子,只有那一次看到父亲在说那一句话时,流了泪。她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他的女同学,地主的女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当时一贫如洗的父亲。但这美好的故事只有了开头,随着父亲入狱,她仅仅做了不到三年的母亲,便永远地离开我的父亲和这个世界。
我小的时候,不清楚这些往事,不能明白那些往事,会跳出来折磨他,激怒他。把他变成一头白发苍苍的狮子——我懂事起,他开始白发苍苍了。在两个姐姐可以独立并出去工作后,他娶了第三任妻子,我的母亲。他在48岁时有了我的哥哥,在他50岁时,有了他最小的那个女儿,和他长得最像,脾气最相似的小女儿。经常会惹他生气的小女儿,一直想知道,父亲是不是最疼爱他的那个小女儿。
我记得,我和他应该很像。一样有着圆圆的鼻头,一样薄薄的嘴唇,一样曾天真地以为世界只有黑和白。以为每一样事物,都会有对错。都要分出对错。我每每在他责骂我,会带点恶作剧地指出他逻辑的不够缜密之处,明知道这样会激怒他。他生气是很大动作的。他会一边擦汗,一边喘着粗气,也许是带点夸张地喘着粗气。他要我们明白,我们把他惹生气了,是多么不孝。他曾在暴怒中,揪着我的头发把我的额头往地板上撞,桌子上的镜子被打翻在地,裂成碎片。
我在紧张和昏乱中,估计我的额头要落向何处,好用手掌和手肘垫着,不要被碎片扎到。也有一次,他把我拉到家门口,要打给所有路过的人看。学校的学生三三两两经过门口,他们都认得我,他们回过头来看我,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记得,小时曾大病一场。医生说,这些药吃了,不见效,也就没有办法。他忧心忡忡地深一脚低一脚往家里走。他的汗水冰凉,我伏在他背上,感觉舒服了一点。他开始给我熬中药,家里总充满着好闻的中药气味。他先试一口,然后再递给我,沉默地看我喝完。然后再递给我一颗糖。他就这样看我缓慢地好了起来,看我伏在桌子上,写作文:《我的父亲》。
我记得,在炎夏,晚上睡觉前,他会答应给我摇一百下扇子。大葵扇摇得很缓慢,很清凉,一呀二呀三呀四。总是摇不到一百下我就睡着了。我还记得,他拿了红色的塑料盒子,让我和哥哥猜是什么,我和哥哥猜啊猜,总是猜不对。他神秘而得意地笑着,从塑料盒子抽出一副扑克牌,我和哥哥都惊讶地叫出声来。多么聪明的爸爸啊,用锯片把红色塑料布烙了副扑克牌盒子,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扑克牌盒子会坏掉了。那时我们多小啊,家那么宽阔。我们就那样家里叫着笑着,要去抢父亲手中的红色盒子。一边骄傲我们的爸爸啊,是最聪明的爸爸,只有我们有。
那次我伏在他的坟前,头抵着黄土。再一次想起这件往事。想到在他的儿女中,总是我最令他生气。想到我曾是多么希望他最疼爱我。想到童年太短暂了。他在我们童年时便进入了老年,他要恨铁快成钢,他希望我们快一点长大成人。我站起来,站在旁边的大姐问我可曾梦到过父亲,我答有。我说了一个有关父亲的梦。她在听,听完后,头不耐烦地侧了一下,说:“爸哪里会这样说话。”然后就走开。
我在她转身的那一刻流泪。我在想,是的,也许我甚至做不出一个像父亲真来过我梦中的梦。可是大姐为什么连我做的梦也要否认。为什么总自认是最了解父亲的女儿——虽然事实便是如此。为什么她总以此自重,仿似站在父爱的高处低头看我。令我自卑和自责。
我写过一首关于父亲的长诗,写完后给父亲看。他看完后,说:“看完了。”然后用手转着健身球,咣当咣当地走开。他没有说写得好。事后也没有跟我说过什么。我想他应该有一点意外,他也许期望他在我们眼中,应该趋于完美,但他因为父亲这个架子,并没有说出对他在我诗中的形象的失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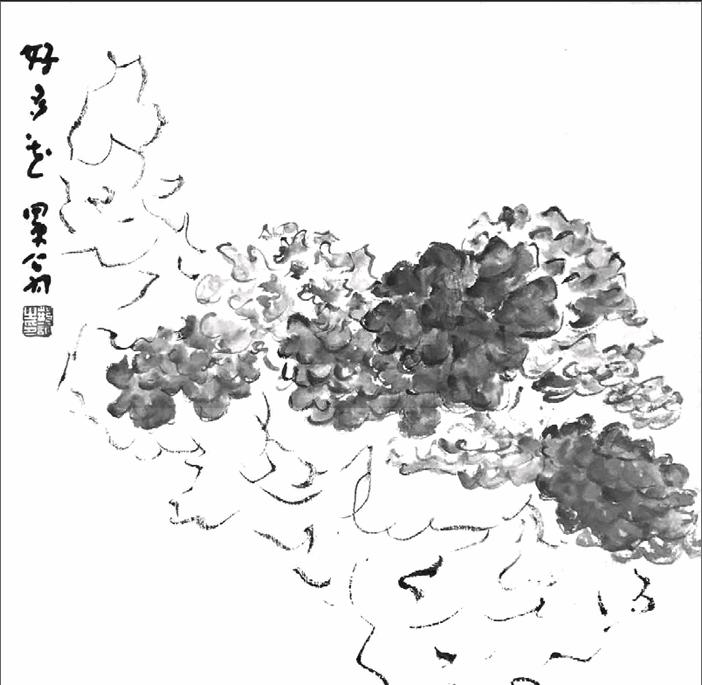
我曾暗暗策划着一个惊喜。我收到《人民文学》诗歌编辑老师的邮件,告诉我的诗歌通过审核,将会刊登在下两个月。我按捺着迫不及待要在父亲面前炫耀的心情,想等待收到《人民文学》的样刊时,把它漫不经心地放在父亲常常喝茶的那张茶几上,等他拿起来看,再淡淡告诉他,我有一组诗歌发表在上面。我是多么期望那充满戏剧性的一幕,我非常希望他能够以我为豪。
但我期待着的那一幕永远没有机会来到,在收到《人民文学》样刊的前一个月,父亲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他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我永远没有机会问他,爸爸是不是我最不乖,是不是我最让他感到心痛。我永远没有机会可以告诉他,我知错了。
父亲刚刚去世那段时间,悲伤是混乱的。更多的悲伤,是在后来不经意想起他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顾客大大咧咧地坐在父亲常坐的那张躺椅,我非常生气。父亲去世后,母亲接手经营那间牙科诊所。那个顾客不停地晃动着二郎腿,坐在父亲常坐的竹躺椅,肆无忌惮的样子。我拿着一杯茶,走了过去,忍着不说话,再走回来,但我终于还是走过去,停在他面前,说:“你坐别的地方吧,这个位置是我要坐的。”他很惊讶地看着我。但我冷静而坚决,他悻悻地站起来,坐到旁边的木沙发上。
七岁的小侄子,父亲最疼爱的小孙子,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更能接受他的离去。他相信他的爷爷在去世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父亲下葬时,他并没有害怕,只是指着那个红色的棺木,问他的母亲:“爷爷是躺在那里吗?”“是的。”“那是什么地方?”“通往天堂的地方。”“红色的天堂?”“是的。到了晚上,爷爷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他听了,很高兴。他拿着铁锹要去铲土,说:“我长大了,我也要去帮忙。”我听了,又再一次地流泪。
小侄子还曾问他的表弟:“你的爷爷去世了吗?”“没有。”“奶奶呢?”“没有。”他大为惋惜,说:“你家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上天堂。我爷爷可是上天堂了。”他带着一点炫耀的口吻,说到了晚上,最亮的那一顆星星就是他的爷爷。他有一次在家里玩游戏,心虚地走到屋外,寻找爷爷,害怕爷爷发现他没有做完作业便玩游戏。他从来没有感到爷爷是彻底地离开。爷爷只是在更高处。
在一个红色的叫天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