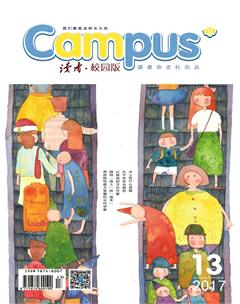我想和你相互浪费
周华诚
昨晚读到一首很好的诗,诗曰——这样一“曰”,容易进入那种诗的状态——
满目的花草,生活应该像它们一样美好/一样无意义,像被虚度的电影/那些绝望的爱和赴死/为我们带来短暂的沉默
我想和你相互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
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诗的作者是李元胜。我在这里录了半首,即使半首,也能读出它的好了。
我不能把所有的美都呈到你的面前。自己花了力量去寻找,那样的美,至少能在心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一点。
以这样的方式和你说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一大块背景,那是我的村庄及田野。每个人说话的时候,心里都是有背景的。很有背景的人来自呼伦贝尔草原,他是一个牧羊人。水手有着更大的背景,他的皮肤黝黑,他的背景是大块的黑黝黝,望不到边。他是牧风者。
我想和你相互浪费——当我在稻田边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宠辱不惊的昆虫——我眼前是婆娑的稻叶、古典的稻花、乱来的野草、沉默的羔羊(在夕阳西下的芝麻地里),还有宠辱不惊的昆虫。
说到昆虫,我跟多数人一样都是虚假的昆虫爱好者,我连它们的名字大多叫不出来。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世界上的人那么多,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又有几个呢。
昨晚我把一些昆虫的图片发布出来,向大家求教,结果大家给出的名字很有意思。
说一只蝴蝶是蝴蝶,就好像说一条河是江,说一个姑娘是女人。对是对的,但是不过瘾。我从小在乡野长大,对大的动物几乎都能叫出名字,但乡下人心思粗疏,对那些很小的东西,一概以“虫子”称呼。大概乡下人觉得那些都是无用的,知道那些干吗——这虫子那虫子,不過都是虫子。
其实正是那些无用的东西,才让我们的日子变得不一样。
今天我收到一张截图,那上面排列着这样一些字:鞘翅目某种虫、直翅目某种蝗、蛛形纲某蜘蛛、蜻蜓目某蜓、直翅目某种蝗的若虫、鳞翅目眼蝶科某种眼蝶。
太棒了!这样的回答让我惊叹,觉得那些小昆虫一下子有了科学的美感。
这位“大神”姓熊,是我弟弟的同事——生物学学士、生态学硕士、生态学博士,如今在美国。干什么呢?就是做一些没用的事,比如,认认虫子。
我也很怀念那个在田埂边上虚度的夏日黄昏。我面对直翅目某种蝗、蛛形纲某蜘蛛、蜻蜓目某蜓及鳞翅目眼蝶科某种眼蝶,静静地按下快门。
长的无意义,短的沉默,满目的野草,我们相互浪费,彼此虚度。
只有稻子并未虚度,它距离成熟又近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