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名义中西谈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 苏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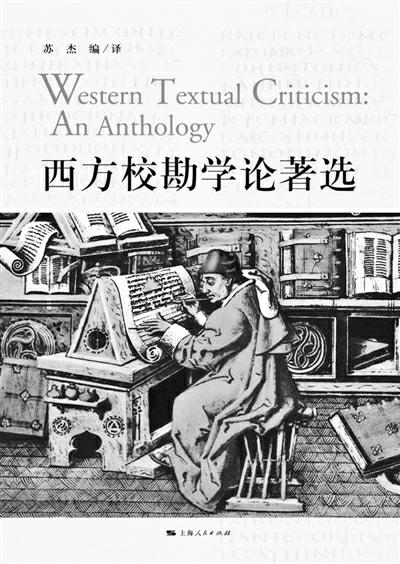
汉语对校对之事(collation)和校勘之事(criticism)没有做明确区分,笼统称之为“校”,以至于人们将校勘学视为小道末技。殊不知校勘学在西方被视为学问的皇冠与顶峰。
苏杰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
“校勘”,顾名思义,是校对和勘误。对于这类工作,人们并不陌生。譬如说某报刊某一期出现了比较多的错字、漏字,知识错误,或者标点符号不规范,往往有热心读者写信给编辑部,“建议加强文字校勘工作”。
有几年时间我在译介“西方校勘学”。与学术圈以外的朋友见面聊天,被问及在研究什么,我回答说,“校勘学”。“校勘?!噢~~噢”,朋友瞠目颔首,一脸“了解之同情”。
不仅圈外的朋友如此。关于校勘工作的学术含量,两年前微博上曾有过一次十分热烈的讨论。有位学者说,校勘是机械性工作,没有什么学术含量,认为真正能够解决文本难题的,是各领域的“专门研究家”,而不是文献学训练出来的“校勘家”,建议将学术含量低的文本工作称作“校勘”,将学术含量高的称作“研究”。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甚至反唇相讥。
我倒觉得,这位学者的话虽然未免偏激,却也并非全无道理。
我们古典文献学所做的校勘,与报刊编辑所做的校勘,有根本差别吗?
报刊编辑所关心的问题是,(一)这排印的校样与作者的原稿一致吗?(二)作者的原稿有什么错误吗?
我们古典文献学所关心的文本问题也大致如此。段玉裁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所谓“底本之是非”,就是传本与作者原稿是否一致,所谓“立说之是非”,就是作者说的是否正确。
两种校勘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字,就是段玉裁所说的“难”。
报刊编辑进行校勘,有作者原稿,大多数情况下还可以咨询作者本人,故而问题(一)的解决就成了一个“照本改字”的机械工作。至于问题(二),作者的记述是否符合事实,编辑作为同时代处于同一历史语境中的人,也不难做出判断。
古典文献学所进行的校勘,比如说,《史记》校勘,则要难得多。我们没有太史公的原稿,现存最早的抄本,距离作者时代也有几百年之久,中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传抄。当我们面前的这些本子出现异文的时候,判断哪一个异文来自太史公原稿;当《史记》与其他文献存在分歧的时候,判断太史公的记述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古籍校勘,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校异同,二是定是非。定是非很难,校异同并不难,基本上是机械性的工作。现在有些校本,只完成了第一层次的工作,即,只校异同,没有定是非,书后“校勘记”,只列异文,几乎不做按断。对于这类“校勘”,有些人还矜诩为“采铜于山”。大约正是有见于此,前文提及的那位学者才提议要将这类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校勘”与真正的“研究性校勘”在称名上加以区分。
西方校勘学将第一个层次的工作称作collation(比对,校对),将第二个层次的工作称作criticism(鉴别,评判)。
胡适首次将西方校勘学介绍到中国,并借此他山之石,对清代的考证方法进行分析:“校勘学的方法可分两层说。第一是根据;第二是评判。”(《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校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找根据,第二步是做评判。文中揭明,“评判”一语是对英文criticism的翻译。而找根据,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比对异文。
Collation,比对异文,这项工作尽管很重要,但对操作者来说,主要是要求其认真细心,知识上的要求并不高,甚至过多的知识还会成为比对异文的障碍。保罗·马斯《校勘学》指出:“不自觉的推测可以很容易地危害校对的客观性”,认为“最可靠的校对者(collator)”往往要“关掉自己的知识系统,纯粹通过视觉开展工作”。
西方校勘家往往并不亲自做比对异文的工作。比如为了校勘《新约》,理查德·本特利曾经“派人对外国图书馆所藏同样古老的抄本进行对校”(《抄工与学者》,p.192)。值得注意的是,版本比对的实际操作者(collator)付出了机械性的辛劳,其比对结果却往往冠以委派者(一般是校勘家)的名字。《抄工与学者》一书中数度出现16世纪著名古典学家蒂尔内布的“校对异文”(Turnebuss collations),有一处行文很明确,a collation made for Turnebus(为蒂尔内布做的校对异文),用的介词是for,不是by(英文第四版,第176页)。
将“比对异文”比作“采铜于山”,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青铜器上,怎么可能勒上矿工的名字?除非他本身就是设计/铸造者。只有当校勘家亲自去比对异文,“采铜于山”的比喻才有称道的意味。就像名厨亲自种菜、亲自钓鱼,引人赞叹,并不是说种菜和钓鱼有多了不起。如果不是名厨在做,那不过是菜农和渔夫的工作而已。
Criticism,鉴别,评判,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校勘,也就是段玉裁所说的“定是非”。
汉语对校对之事(collation)和校勘之事(criticism)没有做明确区分,笼统称之为“校”,以至于人们将校勘学视为小道末技。殊不知textual criticism(校勘学)在西方被视为学问的皇冠与顶峰(A.E.豪斯曼《用思考校勘》,《西方校勘学论著选》,第26页)。西方学术史上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人有时被称为grammaticus(文法学家。有一本专讲校勘学的小册子,题目就是《文法学家的技艺》),但是最令他们满意的称谓却是criticus(鉴别者,校勘家。参看桑慈《西方古典学术史》,张治译,上册第35页)。因为,这是“定是非”的人。
如前所引,段玉裁说,“是非有二,一曰底本之是非,二曰立说之是非”。西方文献学也将这criticism分为两个层次,分别是lower criticism(下层鉴别)和higher criticism(上层鉴别)。前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作者的准确文本究竟写的是什么。后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评判作者所写的这些文字。前者大致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本校勘,后者则有些复杂。
要想正确评判作者所写的文字,当然需要设身处地,搞清楚作者是谁,家世背景如何,该文本的形成,曾参考过什么资料,目标读者是什么人,反应如何,等等。也就是说,除了关注“文本的世界”,还关注“文本背后的世界”,以及“文本面前的世界”。
对作者及其历史处境的关切,是认真读者的自然反应。《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学术传统。
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从认知心理的角度看,西方的higher criticism与中国的“知人论世”,似乎有着大致相仿的心理动因。然而细考其问题语境,却有十分重要的区别。
higher criticism与lower criticism是在讨论《圣经》文本时形成的术语。因为lower criticism(下层鉴别)这个名称让相关学问显得比较low(低级),于是被改称为textual criticism(文本校勘)。相应地,higher criticism(上层鉴别)也改了名称,叫做historical criticism(历史鉴别)。大概可以理解为,对相关“立说”的理解与判定,当以历史为依准,考察《圣经》文本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本来面目与含义。
讨论古典文本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知人论世”,在运用到《圣经》文本时,却被许多人当成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圣经》文本背后是神,不是人;《圣经》文本是神的启示,是神的全然无误的话语。如果当作人为的作品,分析其资料来源,分析其撰作的历史语境,对于信仰来说,那将会有颠覆性的影响。
著名神学家叨雷(R.A.Torrey)在论述“上层鉴别的历史”时,首先解释为何在大众眼里“上层鉴别”就等同于“不信”(unbelief)。因发表《错引耶稣》一书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巴特·埃尔曼(Bart D. Ehrman),最初是“获得重生经验”的基督徒,以《新约》经文鉴别学为志业,最终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当然,他在书后所附的访谈中表示,从事《圣经》文本校勘研究,并不是他信仰改变的唯一原因。但无疑是原因之一。
去年因为复旦大学古籍所组织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幸认识了美国宗教学家、曼森《圣经》讲座教授埃瑞克·齐奥克斯基。
研讨会前,我陪埃瑞克在上海走了一天。他有他感兴趣的目的地,他说了一个街道的名称,说很有名。什么?我请他再说一遍。“潺沟Street”?我竟然没听过。请他写下一看,不由哑然失笑。Changle Street,长乐路。
研讨会上,我应景谈起了中国古典文献校勘与《圣经》校勘,谬托知己,对lower criticism(下层鉴别)、higher criticism(上层鉴别)与中国校勘学之间的共通之处津津乐道。埃瑞克提醒我注意higher criticism(上层鉴别)与historical criticism(历史鉴别)对宗教信仰意味着什么,会后还惠我资料,示我周行。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此前我对这个问题的确未曾深思。
我们太容易以己度人,又太容易目不见睫。中西比较,时见心理攸同,固可欣也;然而名义之辨,可不慎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