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上帝的声音
马铃薯兄弟+赵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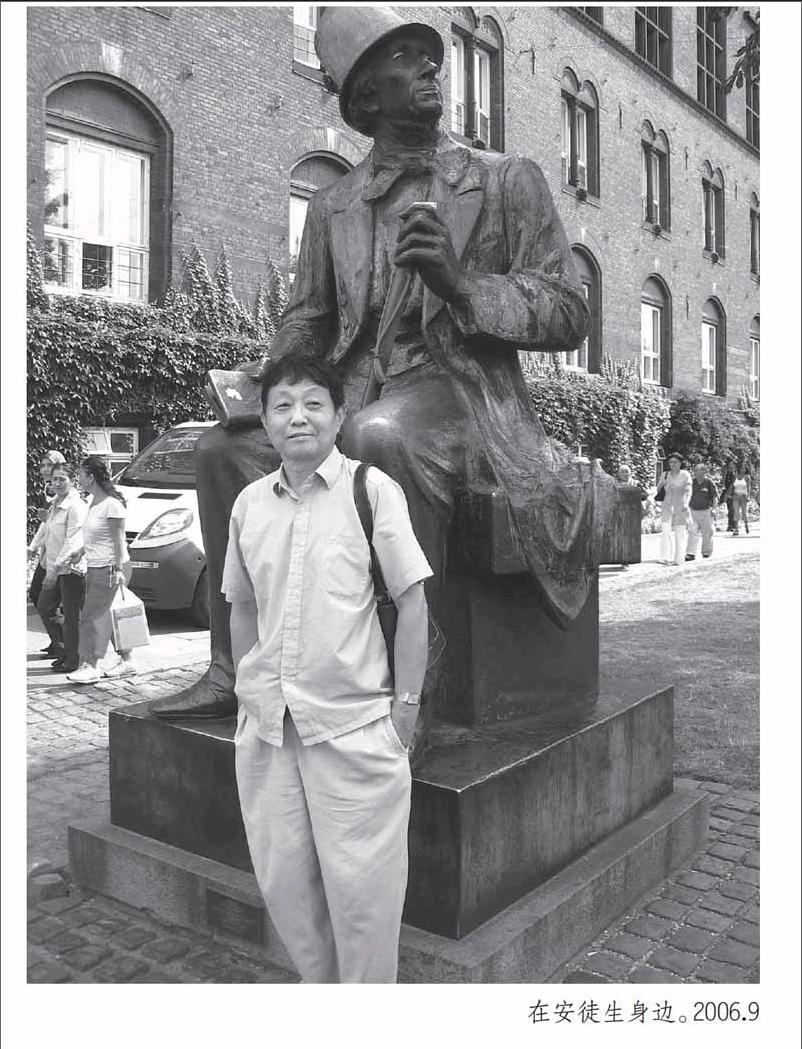

主持人语:
诗人赵恺对80后、90后新生的青年诗人来说是陌生的。而我知道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诗歌复苏后疯狂的年代,他的一首叫《第五十七个黎明》的诗歌,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据朋友马铃薯兄弟介绍,赵恺的日常生活過得非常敦厚、实在,自信和宽厚。我从他的诗歌中读出了一个优秀诗人的境界,其作品无不充满历史感和文人情怀。特别是如今,当我重读《第五十七个黎明》时,依旧被感动,依旧感到优秀的诗歌所蕴含的难以抗拒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这里我想说,诗人赵恺是值得我尊敬的。(雨田)
马铃薯兄弟(以下简称马):赵恺老师,您好。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地对海峡两岸的诗人做过一些访谈,发表在浙江《江南诗》等刊物上。最近,我受托做一个关于您的专题,既是向为当代诗歌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一代诗人表达敬意,又可将您的诗歌成就向当下的年轻诗歌作者和读者做一次较为系统的呈现。接下访谈的工作后,我心底的记忆有被突然唤醒的感觉——在80年代初期,我就是您的读者了,那时我还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那时您的《我爱》获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另外两位江苏诗人:王辽生和朱红,我作为一名江苏人,曾深感荣耀。后来,我曾有机会向王辽生老师讨教,他还曾一字一句给我修改过习作……这些青春时期的美好记忆,一直在心底珍藏着。我不否认,此次听编者以“老诗人”尊称您时,我有些感到陌生的不适感,在我的心目中,您一直是充满激情、充满朝气的形象,和“老诗人”的“老”字似乎不搭边儿。但您毕竟又是属于从战乱、动荡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是我们这个民族一段艰难曲折的历史的见证人。您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童年历经苦难,留下深重的精神创伤。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对于普通人,这些经历或许只求淡忘,但对于一位艺术家、一位诗人,这些经历在伤害着经历者的同时,也在以某种曲折的方式,提供着激励和滋养;诗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命运的磨折。这个访谈的第一个问题,想请您简单回顾一下,战乱年代,您的家庭所经历的变故,您个人艰难成长的轨迹,您是怎么从那种苦难、艰困的生活中顽强生存下来的?
赵恺(以下简称赵): 能够用语言表述的苦难不是真正的苦难。如影随形、肩蹱相接:苦难是我的终生死敌。
苦难不是财富。如果一定把它说成财富,我拒绝这种财富。
一旦苦难来犯,则不能畏惧,不能懦弱,不能回避。回应苦难的唯一方式:抗争。打倒,站起;再打到,再站起:为了尊严。
马:有记载,您1950年即开始发表作品,算起来,那时候您才十二三岁,这个年岁不仅写作而且开始发表习作,可以称为早慧的文学少年了。您最早发表的是一篇什么类型的作品?发表在何处呢?
赵:在重庆明德小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本应三年级以上学生才能参加的全校作文比赛。我参赛的题目是《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居然获奖。奖品是一支铅笔和一个铅笔刨子。举着奖品一路欢呼回家,一头扑进妈妈怀里。那篇作文可视为此生最初的写作。发表文字——不可把任何文字都称为作品,作品是品质,它庄严甚至神圣——是在1950年夏天,从南京五台山小学毕业等候第四中学发榜。当时家住新街口一侧的沈举人巷3号,位于《新华日报》后门边。少不更事,竟然把一篇姑妄叫做散文的文字寄给《新华日报》。有一天,我正在地上打玻璃弹子,从院外来了两个人,他们问:“你们院里有个赵恺吗?”,打弹子的同伴指着我说:“就是他。”话没落地,来人说:“真调皮。”原来,他们是《新华日报》的编辑,来为寻找作者:我的文字发表了。写的什么,现在全忘了。那年,12岁。
马:促使对您走上文学道路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在您从事文学写作的历程中,有那些人或哪些作品曾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
赵:命运剥夺尊严便创造尊严。一切尊严都必须也只能以创造体现,于是我就写作。
许多经典作家北斗星座一般启示、震撼、引导着我。具有命运意义的是雨果和他的《悲惨世界》:冉·阿让就是我。事过多年还了夙愿:麦加朝圣一般去了巴黎,久久,久久,我的手掌紧贴在雨果的墓碑上。
马:《我爱》是80年代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是您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您对这首诗的看重也是很明显的,您后来出版的一本诗集,就以此为书名。这首诗的出现,和那个年代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它发出了那个年代人们心底的真实的声音,呼应了时代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它兼具反思和疗伤的双重意义,是一首痛定思痛兼放眼未来的作品,在帮助人们冲出迷惘、重塑信念的过程中发挥了诗歌激荡人心、温暖人心的作用。请您具体第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以及写作、发表的过程。
赵:《我爱》即我,它是我半生的血和泪,血泪是没有经验的。
马:继《我爱》之后,您的另一首重要作品《第五十七个黎明》出现在诗坛,立即引起了关注和广泛的好评。这首诗以叙事的结构,书写普通劳动者的平常生活,既表现主人公生活的艰辛,又表现她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感情醇厚,节奏张弛有致,读之朗朗上口。这首诗延续了《我爱》的真挚、浓情的特点,但在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方面,这首诗显然更接地气,更透出生活的况味。这种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的闪光点、从平凡中发掘诗意的写法及达到的圆熟度,令人耳目一新。这首诗的写作机缘是什么?请您对这首诗的构思与写作的经过作一介绍。
赵:1980年11月,我去《诗刊》工作并等待《诗刊》次年的进京户口指标。当时《诗刊》没有自己的家,租用朝阳绿化队的房子,地点在遥远的大郊区小关。一个燕山飞雪大如席的傍晚,在公交站台看见穿梭如织的行人中,有一辆母亲推着急急赶路的婴儿车。人和车覆盖着厚厚的积雪,状如一座行进的雪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还要在风雪中奔走多久才能到家呢?婴儿车仿佛从心上碾过,我热血激涌,神魂两痛。自那,行止梦醒都是婴儿车者,约十天。把那位母亲构想为纺织女工是因为我熟悉纺织厂。非常熟悉。成竹在胸,便切身体验。对于文学,不是采风,是体验;不是汗水是血泪;不是甘苦是生死。没有火之焚,水之淬,砧之锻打敲击,何来干将莫邪剑?我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小关赶到使馆区。之后,一条街一条街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走,再之后,沿着长安街自东往西,东单,西单,一步一步往诗的终点天安门前进。发现难,表现更难。写作写作,作品是得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呀。摩顶放踵、焚膏继晷者十日。稿成,如鸟之破壳,如蝉之蜕壳,如蛇之更皮。我和我的诗一道累病了。
马:爱是您写作的主题,“母爱”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您写母爱的诗作,具有特别的感染力。《母亲》这首诗里写道:“白昼和黑夜/ 使时间绵延不息 /无所在 无所不在 母亲/是永恒的谜 …… ”这首诗中咏唱的母亲,不仅符合普遍意义上的母亲的特质,不仅是一种对博大的母爱的赞美,结合您的人生经历,更能读到其中包含的怀念和疼痛感。爱有时候可以是浅吟低唱,但有时候却也可以是泣血的呼喊。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您所属的一代经历过磨难的诗人的作品中,“爱”会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经历过爱被剥夺、爱缺失、爱有罪的非人时代,当时代逐步进入正常的轨迹后,在人性的复苏过程中,爱是疗伤,爱也是重新建立和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么理解您作品中所表达的“爱”的主题,不知对么?您怎么理解您及您那一代诗人对吟咏爱的执着?
赵:爱是权利但不是专利,它属于一切生命。一己之爱,家庭之爱,故乡之爱,国家之爱,祖国之爱,人类之爱:有层次,是攀登。而引领和照耀在这一切之上的,是母爱。母爱是爱的制高点。母爱有神性。神的具象是母亲。“国家”区别于“祖国”。“国家”是权力,“祖国”是命运。对国家可以转身,对祖国,只能面对。
爱,才被爱。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一样,爱是古典人文力学定律。以色列第四位总理梅厄是一位母亲。本是苏联人,因为犹太血统流亡到美国并取得国籍。以色列复国,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色列。对于“祖国”,梅厄的回答是:“不是身份认同,而是命运托付。哪里热爱我并被我热爱,哪里就是祖国。”
塔尖啊请敬畏塔基,一切巍峨崇高,都或是承载或是倾颓在大地的肩头上。
背叛能让石头流泪:
大地,母亲。
马:您是一位对现实十分敏感的诗人,您长于从现实中撷取灵感,并酿造成诗,很多现实题材,经您的点化后,就具有了特殊的感染力。比如汶川地震灾难发生后,无数诗人写下无数的诗篇。您的《哭墙》在此类作品中显得十分醒目。那种对罹难同胞的大爱,那种对“生命美丽如玉”的发自肺腑的珍惜与敬重,对逝者的悲怆追思,都很容易唤起读者心中同样的情感。从具体的生活现实的启发到完成一首诗的创作这个过程中,您是如何提炼、过滤、升华的?您如何规避简单、直接抒情对写作者的诱惑?
赵:起点是对题材的敬畏。把一切题材视作宗教,虔敬地从中领悟神性。天堂和地狱只隔一个门槛:领悟。静止在领悟中流动,污秽在领悟中纯净,平易在领悟中升华:美在领悟中复活。有得忌轻出,微瑕须细评:创造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如同妈妈教导孩子不可拿取别人的东西一样,作家必须把对别人的发现统统砍掉!舍出身家性命去拥有独特。独特性拥有惊奇感。惊奇感:魅力。
马:您认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要写出一首好诗,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您如何看待想象力之于诗歌写作的意义?
赵:好诗是作者综合实力的体现。喻以剑:人格力量是剑柄,想象力是剑尖。想象力存则创造存,想象力忘则创造亡。当然,这个想象是指原创想象。
马:您曾写作过一批我姑称之为“主旋律”题材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中包括长诗《周恩来》《黑雪》等。一般来说,这类题材的写作是高难度的,难在如何处理好“主旋律”和个人创造及诗意之间的关系。请您谈谈,您创作这类作品的契机是什么?请以这两首代表作为例。创作这类题材比较重大的作品,和创作一般的抒情诗作品,在创作的心理状态上有什么异同呢?
赵:“主旋律”何罪?
无论古今,遑论中外,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主旋律,交响乐的第一主题。在中国,在当下,庸俗、功利、偏狭了“主旋律”,权力有意无意地误读、扭曲、异化了“主旋律”。悲哀的悖论。佛说,一切存在皆有灵性。平庸在雕塑上看出石头,天才在石头上看出雕塑。从石头里开掘出灵性来:主旋律超越意识形态,是美的舍利子。
马:对于新诗百年,请说说您的看法好吗?
赵:中国诗歌的灵魂:诗言志。对应“古典诗歌”,“新诗”在中国诗歌的灵魂部位没能“新”,也不可能“新”。
那么新在哪里?在口语滥觞?在形式散漫?在格律消亡?作为诗的祖国,新诗,尤其当下的新诗,当警惕丧魂失魄。何为丧魂?民族正气,国家骨气,人类大气的萎缩沉沦。没有自己的《长恨歌》,《卖炭翁》,《蜀道难》;没有自己的《塞上曲》,《满江红》,《正气歌》。没有史诗。没有一首第二国歌一般的俯仰天地、长啸血泪的《大江东去》。一己悲欢,杯水炎凉,肱股之痒,指尖之痛:良知和勇气水土流失,当今,中国新诗的手指没有把握在时代的主动脉上。知耻者勇。诗歌不知或知之不深,知之不切。当然,有挟泰山以超北海者在。于是标榜叛逆,于是自诩先锋,于是炫耀现代。
新诗当敬畏创新。一个瑕疵凸显的原创胜过九十九个无可挑剔的复制。创造是艺术品,制造是工艺品。新不难,新得高贵难。更何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创新:太阳照耀需要创新吗?江河奔流需要创新吗?母亲生孩子需要创新吗?玉米结稖头需要创新吗?文学的价值在于它对文学本身贡献了什么。诗歌招魂。尼采说,上帝死了。我说,诗歌是上帝的声音,声音死了。
何为失魄?泥沙俱下,投鞭断流,中国诗歌流失着中国文化的DNA。遗传基因是什么?就艺术层次言,是汉诗特有的“韵律和格律”。新诗自由体。试问时间,自由体自由了吗?從某种意义说宋词是唐诗的自由体,元曲是宋词的自由体。自由,却不轻慢放纵。它们自由得不自由。须深谙“诗歌是戴着枷锁的舞蹈”。须深谙“一切无限都有限”。它们创造自己的韵律和格律,传承并发展中国诗歌的品质与尊严。离弦之箭易脱靶,出鞘之剑谨杀伤。不自由难,自由更难。上帝的声音死了,我们拯救声音。诗人燃烧灵魂,实施以爱救赎。
马:您怎样理解“诗歌时代”?
赵:对于文学,物质时代不是诗歌时代。诗是自由,自由是爱。歌哭之爱,血肉之爱,生死之爱。诗歌藐视枷锁,枷锁是囚歌。再高贵的宠物还是宠物,再美丽的囚歌还是囚歌。物质把爱逼向悬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诗萎缩在爱的萎缩里。战士坚持阵地,诗人坚持回忆与憧憬。在回忆与憧憬之间,缺失现实。歌哭现实,血肉现实,生死现实。于是伪诗人和伪诗如过江之鲫。他们在做四件事:或杯水风波,或顾影自怜,或不知所云,或不齿所或。
伪诗使诗蒙辱。英国人说,他们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诗与非诗之间,诗国当作何选择?
马:如果请您精选自己的十首诗歌作品,除了《我爱》《第五十七个黎明》之外,还会有哪些作品可能入围?
赵:我珍惜我的每一个字,因为它们都是从血肉深处抠出来的。当然,这是敝帚自珍。如果提出一篇偏爱,那就是《大撞击》。置身高新科技时代的文学,欠缺让高新科技进入文学的观念和能力。因而原本应该是全方位覆盖的文学只能触摸到人类认知的半径。这是文学的滞后乃至耻辱。《大撞击》试图让科学进入诗歌。当然,只是试图,也只能试图。现代诗歌试图现代。试图才是先锋。
马:您一直保持着对生活和创作的丰沛的激情,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您写作的动力来自于哪里?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您认为诗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么?您为什么而写作?是出于热爱、使命感,与生俱来的天性使然,还是出于书写的习惯?
赵:不是习惯,不是使命,甚至不是热爱。对于我,写作等同乃至超越生命。
马:请谈谈您近期的写作情况。
赵:我在读书。哪怕一个职业作家,他都应该把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读书。中国作家首先读中国书。读经典,只读经典。读中国经典,努力让自己的文字多一些中国血液、体温和体息。舍本逐末,见异思迁,不智。尤其是诗歌!读书如同登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天下只有一座珠穆朗玛。君不见:古往今来,喜马拉雅山的攀登上匍匐着多少无名阵亡者的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