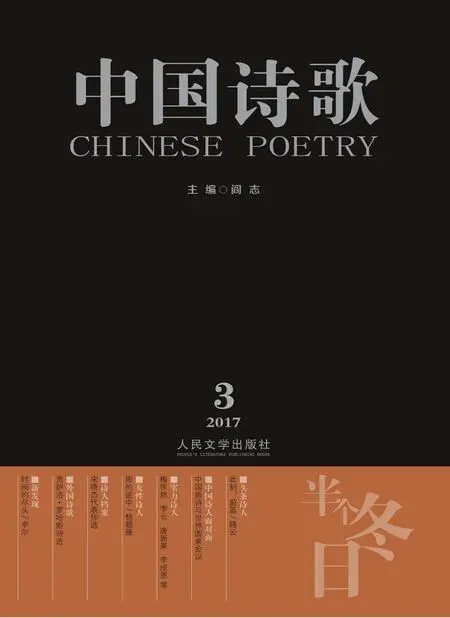贡萨洛·罗哈斯诗选
贡萨洛·罗哈斯诗选
□赵振江/译

你和我是谁在林间
从一棵千年古树
砍下的两块木板。
——《太阳是惟一的种子》
太阳和死神
像盲人对着无情的太阳哭泣
我坚持用空洞的双眼注视阳光,
总是被灼伤。
写在手上的光线
对我有何用?火,又有何用,
倘若我失去了眼睛?
世界对我有何用?
倘若一切都缩小为
触摸黑暗里的愉悦,在双唇
和双乳中啃咬死神的身影,
迫使我吃饭、睡觉、享受的身体
对我又有何用?
两个不同的腹腔生出了我,两位
母亲使我出世,我有双重孕育,
双重神秘,但那荒谬的分娩
只有一个果实。
我的口中有两个舌,
头颅中有两个脑:
体中的两个人不停地相互吞噬,
两副骨架争着成为一根脊柱。
为了诉说自己,
我口中只有一个词语
在我自行折磨的清醒里
我口吃的舌
只能命名一半的视觉,
就像那位盲人
面对无情的太阳哭泣。
始与终
当我在物体中打开自己的门:
谁在偷我的血、我的一切、
我的现实?当我在呼吸,
谁将我抛向虚无?
谁是杀害我自身的屠夫?
啊,时间。多重面孔。
你自己繁衍的多重面孔。
来自音乐之源的雅趣。请你离开
我的哭泣。请扯下欢笑的面具。
等着我吻你吧,抽搐的美丽。
在大海之门等我。等着我
在我永远爱着的东西。
太阳是惟一的种子
我活在现实中。
睡在现实中。
死在现实中。
我是现实。
你是现实。
而太阳
是惟一的种子。
你是什么?我是什么
难道不是借来的身体
在制造影子?
影子是身体
从记忆里留下的东西。
我有父母。
但是已记不清
他们的躯体和心灵。
我的面孔不是他们的面孔
或许只是它们的混合,
只是个阴影。
你行善或作恶。
你是一个事件的起因
然而:你是你的起因吗?
将要求你的给你。
将给你的向你要求。
总之:有进有出。
你丢下自己可怜的影子
如同写在城墙上
随便什么名字一样。
拼搏。睡眠。吃饭。
繁衍。步入老年。
过渡到另外的一天。
其他人和你一样
一点点地死亡,
直至大海将容量用光。
你可曾考虑
那海洋排出的空气?
你和我是谁在林间
从一棵千年古树
砍下的两块木板。
可是谁栽种了那棵树
让我们从它那里出生
又将我们关在其中?
我不认识你,
可你在我心里
因为你在将我寻觅。
你在我身上寻找自己。
我为你写作。
这是我的工作。
我活在现实中。
睡在现实中。
死在现实中。
我是现实。
你是现实。
而太阳
是惟一的种子。
自尽者书
我发誓,这女人分裂了我的脑髓,
因为她出入,像一颗疯狂的子弹,
打开我的体腔,且永不结疤,
夏季或冬季都这样吹过,
这样幸福地活着,在胜利上稳坐
而饱满的胃,像满足的秃鹫,
让我这样忍受饥饿的鞭挞,这样躺下
或起来,像一粒石子
在变化的激流中头朝下沉入白昼,
为了自欺,这样演奏我的古琴,门
这样打开,让十个赤裸的女人进来,
用我的字母在她们的背上做了标记,
她们一些人扑向另一些人
直至筋疲力尽,我发誓,她会长久,
因为她出入,像一颗疯狂的子弹,
时刻跟随我,做我的天仙,
放纵地将我亲吻
企图逃离死神,
当我落入梦境时,她留宿
在我的脊柱里,为我呼喊并求援,
掠我上天,像失去母亲的秃鹫
去死亡中孵卵。
日子过得真快
日子过得真快,在昏暗的激流中
我的任何拯救几乎都缩小为深呼吸,为了空气
在我的肺里多停留一个星期,日子这么快地
汇入无形的大洋,我已没有血液可供安全地游泳
我在变成另一条带着我的刺的盘中之鱼。
我返回本源,走向本源,无任何人
在那里等我,我奔向母体深处
骨骼在那里终结,我走向自己的种子,
因为那里写着:这要在星星上成就,
在我这条可怜的蠕虫上,我还要
和自己愉悦的岁月一起守候。
一个人在这里却不知已经不在,
进入这迷乱的游戏使人大笑不已,
但是有一天残酷的镜子会为你揭秘
你变得苍白却好像并不相信,
好像你不在聆听,
我的兄弟,那是你自己
在内心深处的哭泣。
倘若你是女人,为了自欺,你
会戴上最美的面具,如果你是男子汉,
会让骨骼更加坚硬,但内心却迥然不同,
无物,无人,个中只有你自己:
这样最好把危险看个仔细。
让我们准备好。让我们如实地
赤裸,但让我们燃烧,不能让自己腐烂。
让我们燃烧。让我们毫不畏惧地呼吸。
面对伟大现实在最后时刻的诞生
让我们清醒。
美的朦胧
昨夜我触摸并感觉到了你
我的手没有从我的手后面逃离,
包括我的身体,甚至我的听觉:
都几乎人性地
感到了你。
跳动,
不知像血液
还是流云,
上升的朦胧,下降的朦胧,在屋中
你踮着脚尖,闪闪发光地跑动。
你在我的木屋中奔跑
打开窗户
我整夜都感到你在跳动,
深渊的女儿,好战
而又寂静,多么可怕、多么美丽,
如同一切存在,但对我而言,
没有你的火焰,一切都等于零。
抗拒死亡
伴随过去的每一天,我不得不抛弃这些观点并闭上眼睛。
我不想看、更不能看每一天有那么多人丧生!
我情愿自己是石头,在黑暗中,
也不愿忍受心中软化自己的恶心并对各方
微笑,只求自己事务的繁荣。
我并没有别的事务,只是在这里讲真话
在街上,面对四方:
真实地活着,惟一地活着,
脚踏实地,自由的骨架在这世上。
魔鬼啊,用我们的机器,以思想的速度,
直至跳到太阳,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
即使飞到无限的远方,我们能得到什么,
倘若依然在死去,毫无
在黑暗时代之外生存的希望?
上帝对我无用。任何人对我都无一点作用。
然而我呼吸,吃饭,乃至睡眠
都想着还有十年或二十年,然后便像众人一样
在地下两米长的水泥中进入梦乡。
不哭,我不哭。一切该怎样就怎样,
但我不能眼见那么多棺材
过去,过去,过去,每分钟都在过去
装得满满的,满满的,我不能眼见
棺材里的血还在发烫。
我抚摸这玫瑰,吻她的花瓣,
我崇拜生命,不疲倦地热爱女性:
在她们身上开创世界,提取营养。
但一切都是徒劳,因为我本身
是一个无用的头脑,不懂得
期望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意味着什么,只有准备好被砍掉。
人们和我谈论上帝或谈论“历史”。
我嘲笑自己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寻找
吞噬我的饥渴的理由,生的饥渴
就像优美的天空中永恒的太阳。
煤炭
我看见一条激流像刀一样闪光,
将我的勒布劈为两部分芳香,
我听、嗅、抚摸,像当年在孩子的吻中
游逛,当我在风雨中摇摆,感到
又一条动脉在我的双鬓和枕间跳荡。
是他。在下雨。是他。
父亲湿漉漉的来了。一种
骑着湿漉漉的马的味道。
父亲骑着马穿过一条河流。
这不稀奇。暴雨夜垮塌下来
如同被淹的煤矿,一道闪电使黑夜震颤。
母亲,他就要到了:我们打开大门,
给我这灯盏,我要在兄弟姐妹们之前
迎接他。给他一大杯葡萄酒
为他驱赶疲倦,让他给我一个吻,
将蒺藜似的胡茬刺在我的唇边。
男子汉来了,满身泥泞地
来了,对厄运满腔怒火,对剥削
义愤填膺,饿得要命,从那里来了
披着他那西班牙人的斗篷。
啊,不朽的矿工,这里
是你亲手建造的橡木的房屋。
快进来:我在等你,
我是你第七个儿子。这些年多少星星
划过了夜空,我们在一个可怕的八月
埋葬了你的妻子,没关系,
因为你和她已经成倍地延续。
夜晚对我们两个是同样的漆黑
这没什么了不起。
——进来吧,别站在那里
看着我,没看见我,冒着雨。
相爱时爱什么?
相爱时爱什么,我的上帝:生命可怕的光
还是死亡之光?追求什么,找到什么,何谓爱情?
谁是爱情?是带着深邃、玫瑰和火山的女性
还是彩色的太阳即我愤怒的血液
当我进入到她最深的根中?
或者一切都是伟大的游戏,我的上帝,
没有女人也没有男人,只是一个身体:你的身体,
分化成美丽的星星,昙花一现的粒子
它们属于看不见的永恒?
上帝啊,我死于此,死于她们当中
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战争,由于不能同时
爱三百个,因为我注定只能爱一个,
那惟一的女人,你早已在古老的天堂为我选定。

勿学庞德
请勿效仿庞德,请勿效仿埃兹拉
美妙的效仿,让他用波斯文、梵文、
开罗-阿拉米文书写他的弥撒,
他用学了一半的中文,靠查字典
半通不通的希腊文,华而不实的拉丁文,
自由、浑浊的地中海,用九十年锲而不舍的技艺
才摸索到那伟大的难以辨认的“孤本”;
请不要片面地评判他:要聚集所有的微粒,
从有形到无形,都要编入瞬间之物
和静止琴弦的经纬;让他宽松
盲目地看之再看,因为那就是词语:看,
那“精神”,未完成之物
和燃烧之物,的确我们所爱
和爱我们之物,既然我们是“男人”
和“女人”之“子”,归根结底是不可称呼的无数;不,语言
新的歇斯底里的半神们,没有标识,创新奇才的学徒们,
不要偷太阳的影子,想一想那颂歌
像萌芽一样在闭合时开放,请化作天空,
像老迈的埃兹拉一样的天空之人,总在危险中,
请无畏地从词语跳向星星,矛盾紧张的拱门
在一切可能的速度中,天空和更多的天空
为今天也为永远,
高贵
同时爆发的以前
和以后,旋转的瞬间,
因为这眨闪的世界会流血,
会跳出它终会死亡的轴心,永别了
阳光和大理石、还有狂傲富饶的传统;嘲笑埃兹拉
和他的皱纹吧,嘲笑吧,从此时到彼时,但不要将他掠夺;
嘲笑吧,像灰尘一样过往的轻浮的一代又一代,
文人墨客的子孙们,嘲笑吧,嘲笑庞德
和他背负的巴别塔——如同他者的警告
在其语言中曾经有过;颂歌,
缺乏信仰的人们,想一想那首颂歌。
邂逅古瓶——致伊尔达,我在南京见到她。
这一行以拍摄七刃折刀
开始,她像最后一尊大理石的女神
在巴比伦的市场上舞蹈;
我在梦中杂物里将她拾起,像面对
底格里斯的雌鸽咕咕发情,
用我的吻将她洗净。
我失去这诡秘的女人已经很久,
在此期间几度重生,在所有的门后
将她寻觅,从帝国的罗马
到纽约抽搐的天空;于是我回到亚洲
沿扬子江寻找,多么清醒
似乎为了此刻见到她,“真的见到她”:除了
在华丽的南京,一个缥缈的饭店,
还能在哪里,在动情的纯洁中
如此轻盈,在青铜色
油脂的清爽中如此深邃,
在汉民族阳光的均衡中
如此的皇家气派,除了那里
还能在何处,
在那里,
在眼前,
在静止中
多么敏捷,伊特鲁里亚
女人笑容满面
在天然芬芳中的冒犯,
在古坛
秘密的伪装下,
在平衡中
盲目地令人
眼花缭乱。
“发现”并非赞歌
而是将发掘永远地失去:
再见了:挥霍;
再见了,迷人的魅力。
镜头
将这场景关闭。
音乐会
大家合写了那本书,兰波
描绘了元音的轰鸣,谁也不晓得
基督那一次在沙滩上画了什么!
洛特雷亚蒙长长地嗥叫,卡夫卡
好像用稿纸点燃了一个焚尸炉:
从火到火;巴略霍
没有死,他遍布悬崖,如同
“道”充满了萤火虫;其他人
无影无踪;莎士比亚
用一万只蝴蝶搭建了场景;
此时自言自语从花园经过的人
是庞德,他在和天使们
将一个表意符号讨论;
卓别林在拍摄尼采;昏暗的夜晚
沿着太空,从西班牙
来了圣胡安,戈亚,
身穿小丑服装的毕加索,
亚历山大的卡瓦菲斯;其他人
像赫拉克利特一样,躺在阳光下
彻底酣睡,萨德,巴塔耶,
布勒东本人;斯威登伯格,阿尔托,
荷尔德林,在音乐会前
伤心地
向听众致意:
那时
流血的策兰
做了什么
在那里
面对着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