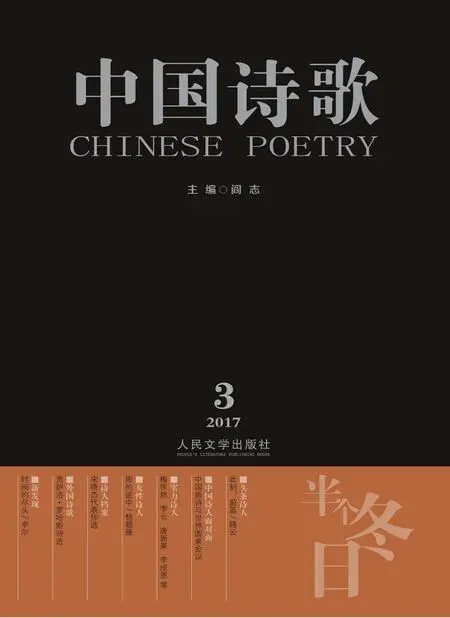此刻,蔚蓝·组诗·
此刻,蔚蓝·组诗·
□路云

路云
1970年生。受聘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授创意写作。研究方向为创意写作和当代汉语诗歌句法。出版诗集《望月湖残篇》、《凉风系》和《光虫》。
经过
一只内向的苹果在胃里
大声说话。
我边接手机边走过两个红绿灯,
对方手机里突然冒出
一个鸡蛋磕在碗口的声音,
然后是搅拌,
然后什么也没有了。
正好横过斑马线,
那么多车灯一齐盯住我,
我没有说请原谅,
谢谢,再见。
当它们从我身后猛冲过去,
手机又响了。双向车道,
右边塞得比左边严重多了。
空盒子
盒子里剩下一支烟,
把它取出来,一分为二,
屋子里就有四个人,
同时陷入孤独。夜晚是完整的,
空盒子因为空,
抽身离开。我从未想到过自杀,
但抽烟很凶,你也是。
多年后想起这个空盒子,
在另一个房间,你把脸转过来,
盯着我。目光突然拉近,
空盒子把我们同时装进去。
夜色没有因为点燃,
冒出细小的火焰,孤独也是,
空盒子随之化为灰烬,
具体到双手来说,可触摸到你。
冲动
绝壁上什么也没有,
除了一根绳子,系在你腰上。
我听不清你说的话,
声音陡峭,几乎没有踩脚之处。
我摔下来多次,
疼痛因为找不到伤痕,
你不信,我也找不到语言,
来复述。长这么大,
绝望过一回,而现在我怀疑,
这是不是绝望。因为,
凡是被描述成绝壁的地方,
我几乎去过,而且说不出快乐。
它把我抓得紧紧的,生怕我
掉下去,我时刻
有着把这个说出去的冲动。
岩石
下半夜,从半生不熟的
睡梦中
渗出的一钵米汤,
把胞衣像一件旧夹衣
浆洗过后,泼在桂花树下。
月光比平日硬扎,
我独自享有岩石般的沁凉。
一股从未有过的活力,
令月光变得勤快,
它一轮轮浆洗自身,
和你叠好的影子。
月光和米汤,把岩石感
从岩石中取出来,你把它
抱在怀中,我叫它凉风。
反转
把腿伸到意识之中,用掌腹,
连击它的膝盖,
脚老在抽筋,我四处张望,
仅有一人用余光看我。
雨突然停了,
一滴水滴进我的鞋套,
我爱上划船,不,是雪橇。
一种速度追不上另一种速度,
能够腐烂的东西都不会,
停止奔跑。
失眠与外墙渗漏谁更坏,扯不清,
需要防水漆一大桶,
腻子粉两包,一般情况下,
会送一个滚子或两把刷子。
问题是两者我都想要,
结果是空着手来空着手去,
来来回回跑一下午,直接耗掉的是,
进入睡眠的时间。多好啊,
醒来,想都没想就把脚伸进一双拖鞋。
不对称
我乐于看见鸡同鸭讲话,
狗追猫,
笑声落在地上,抓不住。
花朵在春天走得真快,
追不上,并没有失败感。
雨水不同,它找到骨头
与骨头之间的缝隙,
我害怕霉味,它害怕阳光。
一片绿叶所理解的,
我不能。你证明脚跟比
树根进化得更彻底,
草坪上,我试着站了一整天,
没有任何一只鸟,
在我乱发中飞来飞去。
噤声
鸟一叫,她就跳舞。
身体表层,
像海水溜向港湾泛起波浪,
整个儿,
比八爪鱼还八爪鱼。
见过野天鹅,孔雀的我,
忘记曾见到过蜻蜓,
河堤上草丛中,
不是刷过透明漆的木地板。
原谅我在一分钟后,
想起这些,并愉快地想起泥鳅,
在我手心里,
表演过类似的动作。
那时,还不知道舞蹈这个词,
这丝毫不影响我,
在一块空坪手脚同时挥动。
那会儿有没有鸟叫,
不知道,但有一个刹那,
盯着地上的影子出神。
极限
站在悬崖边石头一角,
想说的话没了。
双腿哆嗦着,代替另一个人,
说个不停。咳,这家伙,
为什么不配合一下,
哪怕一分钟。我痴迷于极限,
边界只是其中一种,
表演完毕,丢下一句话,
像丢下一块石头。
话或者石头,不可能悬在空中。
在沉默中,我把头抬起来,
双手开始发抖。假定你
站在云块上,重复刚才的动作。
我常为这么想而感到后悔,
并坚信此刻,
双腿沉默,不是为了配合。
距离
在两只刺猬之间找到谜底。
反过来却很难,
有时一只都找不到。
很简单,你离它太远,
认为它不存在。
我变成兔子你变成菜叶,
零距离接触,结果兔子怀孕。
我爱上刺猬时很直接,
血液距离痛太近,不怕,
太远,什么都不爱。
你不信,拿曲尺一量,
左边三公分,要用右眼看。
右边刚好。经常笑出眼泪的人,
喜欢仰泳,你这只旱鸭子,
快跑。被腌过的月光,
又咸又腥,我祝福过你。
通过榨汁机爱上水果
通过榨汁机爱上水果。
水果还是楼脚下佳乐超市的,
不同的是这台榨汁机,
原装德国货,
声音小得就像胃壁在蠕动。
以前的那台发动机,
把我想喝点什么的想法,
直接打成泥浆。对德国的敬意,
除了文字,还有机器,
包裹其中的一种螺丝钉精神,
将我伤透的脑筋回炉,
车出螺纹,它们伸出手臂,
等同于枝条伸向春天。
花朵与果实,蜜蜂与甘甜,
轻易找出人与自然的连接方式。
半个冬日
阳光透过玻璃变得纯粹。
一个下午躺椅安静得
像某截古老的枝丫,
伸展在半空。有不少词句
闪现,又滑入沉寂。
对不起,我不想捞起它们,
为什么?我也一样,
接近液化的临界点。
词,完全溶解在透明中,
与透明的体温一致,
呼吸一致,没有一丝缝隙。
我闭上眼睛又微微张开,
有一种冷,变得纯粹透明,
浸入我的全身,
平缓,清晰,坚挺。
先是摇动双腿,然后把整个人,
拉直,双手自然伸平。
左手停在躺椅上方,右手尖
几乎触到悬在山顶的光盘。
我在凉台上,看着它,
轻轻拨开一根细小的唱针,
又放上去,反向转动,
释放出一种同样精确的威力。
把苹果削好给你
把苹果削好给你。
空气太紧张。我顺便
把长在话里头的核,
剥开。白得刺眼。
你将啃了两口的苹果,
递到我嘴边,我啃了一下,
代替平时说话吵嘴。
我不知道诗意是什么,
我不相信语言。
我愿意不停地削苹果。
苹果皮堆在你脸上,
继续生长,凉沁沁的,
我歪着头再啃一口。
感恩
被身体忽略的影子
穿过一排柳枝,停在湖面上。
秋天的后半段,
你盯着它,它不会下沉,
偶尔被一只鸭子掀开,
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好奇身体的全部,不是你
奔跑行走的样子,
双脚明显比双手粗壮。
是什么确保它们跌跌撞撞,
而不至于悬在半空?
我猜,每个人的身体,
对应一块同样重量的石头,
或者一句话。包含在这里头的
轻与重构成一种平衡:
谨防在某个晴朗的早上,
全部的身体,与它长长的影子,
签下一个试飞合约。
假日
假日在最后一天变得温驯,
无限接近湖水。
滑过去的每个日子都像回头鱼,
重返此地,在这儿产卵,
把憋住的轻叹浓缩为细小的颗粒,
透着橙光。它看不见我,
在困倦中闭上双眼,又在来年打开,
触及某个边界。
没有什么能把不由自主的脚步声,
转换成一个生锈的铃铛,
在俯身向下的坡道焕发异彩。
风吹动湖水,它的皱纹里传出
一阵虫鸣,万物闪身进入另一个频道,
那时你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山头,
眉心起跳,目光一根根如棉线散开,
又自动翻卷,恢复纺锤状。
冰箱里的雪糕
雪糕搁在冷藏室第二块隔板上,
被一层保鲜膜裹着。
想起它的念头,同样柔爽、嫩滑,
搁在体内哪一层隔板上,
尚不清楚,
眼睛与手听命于它发出的指令。
鼻子首先嗅到腊肉的火熏味,
从冷飕飕的风中窜出,
不妨碍右手径直伸向雪糕。
我在剥开这层膜的时候,
觉得这玩意儿真好,
至少在我享受一种味道时,
免除另一种气味打扰。
我的双唇像冰箱门一样合上,
又拉开,一阵凉风吹来:
某日雪糕般保存在这个刹那之中。
祝福

苹果在电脑上浮现,
手臂伸出去和一根枯枝伸出去,
几乎同时。
我藏在水果香味中,
清扫落叶,从早到晚。
苹果消失了,一阵倦意,
将我带走。那儿,有一枚
浑圆的,风一吹,
就闪烁出种种波光的果核。
射向它的目光,
自动弯转,旋入停顿之中,
你一愣,就被一颗石头击中。
屏幕上飘出大朵的雪花,
请原谅,刚才不知道碰到它的
哪根神经,而我浑然无觉。
波光
一抹波光在水面上抡起臂膀。
刹那间,帆的影子被切成数段,
埋藏其中的阴郁与平静,
剔除浩渺中起伏不定的目光,
和难以测度的重量。
忽视它们的是一瓶农夫山泉,
把它倒进海水,转瞬就成了蓝色。此刻,一艘船飞快地掠向对岸,
掀开雪白的裙边,没有人四处打量,那友好的斧柄脱落何处,
可能是它顺手劈开无声的喝彩。
阴影
1
没人在意阴影标出光线的
角度和大小。站在一棵苦楝树下,
肯定比站在梨树下安静。
我在乎阴影带来的一点相似。
如果你说芝麻,我说蚂蚁,
我们就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我说一棵好大好大的树,
你说没见过,那好,再见,
如果你说黑暗,我一惊,
随即把这个难以察觉到的反应,
藏在一片叶子中。
你轻易将它从任何一抹阴影中
拣出来,我站在那儿不动,
一阵风过去,它从不留下什么。
2
心中的一块石头不见了,
我差点飘起来。
这是昨天下午的感觉,
而现在,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不见了的石头留下阴影
比石头更重。
我团团转,急于抓住什么,
而什么都晃个不停,
我坠落在地,抢在那块石头前。
它的重量把我摁住,
无法说出的快乐变成一个坑,
雨水从中漫溢出来,
悄悄沿着树根渗入一片阴影,
某个时刻可以拧出水来。
3
桂花树的阴影在月光下跳舞。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回到书桌前,
模仿其中一个动作,
从阴影中跳出另一个阴影,
有淡淡的香味。鼻子与眼睛,
瞬间交换位置,指头在键盘上疾走,
惊动一群野鸭在真空中飞行,
鸣叫声,偶尔在半夜
发出磷光,照亮同伴的羽毛,
其中一片掉下来变成钻头。
阴影中有不少陶片,碎骨块,
木桶铁箍,我在哪里见过,
没见过的是直立行走的水,一下
冲过我头顶,一下爬上脚背。
4
三伏天经过路边一棵樟树,
无意中触到阴影的表皮,
它提示另有一个世界我进不去。
我在我的世界,用脚尖
触到它的脚跟,贴得再紧,
也无法深入。今天下午七点,
落日停在山顶,在卷走它的沉默
之前,书页般翻开背面。
这不能阻止我歪着脑袋想,
为什么不用脚板踩着我的脚板,
或者让头正对着我的头?
想着想着,我就多出一份小心,
脚步尽量放轻,不时把头抬起来,
穿过某朵白云撞向它的腹肌。
5
语言在孤独时变成气流,
不是落叶。它拧干体内的水分,
舍弃躯壳、花岗岩底座,
俯身取走一件轻纱。
在孤独中,我举着空火把,
燃烧着的光没有灰烬。
我溜进我的阴影中,它说话,
行走,发烫或者冰凉,
化身为一棵花椒树,
留下各种气味。而我,
在不同形状中测出那张嘴,
那双眼睛,同样清冽,
均匀,被一阵凉风吹向此刻。
洒水车掉头,扫向左侧,
中断我与它彼此交替的游戏。
2月14:铁树开花
有人喊你。假装没听见。
快乐从手心里冒出来,
一把镊子夹不住
我的鸟嘴,
它们消失在通往酒精棉球的路上,
影子溜进玻璃瓶。
铁树开花,我止步,
大朵的乌云在半夜被一场暴雨擦得
嫩白,你的玩具猫喜欢装睡,
我揪住它的头发,
没用,踢它的小屁股,没用,
这个时候,谁哭一下,
谁就是我奶奶。裤兜里有一个气球,
触摸到它,我立刻安静下来。
荷叶
从东走到西。三公里变成两秒钟。
一个人的脸上挂满微笑。
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微笑比春药安全,
长时间大剂量使用,会使一张衰老的人皮,
变成谜。湖水浑浊的原因,
是晨跑的人扰乱柳枝摇摆的节奏。
你在荷叶上面练习冥想,
混乱比什么都有意思,
我爱你连说十遍,
变成栀子花开在隔壁家的灶台上。
逃到另一种节奏中去,
白色就已红透。
在微笑中,我们是任何人。
幽默感是小船摇向零乱的倒影,保持水的清澈。
好心情把世界缩小成一滴露水,
能完全溶解的,不被污浊的,
除了八九点钟的太阳,还有此刻的负离子。
雨正在下
老婆喜欢啃苹果。咔嚓咔嚓,
这个节奏让早晨变得安宁。
树上有几片叶子对绿色的理解,
多如我对羞耻的理解。
没人喜欢脸红。
但一张红着的脸让人觉得踏实,
新鲜,甚至冲动。
我一高兴就自动嚎叫,
初次听到的人有点紧张。
现在轮到你,用刀子啃苹果皮,
牙齿不能发抖,
那……那……那是什么,
疼痛化成一种声波塞满半个宇宙。
请把快感分解成颗粒状……
明天
一个词消失在白云深处。
雨滴的一部分与你的猜测相当,
别去怀疑那些在夜间开放的昙花,
幽香与门栓互通信息。
今天变成昨天,
白蜡树影子刚好覆盖一片荷叶,
未来用水蒸气代替爱情,
我们进化成雌雄一体的异类。
橡胶树诅咒过的马路越来越宽。
雨下得大下得小都一样,
如果停下来停得太久,我不知道,
请让我抬起头,想一会儿。
雨滴在想象中比蜜蜂勤奋
在够不着的地方,翅膀是优雅的,
藏红花不打瞌睡。
一颗葡萄比星星多出两片叶子,
透明的夜晚有一股长时间的甜味。
我相信滴溜溜的眼珠子,
它看见云的方式一度落后于风,
高于手,但奔跑的样子可爱,
从凹透镜跳到凸透镜,风就停了。
黑暗默认部分器官罢工,
不影响春光一寸一寸被当成菜蕻子掐断,
今天白灼。手和筷子的结合,
不如舌头与遥远,无意识是什么?
一片洼地,位于你的中指与食指中间,
下雨天别把抽油烟机打开。
此刻,蔚蓝(组诗)
秘密警察
杜甫的草堂为何瞬间变成一个窟窿。
我低下头,密西西比河上游的一只蝴蝶,
从压在《全唐诗》下面的画册中起飞,
她的翅膀在阳光下,翻开合上的线装书页,
一组对句裸露在庞德的眼中,
秘密敞开:一场暴雨令河水变得欢畅。
我双掌合十,仿佛蝴蝶停在手腕上,
此刻,问题把我搁在鼻尖,
几根稻草在河边飞起来,又落下,
风没有吹乱头顶上空一连串的鸟鸣。
我认出一只九头鸟,当它再次叫起来,
我感觉逮住了它。
它没有去过巴西。
去亚马逊河的冲动消失在一条脚注中。
十七个月后,一阵龙卷风钻过墙壁,
书柜背部的缝隙,渗入我体内,
霉味把思考界定在一面朝北的墙。
半个苹果被早晨啃光,剩下的一半,
站在一张餐巾纸上对我说话:
是时候了。它们合成一个完整的念头,
我说:吃过了,谢谢。
北风透过窗玻璃像一个不太负责的邮差,
说有一封你的快件下楼来取吧。
来自各地的多条线索,被一个门牌号码,
轻易锁定。如果你抬头细看,
有一只蝴蝶放弃飞行,停在你头顶上方,
把昼夜的更替和刹那间的幽光,
转换成一串数码,它们穿过被锁住的空间,
破译出疑团:秋风受雇于某个没有日期的邮戳。
这意味着一个拆开的包裹不是窟窿,
垃圾桶也不是,他们未能阻止我重新走进书房,
笔录开始:我只写过一个开头,是的。
小纸团
一页刚写下开头的纸被撕下来,
揉成一个小纸团,
引出一个惊雷:我闯入体内那片热带雨林。
无人在意此刻有一丝惊慌,
被键盘捕捉在一个废弃的词中:轻笔。
二叔两个弯曲的指头没有出现在额头上,
我无法删除这个词,
它是一块巨石嵌入崖壁,
砸碎仰望者的目光。
写作是低下头,看着一个个指头在黑键上疾走,
赶在一个系统崩裂之前,把自己逮住,
交给回声。它说出你历经的一切,
现在,转换成一丝微笑从嘴角上掠过。
小纸团如何变成一滴水,
从一片叶子跃向一块劣质镜片,
跃进一行诗——
我以为抓住了它的影子,
而它在风中飘荡,多年以后,
解密的信息,对称于一阵凉风。
一个人绕着自身的轴心转动,
直到把孤独搓成一个纸团,扔到麓山脚下,
等着,它自动张开,如同一张打印纸,
从硒鼓的眼皮底下溜向书桌,
有点烫手,又归于沉寂。
时间比碎纸机先进,它留下的完好无损,
交给你——凉风——环绕于大地,
接着写,就是这张纸。
疑点:父亲
二叔的两根指头和我的一支笔,
作为小纸团之父的嫌疑人,健在,
不能同时出庭:着急的是我,
如何对着一只乌鸦说出我的口令。
父亲,父亲。我抓周抓到你父亲留下的
英雄牌金笔,你抓到我,
一个奇怪的阄儿,皮包着骨头,
这是什么征兆?我的父亲是一根麻绳,
一端紧扣打谷机踏板的中间,
另一端把肩膀变成支点,他赢了:
独自拉动一个时代,在泥沼中前进一米。
贫穷的父亲,富贵的父亲,
都是一顶帽子,戴在同一根手杖上。
卓别林的笑声从西半球传到东半球,
不变形,你看见你的阄儿,
经过他的手心变成一枚野果,
任由星光落在上面也不吭一声。
它对称于一颗小矮星,椭圆形的父亲,
迈着狐步,跟上它。跟上。
疑点:两只蝴蝶
小纸团突然失踪。一个声称找到它的人,
在餐纸上画下鳞片,
五月的空气能拧出水来。
两只蝴蝶同时抓住一根枯枝,
一个说:咸,
另一个说:腥,
它们都不知道哪一片叶子
卷走了肇事者的令旗?
请允许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勇士,
来点儿石灰水,来点儿西洋参,
来,把酵母粉撒在活死人的脸上,
野草比胡子还顽固。你,扎着辫子,
银色西装套着一条苏格兰围巾,
上面有几只虱子的魂灵,
叫声刺耳,让人出虚汗,失眠多梦。
订书机说,它是一根失去弹性的曲别针,
夹不住硬骨头,
和一本用繁体字印刷的《野草》,
一只蜻蜓从里面飞出来,它有四个翅膀。
时间挣脱韵脚,新的节奏是在荒野上,
赤脚奔跑,没有方向。
疑点:蛹
在黑暗中奔跑的人,一张瓜子脸,
没时间搭理我们,
炭盆摆在堂屋中央,
取暖的人被寒意追着不放。
我,被监听,
被一只小小的蛹卷走,
变成另一个纸团。
由对称所释放的张力,扰乱人的心智,
没有一个脑袋是空的!
最新的说法是,第一个把酒装在靴子里的人
是勇士,他蒙住双眼,
打赢第六场躲猫猫模拟战争。
一只老鼠标准的鸣叫,压在右手第二个指头下面,
我想起母亲,把胆汁涂满乳头的是她,
吃奶吃到七岁的人,是我,
我正在把自己掏空,白色汁液洒落一地。

疑点:空葫芦瓶
喝多了龟蛇酒的人,眼睛眯成准星,
窗台比枫树尖矮一厘米。
先是一桌人消逝,然后是一整条街,
最后是他自己。回忆缠绕在银环蛇的影子上,
一堆碎龟甲骨拼出半个古方,
老家伙红光满面,我不喜欢洞庭湖,
没有一只海鸥,全是麻雀,把朋友送来的铅弹,
交给死神,我真是活腻了,
你不知道,每一根神经都已退化成钢丝。
掉下去的人,化装成麦子遍地发芽,
来,最后一坛,喝完就成了秘密。
这年头,指甲不能信任,看,竖条纹,
自动解禁十年前的信息,
跟上来,跟上来,各就各位。
能够做到的只有一块石头,飞过你的秃顶,
放心,没人敢触碰那个削尖的脑袋。
打开它的是意外——那把空葫芦瓶,
眯着眼睛:别烦我,没有!
疑点:蓝墨水
上游是一块虚拟帆板,挂在水墙上。
首个指令输入:借我三滴蓝墨水。
那时候,不流行打借条,也不会撒谎,
说出口的话,就会是米斯特拉型,
风不会被禁止,问题是如何理解一个翅膀。
它在水面上标出的红线,
偶尔在眼眶里闪现。风暴就是如果。
这个词从脑海中浮现,
如果——你知道,我会把这个异兆修改成
绝对纪录。相信我一定会登上这座小岛,
一颗星把你的滑行线路拉直,
远方把一块手帕染成纯蓝,
再借我一滴,就一滴,
我咬紧牙,仿佛什么都能压成一块帆板。
来吧,掀开那张用了多年的桌布,
挂在你笔挺的身上,一个问号拉伸桅杆,
漂流即审察:此刻,蔚蓝。
月光照着芦苇
那个把月亮作为反光镜的人,
在深夜疾奔,经过任何人的梦境不被烫伤。
他从死者身上取走钥匙,把失眠者
关在同一个时段,记住:黑色在身上涂抹七遍,
可摆脱一只电子狗的追踪。
我看见你从一根枝丫上掉下来,
蜷缩成一个苹果,咬一口,打开另一条通道,
请息怒,他是谁?他不是月亮村的公民,
原因是他打碎一面镜子,
把我放了出来。我什么也不是,
把怒火交给众人,甲咬一口,西红柿,
乙咬一口,火龙果。对不起,这里没有对不起,
只有画圈圈比赛:画得最圆可以免除死刑。
但活下来的都是茄子,土豆。
它们不会撒谎,
谎言就是在绝对意义上画出一个圆形,
令人着迷。我开始奔跑,
两只黄鹂消失在长江中下游——
一个有名的闸口:它拍下的照片被回头鱼
运送到每一个采风者的舌尖。
双桨把我和众多镜头绑定在逆光中。
老船工把一张空网撒进艺术家嫩白的手心,
没有谁留意到他把刚捞上来的小鳊鱼,
拿去喂狗。他们拿这些照片去喂猫,
不同之处在于猫的叫声撩人。
这不会增加我作为本地人的难堪,问题在于
那些赞美的声音像狗叫。
他们的底气在于看过芦苇荡一眼,
照片能够证明:按动高级相机快门的声音,
远不及一只野鸭嘎嘎吃着小鱼的声音。
关于芦苇,请随我来,
在一片废弃的钢筋货场,盘腿坐下,
笑过之后,就会慢慢沉浸在一种荒凉里。
你逃不掉。而我不想逃。
我会在新版仿宋字体中找出一行白鹭,
它们从沃伦的诗句中飞回来,
在芦苇丛中悄悄鼓动双翅。
理想的夜晚
我的理想是用月光把自身清洗干净,
一遍又一遍,
直到消失,不留下任何踪迹。
在那里接受凉风的造访,
你不存在,不妨碍我们用另一种语言交谈。
为什么是月光,而不是叶绿素?
那只是一种假设,万物隐藏在各自的反光中,
我只是我的见证。我的一切,
早已溶解在月光中,它把它收集到的信息,
还原成一切。这是一个理想的夜晚,
没有加速挡,没有刹车片,
没有鸣响的警笛,
甚至没有源头,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出口。
你坐在凉席上,望着四野的虫鸣和星光,
我问你什么在叫——你说:星星。
一股敬意从内心陡然升起。
我的脑袋靠近北方,
双脚沿着相反的方向,在南风中疾走,
我绕着自身的轴心旋转,
从未离开自己半步,
也不可能,我时时醒着又睡去,
东方隐约可见,一个邮差模样的人,
取走我的影子。我已没有影子,
也没有反光,它们被一个词锁住,
一个词打开另一个词,测出我的频率。
我是一个片刻。一次意外。
一阵风。从一个夜晚飞进另一个夜晚,
月光溶解在水里。漫长的雨季,
把我重新扔进一间小屋,
窗子向西面敞开,一阵雨滴猛击夹层玻璃,
我说:你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