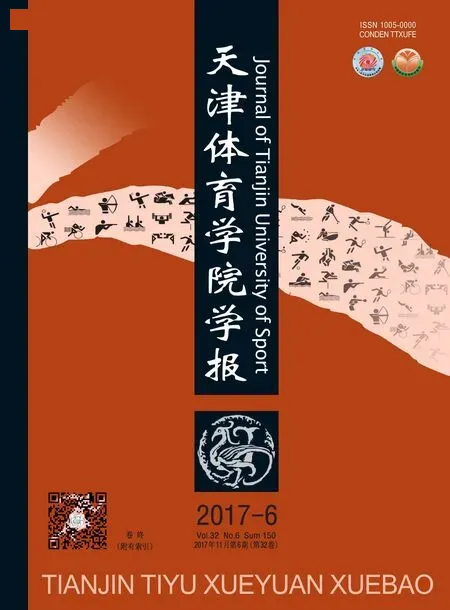现阶段我国体育概念新说:基于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视角
黄尚军 ,郑 勤,蒋红霞
长期以来,体育活动的动态变化常使人们难以把握“体育”的内涵与外延,困惑于如何给“体育”一个公认的概念。通过考察“体育”一词的历史演变,发端于古希腊的“体操术”,卢梭和斯宾塞倡导的“体育”都是“体育”的不同表达。“体育”自清末传入我国以后,经过不断演变,发展至今以“大体育”(Sport(s),S)与“真义体育”(Physical education,PE)2种界说最为盛行。因此,从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2个维度加以分析,将会形成一种较新的走出“体育”概念困局的思路。
1 体育概念争鸣的由来
__“体育”是一个常用,却难以给其下一个准确定义的词语,如我们说某人喜欢打球,经常可以表达为“某人喜欢体育”。但熟知非真知,谭华在《体育本质论》一书中就梳理出30余个不同的“体育”概念.正如杨韵[1]所说,体育“动态的发展式本质属性,使得对于稳定而具有普适性的真理的追逐变得遥不可及”。
在国外,一般把古希腊的“体操术”(gymnastiké)视为最早的体育,其原意是一种裸体进行训练的技术。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指出,体操术是市民教育的2大范畴之一。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个专门表示身体教育的名词——Éducation physique。关于其来源,一说是1762年出版的卢梭名著《爱弥儿》中使用了该词[2];另一说是,巴勒克泽尔于同年发表的论文Dissereation sur I Éducation Physique des Enfanes中首先使用了该词[3]。较为一致的是,1808年,居里安所著的《教育概论:身体的、道德的和智力的教育》中所讲的“身体的”教育的部分,被认为是体育概念的雏形[3]。斯宾塞于1861年将《体育》篇章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智育》《德育》等3个篇章并列出版称为《教育论》,明确地把体育置于教育之中。此后,西方一直把学校教育中与身体活动、身体健康和身体锻炼相关的课程称为“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一个能表达总括身体活动的专门词语,但与古希腊“体操术”相似的身体活动却长期普遍存在,如射箭、骑马、投石等;与古希腊教授身体技艺的“体育馆”功能相似的场所也比比皆是,如奴隶社会的“序”、封建社会的“武学”等。据张天白考证,“体育”一词最早引入我国并见于文献应是在1897年,释义为“体育者,卫生之事也”[4],即“养护生命,促进成长”。但在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中率先出现的是“体操”课,后在1923年北洋政府《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改为“体育”课。
新中国成立之初,青少年营养不良、健康状况恶化迫使学校体育活动与卫生保健工作相互结合,体育与卫生并列出现。为快速提高我国竞技运动水平,助力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195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工作方针,出现了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等3种“体育”并存的局面,并被1995年实施的《体育法》法定化为“体育”的3种类型。2000年12月,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高中《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体育课程更名为“体育与健康”课,发生了名称上的第2次变化。
通过上述考察,国外从“体操术”演变至“体育”,国内从无统一名称到出现“体操”“体育”与“体育与健康”,再到“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等多种名称的出现,其内涵与外延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变化。就连与汉语“体育”对应的英文也有不少,如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activity,physical training,physical culture,sport(s),play,exercise和game等,即使是常用的工具书也未见统一表述。其中,最惹争议的是汉语“体育”究竟指的是sport(s),还是physical education,这与我国理论界关于体育概念的争鸣主要集中在“大体育”和“真义体育”之间有关。
熊斗寅是“大体育”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1980年就提出“体育”要有大概念的观点[5]。他论证道:按照整体性原则,根据我国的体育实践和约定俗成的叫法,应使用S作为“大体育”;S最能反映国际体育潮流,是可以涵盖社会体育、竞技体育、体育教育的总概念;再或者,从概念本土化的角度出发,可把更为简洁的汉语“体育”(TIYU)作为概念推向世界[6]。20个世纪80年代,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体育概论》也采用了“大体育”的观点,认为“广义的‘体育’,又称‘体育运动’作为总概念,包括狭义的体育,和竞技运动、身体锻炼与身体娱乐。狭义的‘体育’是指身体教育。”[7]
此种“‘约定俗成’的定论或范式”[8]虽不能令人折服,却得到很多学者的响应。崔颖波[9]研究认为,“体育”在日本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分别是“身体教育”阶段、“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阶段和“运动教育”阶段,照此比对,目前我国正处于“运动教育”阶段,因此,以“运动教育”释义“体育”较为恰当。魏立宇等[10]则认为崔颖波的观点有误,理由是:崔对身体的认识深受身心二元论的影响,这已经在哲学界被扬弃了;“运动”应与human movement对应,人们将之与sport对应是习惯问题,是不严谨的;把我国的体育划分为3个阶段的标准缺乏依据,日本体育的3个阶段划分也不具有普遍意义。对此,崔颖波反驳道,国内“体育”已不限于学校,也不限于学生,教育范畴内的“体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日本政府部门和法律的名称都说明“スポ—ツ”是日本体育的总概念,美国、英国、德国等均把一般意义上的体育称为sport(s),把教育范畴内的体育称为physical education,这是术语变迁的结果;另外,“体育”(TIYU)是一个可以囊括一般意义和教育范畴体育概念的术语,在一般意义上,它以S的形式出现,在教育范畴内它又以PE的形式出现[11-13]。
其实,即使是在“大体育”论者认为存在整体概念的日本,也不乏学者表示“体育”当属教育领域,如前川峰雄认为,体育与运动经常相提并论,但绝不能把体育和运动、身体活动混为一谈[14]。日本学者岸野雄三通过考证认为,gymnastics(英)、gymnastique(法)等词在日本统称为“体操”“体术”或“体学”;箕作麟祥最早把physical education译作“体之教”,后又有“身体之教育”“身体教育”“身教”等说法;后由近藤镇三简称为“体育”并被人们广为接受和使用[14]。所以,“真义体育”一派也从词源考证出发,寻找体育的本质。如韩丹[15]在比较了法语、英语、俄语、德语、日语中与“体育”相关的词源后,指出这几种语言中的“体育”都由“身体的”和“教育”或“培育”构成,翻译为汉语也必然是“身体教育”或“体育”,所以“体育”就是“身体教育”。韩丹还认为,对于熊斗寅所述体育社会形态的共性就是总概念[6]的说法,都是含义不明、大而宽泛的概念,用这些尚需定义的概念去界定另一个概念本身就值得推敲。不止如此,韩丹还引用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埃斯特角宣言》里面“重视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内容说明,国际上PE、S和休闲活动呈分化趋势,根本不存在什么整体概念[16];再说,所谓的“大体育”“总体育”或“广义体育”,实际上指的是“体育工作”,把“体委工作”当成“体育概念”,是理论研究中的根本错位[17]。张军献[18]也指出,美国并不存在所谓的上位概念,熊斗寅等学者执着于概念的本土化只会增加逻辑混乱,S作为“大体育”本身经不起推敲。
根据国外著作的介绍,sport一词是个现代术语,它源于法语de(s)porter和拉丁语deportare,二者都是“自娱自乐”的意思;1440年,英国最早广泛使用sport来指在游戏、个人业绩和打猎等形式中的竞争性[19]。在我国,王学锋[20]也把sport的本质属性界定为“竞争”,把“体育”(PE)定义为:育体,是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发展与完善人类体质的教育。他说把S当作PE是认识上的最大误区,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的20种重要刊物的名称均说明“体育”对应的是PE,“大体育”是不存在的[21-23]。1989年,林笑峰[24]就说:体育的真义,确是身体的教育,即增强体质的教育。人们对“体育”名词使用的混乱,实际造成了“体育”(PE)、“身体文化”(PC)、“身体娱乐”(PR)和“竞技”(sport)4个词和它们的概念发生双双脱离、转移和脱落现象[25]。大体看来,“真义体育”一派普遍坚持教育是体育的本质。
总之,PE与S之辩是我国学界关于“体育”概念论争的代表,对我国“体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反映了“体育”概念困局的主要问题。
(1)争鸣的原因。首先,自清末传入我国与“体育”相关的术语较多,以至于在实践中常有“体育”“运动”“身体教育”等词语的混用;其次,人们惯于以工作便利为原则划分“体育”的不同领域,出现了诸如职业竞赛、社区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等词语,增加了辨识难度;最后,中国体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党和政府为实现革命和建设任务,把既有sport活动体系作为一种手段利用的特定机制[26],“体育”功能的泛化(如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文化功能等)阻碍了定义过程中逻辑思维的发展。亦即,不同语境下的语义与语用造成了“体育”概念的混乱。
(2)争鸣在本质上包括了“体育是什么”和“体育如何存在”2种意向,坚持“真义体育”的学者从“体育是什么”出发,努力寻找“体育”的本质,即恒定不变的东西;坚持“大体育”的学者,则是从“体育如何存在”出发,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寻找一种能够统揽“体育”外延的概念,二者的矛盾根源于此。
为了破解“体育”概念之难,多数学者仍以汉语“体育”作为总概念。如兰孝国、吴永存等,用结构主义方法论提出,用“体育”作为一级概念,对等于 sport(s)概念,“体质教育”“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等并列为二级概念[27]。刘湘溶[28]指出,体育是人类特有且特殊的育化方式;体育是“四位一体”的社会现象;体育已成为现代人类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张洪潭[29-32]认为,需从“肢体活动、强化体能、非生产性”这3大要点中去把握体育的本质或本义,在其下又可按照单元领域和活动性质划分下位概念。胡科和虞重干[33]认为,把“真义体育”改称“身体教育”,与身体竞技、身体娱乐等一起作为“体育”的内容。刘映海等[34]则从人的本质出发,得出体育是指向竞争和内在自由的促进类本质的身体活动的结论。这些研究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启示,但我们又不得不谨防此类概念可能产生的另一种危险,即高度抽象的哲学化倾向,且用“理念”代替“概念”将会消解对体育实践的指导性。
2 历史逻辑中的体育
“体育”的定义既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也是一个理论性问题。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界定“体育”的2个前提条件是:在历史演变中寻找体育内涵与外延的变化线索,从逻辑分析中找出体育概念的原旨。
历史地看,自我国使用“体育”一词以来,体育的内涵与外延曾发生过2次重大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体育”主要局限在学校中,指学生身体的自然发育,是“身体教育之简称”[35]。陈永声[36]的记述中说道:“中国目前的体育设施,差不多只限于学校以内,学校之外几无体育设施之可言。”1929年4月16日,我国历史上第1部专门的体育法令——《国民体育法》公布,其中规定国民体育由训练总监部会同教育部实施,同时对民间体育会的成立等加以规定;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体育委员会”,下设学校体育组、社会体育组和研究编审组,这显示在民国时期,“体育”即已走出学校,其涵义也在“身体教育”之外增加了“竞技”“养生”“健身”和“卫国”等内容。总的看来,在20世纪中叶之前,受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国民体育法》《国民体育实施方案》都没能很好地实施。1941年,修正后的《国民体育法》仍规定教育部是全国体育行政的主管部门,可见,在建国前学校体育是“体育”的主力,“身体教育”是“体育”的主要内涵。
新中国成立之初,改善和提高人们的身体健康水平促使确立“健康第一”的教育方针。后来,为快速提高我国竞技运动水平,助力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体育实践的发展反映出在20世纪下半叶“竞技体育”居于我国“体育”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学校教育中,体育主要在“健康第一”教育方针的指导下,随着对“健康”认识的不断深入,“体育”从身体的健康拓展为身体的、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等注重人的身心协调完满的一种状态;另一方面,主要受到国际竞技运动发展的推动和我国“体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体育”已经兼有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activity,physical culture和sport(s)等词的意义,并呈现出以sport(s)为主导的面貌。
由此可见,我国“体育”从无到有,从进入学校到走出学校,已从“身体教育”演变为与发展人身心的一切身体活动形式(见表1)。

表1 我国“体育”内涵与外延的演变
其后果是,受体育概念内涵与外延变化的影响,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出现了历史性偏差,产生了“体育即竞技运动”或“竞技运动即体育”的认识误区。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竞技运动的崛起并不能使我国迈进体育强国的行列。而早在2000年12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高中《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小学“体育”课更名为“体育与健康”课,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这2个方面看,我国体育在经历了“以学校体育为主力”“以竞技运动为统领”的2个阶段之后,已经进入了全面反思“体育是什么”“体育应当如何发展”的新时期。这其中,学校体育中归属于竞技体育的部分是实现与精英竞技进行连接与互动的结合部[37],体教融合是转变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破除体制性障碍,借鉴世界体育强国相关经验的必然[38],中国未来的体育人口必须首先在校园中培养[39]等均反映出我国体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历史反思与诉求。
3 理论逻辑中的体育
逻辑地看,现有“体育”的争议主要是在“真义体育”与“大体育”之间当作何取舍。张天白[40]发现,古希腊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区别人的不同身体活动形式,其中,竞技术强调运动技术的指导,并以饮食等生活制度增加体力、体重,来适合运动和训练的需要,着眼于运动技能的提高;体操术以所有自由民为对象,根据医学知识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进行合理运动、卫生保健的指导,着眼于运动对身体健康的实际效果。作为以获奖为目的的身体形式的“竞技术”,与以提高身体素质为目的的“体操术”在古希腊就已分道扬镳了。
古希腊对竞技术和体操术的区别主要是对象和目的上的区别。竞技术的对象是以参加竞技赛会的职业运动员为对象,通过较为专业的训练提高竞技能力和水平,以赢得比赛为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体操术的对象是所有人(自由民),所用手段综合了医学、运动学等多学科知识,其直接目的是促进人的身体健康,最终目的是为城邦培养健壮与美德兼俱的公民。古希腊实际区别竞技术和体操术的意义在于,竞技运动和体育具有天然的联系,它们都展现出身体活动的形式,并辅以运动、训练、医学、卫生和饮食等多方面的知识。但是,竞技运动以参加竞赛为目的,其直接受众只能是具有较高运动能力和水平的少部分人;体育则不然,体育以所有人为直接受众,并根据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制定不同的运动和训练方案,竞争和参与都是体育的应有之义,却不是体育的目的。
现在,国外通常都是将sport(s)与physical education独立或并列使用,参照安德森著作中的释义,sport(s)是“具有竞争性的身体活动或游戏形式”,其“目的是使用、保持或提高身体能力和技能,同时为参与者提供一种享受,并在某些情况下娱乐观众”,“比赛或游戏的双方都试图胜过对方”[41]。日本学者也从目的上区分体育和运动,他们认为,体育和运动都是锻炼身体的活动,虽然活动的强度有强弱的差别,但是几乎是同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由于学校体育把运动作为内容和教材来教授,很难说是在开展性质不同的身体活动,加入目的和时间这2个考察因素后,,体育活动的结果(也就是预期价值的实现),是期待在活动结束后的收获,体育的目的不仅蕴藏在身体活动之中,而且还会在活动之后继续发挥着作用[42]。以此管窥国外的相关研究,或许是受古希腊对竞技术和体操术分别的影响,基本没有出现将sport(s)与physical education混淆使用的状况。
根据陈村富[43]的研究,在古希腊语中,physical的词根physis指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成长的东西,即“天生的”“自然而然的”,和它对应的是“techne”,即“制造术”。樊杰[44]分析认为,physical education指的是依据人之自然而然的生命力量而进行的教育,倘若追溯到这一本源性的词义,那么,体育的教育性和运动性在这个层面上就得到了统一。这表明,“体育”与“运动”本无矛盾,不过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分化形态和价值指向发生了变化而已。如果因强调体育不同于他者的运动形式而合起来称作“体育运动”,貌似兼而有之,实际上也是画蛇添足。
再从physical education本质属性的角度来看,以美国社会对PE内涵解读的变化为例,有一个从“针对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转向“通过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现又转向“在身体内的教育”(Education in the Physical)的过程[45]。不过始终未变的是,PE的“身体运动”和“教育”未曾脱离,连坚持“大体育”的熊斗寅都承认,“体育的本质必须从教育和文化2个范畴来认识”[46]。甚至有些人为了要把“体育”和“教育”结合起来,创造出“体育教育”这么一个“四不像”的词来。要知道,从词语构成的角度来分析,“教育”本身就包含在体育之中,预设为体育的应有之意,既然结果包含于前提之中,也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来验证教育是体育之本质了,本质早就在名称中被赋予了[33]。
因而,体育的本质是教育,竞技、锻炼、训练和比赛等都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具有与“体育”相同形式的社会活动,它们是考察体育的现象之维,以其中之一的特征替代体育的全貌,并试图抽离体育的本质是不可取的。同时可以看出,历史上曾论及的“体育的教育化”本质上是身体活动形式的教育化,至于哪些身体活动形式能成为教育资料,则要经过“一般文化—有文化价值的文化—合乎一定社会需求的文化—适合教育过程的文化”[47]这样一个抉择和提炼的过程。把体育的本质归入教育,虽不能被所有人接受,却是可以通过历史来论证,这并非只是词源意义上的考证,而是在有意义的历史资料中建立起来的逻辑基础,已经超越了操作层面的认识。所以,不是硬生生地把体育拉进教育的大门,而是教育必然会把一切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内容纳入其中,体育以其影响人身心发展的特殊性质必然地属于教育的范畴。
4 关于“新体育”的构思
叶澜教授[48]曾对教育作出过一个描述性定义,即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教育只是人类实践中的一个系统,体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把体育归入教育,便不会陷入到“体育是实践活动”“体育是文化活动”的泛泛而谈中去。又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运动”是一切物质的存在形式,“活动”是由主体心理成分参与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运动形式,“体育”区别德育、智育、美育的种差可界定为“身体活动”。
由此,“新体育”便是指以身体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活动。(1)它并不是“身体教育”的简称,也不是“真义体育”的翻版。我国体育在经历过学校体育为主力、以竞技体育为统领等2个历史阶段后,已经步入了更加重视人的共性与个性、身体与心灵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因此,根据否定之否定原理,“新体育”将会是超越“以学校体育为主力”和“以竞技运动为统领”后的再次飞跃。(2)它包括了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通常所说的学校体育是体育的典型形态和制度化形式;而通常所说的“竞技体育”,实则是“竞技运动”,它虽然形似“体育”,却因其在对象和目的上均与“体育”有根本区别,并不在“新体育”之内。
总之,文中所提“新体育”概念,意在摆脱类似于“体育是一种文化活动”式的泛论,也试图摆脱当前学校体育概念对受教育者和受教育场所的界定,为涵盖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作铺垫。因此,“以身体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活动”未谈及具体的体育手段和方法,也没有罗列具体的体育目标,而是把这些都寓意在了“教育”之中,这是为了突出体育的育人价值不得已而为之。另外,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是何种关系将是提出新的体育概念后另一重要问题,留待今后继续拓展。
[1]杨韵.后哲学文化演进中的体育哲学:基于理查德·罗蒂哲学思想的探究[J].体育科学,2011,31(7):92-97.
[2]乔玉成.“体育”概念的发生学研究:兼论“Sport”能否成为中国“体育”的总概念[J].研究与教育,2013,28(1):1-16.
[3]韩丹.谈体育概念的源流演变及其对我们的体育认识和改革的启示[J].体育与科学,2010,31(4):1-8.
[4]张天白.“体育”一词引入考[J].体育文化导刊,1988(6):16-19.
[5]熊斗寅.现代体育与体育现代化问题初探[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80(1):1-12.
[6]熊斗寅.“体育”概念的整体性与本土化思考:兼与韩丹等同志商榷[J].体育与科学,2004,25(2):8-12.
[7]曹湘君.体育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5:21.
[8]刘转青,刘积德.我国体育分类刍议[J].体育学刊,2017,24(1):47-51.
[9]崔颖波.论“体育”不是“身体教育”[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4(6):491-493.
[10]魏立宇,杨薇,韩飞.“体育”不是“身体教育”质疑:兼论中国体育本质研究的症结[J].体育学刊,2011,18(3):1-6.
[11]崔颖波.“寻找虚无的上位概念”并不是我国体育概念研究的症结:与张军献博士商榷[J].体育学刊,2010(9):1-4.
[12]崔颖波.中日两国身体文化领域的上位概念变迁——兼论将体育一词译作Sport(s)并不是“偷换概念”[J].体育与科学,2007(5):18-21.
[13]崔颖波.スポ—ツ为什么能成为日本体育的总概念——兼论怎样理解Sport(s)概念[J].体育与科学,2005(3):6-9.
[14]前川峰雄.体育原理[M].鲁彩云,译.北京:国家体委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组,1982.
[15]韩丹.“体育”就是“身体教育”:谈“身体教育”术语和概念[J].体育与科学,2005,26(5):8-12.
[16]韩丹.辨析体育的共性与整体:答熊斗寅同志的商榷之一[J].体育与科学,2004,25(4):5-9.
[17]韩丹.论体育概念之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2,33(6):1-11.
[18]张军献.寻找虚无上位概念:中国体育本质探索的症结[J].体育学刊,2010,17(2):1-7.
[19]MECHIKOFF R A,ESTES S G.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M].Fourth Edition.New York:McGraw-Hill Companies,2006:4.
[20]王学峰.“Sport-体育”:中国体育认识上的最大误区:再谈体育(PE)与竞技(sport)的本质、功能、目标、手段和主体[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3(1):16-18.
[21]王学峰.中国体育Sports化问题辨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3(6):6-8.
[22]王学峰.体育概念研究中的两种“硬伤”:从概念分析到转变思维方式兼与熊斗寅先生商榷[J].体育与科学,2004(6):42-44.
[23]王学锋,田玫,彭成,等.对体育概念的基本认识与思考:兼评<体育与竞技——现代导言>(英文版)[J].体育学刊,1996(3):52-55.
[24]林笑峰.析体育的真义(摘要):兼谈中国真义体育[J].学校体育,1989(2):60.
[25]林笑峰.健身教育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2.
[26]韩丹.纵论中国体育:特征、概念、历史和转型[J].体育与科学,2014,35(6):2-4.
[27]兰孝国,吴永存,崔忠洲,等.“真义体育观”与“Sport(s)大体育观”之争的方法论意义:一种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11):20-24.
[28]刘湘溶.对体育的全新诠释[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6):721-723.
[29]张洪潭.体育概念及目的任务新探[J].体育科学,1990(1):7-12.
[30]张洪潭.体育真义论[J].体育科学研究,2003(1):1-3
[31]张洪潭.体育的概念、术语、定义之解说立论[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6(4):1-6.
[32]张洪潭.体育概念研究进展[J].体育与科学,2011(3):11-19.
[33]胡科,虞重干.真义体育的体育争议[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0,24(4):59-62.
[34]刘映海,石岩,丹豫晋.论体育的本质及其教育价值[J].教育研究,2014(9):24-32.
[35]吴蕴瑞,袁敦礼.体育原理[M].上海:上海勤奋书局,1933:9.
[36]陈永声.体育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42.
[37]辜德宏.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起点[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30(5):383-387.
[38]吴建喜,池建.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中体教结合向体教融合的嬗变[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4):88-93.
[39]张正民,陈宁.我国学校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诉求与理论导向[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12):87-94.
[40]张天白.古代“体操”语义的演变[J].体育文化导刊,1992(2):9-11.
[41]ANDERSON D.The Discipline and the Profession.Foundations of Canadian PhysicalEducation,Recreation,and SportsStudies[M].Dubuque,IA:Wm.C.Brown Publishers,1989.
[42]朝比奈一男,水野忠文,岸野雄三,等.スポーツの科学的原理[M].第三版.东京:大修馆书店,1980:39.
[43]陈村富.希腊原创文化及其观念[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3(3):5-12.
[44]樊杰.体育作为教化之源:古希腊体育的教化意义[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45]覃立.论“physical education”的第三种解读:“Education in the Physical”[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4):111-117.
[46]熊斗寅.什么是体育[J].体育文化导刊,1996(6):8-10.
[47]陈桂生.教育原理[M].第三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2-24.
[48]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