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制造出主观的真实
——论纪录片的真实性
李炳钦
客观制造出主观的真实
——论纪录片的真实性
李炳钦

长期以来关于什么是纪录片的真实性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纪录片的真实性,牵涉到主观与客观、纪录真实与叙述真实、客观纪录与合理虚构的有机统一问题。
美国纪录片学者保拉·莱宾诺维茨认为纪录片无论怎样客观,但在它再现的真实里总是包含着主观的因素。他说:“纪录片试图以其似乎纯粹的形式——真实电影,透过摄影机与麦克风记录下来的客体去再现真实,包括主观的真实在内:客观性制造出主观的真实。”[1]
“客观性制造出主观的真实”,莱宾诺维茨说得很对,纪录片的真实实际上就是通过客观的方式制造出来的“主观的真实”;真正纯客观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客观生活是无法在没有主体介入的情况下被原原本本地复制下来的。
正如真理是相对的一样,纪录片的真实也只能是相对的,只能是创作者的主观与客观生活的有机统一,绝对真实是不可能的。有时候,纪录片的真实更像一个悖论,当你想要更真实的时候,结果反而不那么真实。比如我们去拍摄一个居委会接待居民来访的工作情景,我们事先不打招呼,希望拍到比较真实的情况,结果工作人员老是偷看镜头,如果这样在电视上放出来,观众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好不容易让他们不看镜头,开展正常工作,但实际上由于摄像机的介入,他们还是正常不起来,下意识地开始整理头发和衣服,清理桌面,说话和动作也开始带上表演成份。就是说,此时摄像机前的居委会工作状态是不那么真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提前打招呼,居委会又会弄得很做作甚至作假,虽然会很规范,却不是真实的正常工作状态,拍下来的镜头还是无法达到客观真实。
一、纪录真实与叙述真实
说真实是纪录片叙事的底线其实是一个空洞的老生常谈。通常当我们谈论纪录片是否真实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所看到的纪录片的故事是否真实。纪录片的故事是叙述者所叙述的内容,叙述的内容是否真实,有时是我们无法判断的;就是说,当我们观看一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未必就能断定它的故事真实与否。也许,那些看起来真实自然的东西其实并不真实。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必须进入到操作层面来考察:纪录真实与叙述真实,从这里来探究纪录片故事的真实性才显得更加实在而重要。当然,这也是纪录片的良心所在。这一点可由纪录片伦理学来作更深入的研讨。
(一)纪录的真实性
所谓纪录的真实,是指纪录片人在前期拍摄时对生活本事作真实全面的纪录,排除伪造和人为导演的成份,尽可能真实地纪录生活本事的原生状貌。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纪录下来的事件必须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是能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东西,而不能是虚假的,人为导演出来的东西。比如纪录一次游行,必须生活中确实存在这么一次游行,而不能伪造一次游行,也不能将旅游的人群伪造成游行示威的队伍。其次,纪录下来的事件必须是最能表现事物本质的东西,必须表现全貌,而不是局部,如纪录游行队伍时必须拍下最能反映此次游行本质的镜头,拍下游行队伍的整体状况,而不能只捕捉局部或几个捣乱分子发出的另类声音。纪录不真实和纪录不全面,都是造成纪录片故事失真的根源。1993年发生在日本NHK的“作假”风波是一次很值得纪录片人记取的事件。日本创作人员在木斯塘拍摄《喜玛拉雅深处的王国——木斯塘》时,一位摄制组成员因高山反应而病倒,当时因忙于照料病人而没有拍下来。但在返回途中,导演决定“情景再现”,补拍搬演“高山病”的一幕。显然,这次纪录的事件是虚假的,真实的情景已被错过。当影片制作完成后在“NHK特集”中播出的时候,一位创作成员向媒体披露了“作假”事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NHK的会长十分震惊,未经充分查实事件经过就在电视上发表了“谢罪讲话”。尽管情有可原,但最后该片导演还是被处以停职降薪。显然,NHK秉承了“直接电影”的纪实理念,纪录者只能对眼前发生的生活事件做“墙上苍蝇”式的客观记录,排斥任何虚构的成份,更不允许所谓“情景再现”的存在。只有不作假的纪录片,才符合纪录片“非虚构”的本义。从这个角度看,NHK当时的处理是正确的,这不仅提高了NHK的媒介公信力,也警告了纪录片人:纪录生活是一件严肃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因为今天的纪录,就是明天的历史。如果纪录可以作假,那么历史还值得相信吗?况且《木斯塘》剧组作假表现的是自己,则更有自我表现、自我吹嘘之嫌。不过,随着人们对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适当的“情景再现”已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摆拍,情景再现是有条件的。至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允许“情景再现”,则视具体情况确定,关于这一点容后论述。无论如何,前期纪录的真实性是纪录片必须坚持的原则。

朗兹曼《浩劫》
(二)叙述的真实性
纪录片只有纪录的真实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叙述的真实。纪录真实是制作纪录片的必要前提,叙述真实才是保证纪录片整体真实感得以最终达成的保障。因而所谓叙述的真实,是指纪录片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必须遵循真实的原则,特别是在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要求在纪录真实的基础上恰当地选用真实的事件素材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不是靠玩弄蒙太奇技巧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地杜撰故事,它是同虚构叙事绝然不同的叙述方法。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在具体的后期剪辑过程中很容易出错。
在虚构叙事里,作者可以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随意安排场景和虚构人物性格及其行为举止,比如可以将晴天改成雨天,夏季改为冬季。正如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言,“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2]鲁迅先生所言是文学虚构叙事的一种“综合法”,已被传为文学创作的经典叙述方法,但在非虚构叙事的艺术样式中是被禁止的。
在非虚构叙事中,绝不可随意摆弄故事情节,捏造事实,也不能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张冠李戴”,把彼地场景“嫁接”到此地,把张三的事情记在李四的名下。法国著名导演朗兹曼为我们做出了典范。他耗时十一年摄制的长篇纪录片《浩劫》,表现纳粹时期屠杀犹太人的“灭绝营”,拒绝使用任何类似的拍自“集中营”的图片和影像资料。因为朗兹曼坚持认为,既然“灭绝营”早已经过周密策划毁灭了任何证据,影片就没有必要自作聪明弄一些类似图片来图解,因为那样反而显示出“无中生有”的矫饰,比NHK的所谓作假事件要不可饶恕得多。朗兹曼始终坚持依靠人物的证词来构建出“灭绝营”的恐怖情景,因此也使纪录片真实叙事的原则得到有力的贯彻。在对待真实的问题上,朗兹曼的态度是严肃的,值得纪录片人仿效。
在纪录片创作实践中,叙述的真实性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由于纪录片的片比很大,素材与成片之比可达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前期拍摄的素材量非常巨大,剪辑师很容易在不经意之间将凌乱的素材移花接木、张冠李戴,造成人物、地点、时间、空间以及因果关系上的颠倒和错乱。有时为了叙述故事的需要,故意颠倒素材之间本来存在的逻辑关系,利用素材来虚构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故事情节或细节,以达到好看的目的。比如生活中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往往会心情沉重面部表情阴沉,这与天气本来没有联系,也许这时刚好天气晴朗,但是有的作者却喜欢像电视剧那样为了烘托气氛而改变天气,换上乌云密布或风雨交加的镜头。特别是在非线性编辑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这种剪辑上的“造假”易如反掌,素材的本来面貌可以被瞬间改变,加上蒙太奇手法魔术般的变幻,这些都足以令纪录片的真实性变得脆弱不堪!
因此,守住纪录和叙述的真实性,是纪录片人不可须臾废弛的良心所在,也是纪录片人必须坚持的道德原则。
二、自体复现和情景再现
这是有关纪录的两个概念。纪录片人总是满怀激情地期待自己的纪录能够切近生活和历史的本质。不过,尽管他们的手中握有锐利的武器,但在诡异多端转瞬万变的生活面前,他们仍然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
说纪录片人握有“锐利的武器”,是指他们手中的那杆“枪”——摄像机(有些纪录片人有时爱把摄像机简称为“枪”)。与画家和作家手中的笔相比,摄像机在纪录生活时,的确拥有自己的优势,因为摄像机的镜头可以十分忠实地将客观物像复制下来,体现着异常严格的客观性,这是其他记录方式所无法企及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体复现”。但遗憾的是这种物像的“自体复现”却受到“时态”的限制,只有纪录者与生活同步或同“时态”进行纪录,方能达成“自体复现”的效果;否则就是梦想。但是故事还得讲下去,纪录片人就不得不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情景再现。就是说,当现实生活已成历史往事,客观纪录已无法进行的时候,于是再造一个类似的情景出来,然后再行纪录,就是所谓“情景再现”,亦称“真实再现”。不过这种方法始终存在着争议。一般认为,所谓情景再现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措施,而且不可有违历史真实这条底线。
如此说来,照相般的“自体复现”和人为搬演的“情景再现”代表了纪录片叙事的两个极,一极指向客观,另一极指向主观,纪录片的故事就是在这两极之间此消彼涨、彼此交融的结果。纯主观的纪录片和纯客观的纪录片都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有主客有机统一、或是在主客观之间有所偏重的纪录片作品。
(一)“自体复现”:真实如你所见
无论如何,让纪录片的故事“自体复现”总是纪录片人和纪录片观众共同的梦想,因为“真实”是人类共同的审美追求。
“自体复现”这个说法取自崔君衍所翻译的法国电影学者让·米特里的一篇文章《论一般影像》。米特里在这篇文章中说:“影像在各个方面都形似于被摄原物。它不是艺术家的造物,可以说,它是实物通过折光和透镜的作用映在胶片上的自体复现。复制在胶片上的物象是严格等同的摹本。”[3]米特里的意思是说,艺术家用摄影机所拍下来的影像不是“艺术家的造物”,而是被摄对象在镜头中的“自体复现”,就是说,实物是什么样子,在镜头中就是什么样子;拍下来的镜头是与实物“严格等同的摹本”,就像观众自己所看到的一样真实自然。在这一点上,镜头远比画家的色彩描绘和作家的文字描述要客观得多。这就象艾柯所解释的那样,“看一幅斑马的照片,比听到或读到‘斑马’这个字眼,在某些方面更接近看一匹真实的斑马。”[4]而纪录片镜头中的斑马又比静止状态的斑马照片更加真实可感。
在纪录片叙事里,镜头的这种“自体复现”包括两个方面:它既有生活物像的静态的“自体复现”,同时也包括生活事件的动态的“自体复现”。如纪录片常用的所谓“纪实”摄影,就是对事件作动态的纪录,将生活中的事件发展流程客观地“复现”在摄像机的镜头里,使之成为所谓“原生态”的生活影像。这种理想的客观纪录曾经是一些纪录片人的执着追求,尤其对于那些在纪录片史上被称为“直接电影”的纪录者们。“直接电影”因直接取材于生活原貌而得名,正如林旭东所言,“尽量让镜头前自生自灭的‘事实’在影片当中进行‘自我阐述’——这种电影因此获名:‘直接电影’——这就是说:它是如你所见。”[5]这种电影理念宣称创作者只是严格的旁观者,摄像机如同“墙上的苍蝇”,冷漠地纪录生活而不干预生活,遵循一种近乎偏执的客观原则,一反格里尔逊式的“对现实进行创造性处理”的纪录电影观。法国电影学者拉法艾尔·巴桑在《纪录电影的起源及演变》中说:“在50年代末的加拿大、法国和美国,纪录电影的观念与合目的性得到更新。对‘直接电影’的倡导者来说,这种更新表现在:去除唯美主义,将镜头重新对准被摄主体,让拍摄对象自己说话,而不是将作者的话语强加给事先组织好的场面,尤其是通过蒙太奇手法。”[6]
“直接电影”的创作理念在成立于1958年美国纽约的罗伯特·德鲁小组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1960年,德鲁小组用一套组装的16毫米摄影机完成了第一部直接电影的代表作《初选》。这部影片在跟踪纪录196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产生的前后过程时,模范实践了直接电影的“客观”理念,德鲁小组不介入现场发生的一切,只用随机拍摄的方法把碰巧在镜头前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于是在他们的镜头前,约翰·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参加竞争的活动过程得到了真实的呈现:一次又一次的集会,街头拉票演说,电视讲演,汉弗莱在电视转播前一遍遍地排练,肯尼迪为得到一批波兰裔选民的选票而反复背诵一句波兰话,参议员的智囊团成员们开着粗俗的玩笑,竞选后肯尼迪彻夜不眠守候着成功的结果公布出来……所有这些生活事件和场景都被即时纪录下来,德鲁小组在影片中把这些事件如实地一一呈现出来,不带任何观点和倾向性。
直接电影的“墙上苍蝇”式纪录为纪录片叙事的相对客观性提供了可能,而“摄录一体化”摄像机的技术性能又为这种客观提供技术上的保障。摄录一体机延伸了人体器官的功能,它将人眼的视觉功能和耳朵的听觉功能强化了,因而能比人作出更细致的观察。前苏联著名电影导演吉加·维尔托夫曾不无夸张地声称:“电影眼睛是完美的,它能感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7]他认为“电影眼睛是以电影纪实的手段,为肉眼译解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8]人的眼睛在观看事物的时候,总会遗漏许多信息,有时甚至会“视而不见”,特别是对那些处在平常角度中的,或者司空见惯的事物。而且由于人的感觉器官远不如机器灵敏,眼睛的视力也非常有限,我们的目光常常只能在事物的表层游移,得到一些模糊的映像。但是摄像机却能“发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在那些特写镜头里。由此可见摄像机的客观性有胜于人眼。匈牙利著名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在无声片时期,首先被电影摄影机发现的新世界,是那些只有在最近距离内才能看清楚的极其微小的事物的世界,是微小事物的深藏不露的生活世界。由于这一发现,摄影机不仅使我们看到某些前所未见的事物和事件:昆虫在宽阔的叶上的冒险旅行,初生的小鸡在鸡舍的角落里经历的悲剧,花的爱情行为和纤细风景画的诗意。摄影机不仅带给我们新的题材,它在无声片时代借助于特写,还给我们揭示了我们自以为早已熟悉的生活中的潜在基因。”[9]摄影机以其特殊的手段如显微摄影、长焦摄影、微距摄影等带给我们肉眼常常看不到的事物,为我们呈现客观世界的丰富性。看过纪录片《点点虫》的人都会惊叹,在我们的视力所忽略的地方竟然存在如此丰富动人的微观世界!

纪录片《点点虫》
的确,摄录技术的进步把更多的客观存在“复现”在人们的眼前,也使所谓直接电影或真实电影看起来更加真实可信。不过直接电影或真实电影在纪录和表现生活时太过拘泥于不偏不倚的“复现”,而容易使影片流于松散而冗长,就如W·米勒所说的那样:“这样的拍摄方法具有危险性。制片人希望拍摄到的‘特殊时刻’也许迟迟不出现。《沃伦戴尔》若没有黑人厨师的死,能有那样的效果吗?若没有保罗引导观众的视点,还会有《推销员》这部片子吗?由于缺乏严谨的结构,使观众对新纪录片(指直接电影,引者注)兴趣减少了。这在梅斯莱(多译作“梅索士”,引者注)1976年拍摄的《灰色花园》中已充分体现,该片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有趣的,然而因冗长而令人生厌。”[10]的确,等待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时刻“自体复现”是一件需要耐心且不一定有结果的事情。成都电视台彭辉编导的纪录片《平衡》摄制时间长达4年之久,如果没有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英雄突然遇害,片子的震撼力就会大打折扣。
另外,直接电影的所谓客观真实性也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即使人类“复现”物像的手段再高明,人们的叙事也只能达到相对的客观。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叙述本身就不是一种纯客观行为。这正应了物理学中关于水温测试的“测不准”原理,当你把温度计放进水中的时候,水温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哪怕这种变化是极其微小的。纪录也是如此,当我们开始把摄像机摆在事物面前的时候,就意味着对事物的纪录已经有了先在的视点。况且,客观事物或事件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当事物或事件转瞬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失去了即时纪录的可能。不过这时,历史虽不能重演,但纪录却可以重现。
于是,出现了以“扮演”和“搬演”为主要手段的“情景再现”。
(二)“情景再现”:真实的重构
情景再现又称真实再现,就是在纪录者所要纪录的事件已经成为历史而无法进行现场纪录的时候,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得不采取“搬演”和“重构”的方法,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再现事件发生的过程。从理论上说,纪录片所叙述的故事应该是在真实时间和真实环境中发生的真人真事;但是实际上,真实时间和真实环境往往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纪录者常常来不及记录就已经过去了,不得已采取情景再现之法来记录模拟的“真人真事”。

《北方的纳努克》
从表现形式上看,这种情景再现的故事,有扮演、搬演、隐喻或象征等。所谓扮演,就是请人化装成当事人出现在镜头里,多少带有一些表演的成分。例如历史纪录片《复活的军团》,其中的秦始皇和秦国军队都是请人扮演的。不过这种当事人的扮演者不能像影视剧的演员那样尽情发挥才艺来表演故事情节,他只能是当事人的“替身”,其所谓“表演”也只能是做做样子而已。所谓搬演,就是重演,是把发生在另外一个时空中的故事或事件重演出来。搬演和扮演的区别在于模拟的对象不同:前者演“事”,而后者演“人”。隐喻和象征也是情景再现的常用手法。隐喻是用此物比拟彼物,用类似的事物指代另一个事物,当纪录者无法拍摄到那个想拍的事物时就常常采用这种手法。象征则是采用某个具体的事物来表现某种特殊意义。对于非纪实性的历史纪录片来说,隐喻和象征的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内容上看,情景再现又有事件的再现、人物的再现和事物的再现等几种情况。事件的再现就是把事件的细节或经过再现出来,其相应的基本手法主要有搬演,比如《北方的纳努克》就是用搬演的手法让主人公重演了过去捕猎海象的全过程,从而将爱斯基摩人传统的生存方式呈现在观众眼前。人物的再现一般通过扮演的方法来完成;而事物的再现则用隐喻或象征的手法,通过一种虚拟的物像来隐喻作者所要表现的某种事物或用来象征所要表达的某种意义,如以花朵隐喻爱情,用朝阳象征新的希望。
从现存资料看,最早运用“情景再现”手法的始作俑者是弗拉哈迪。1922年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问世,其主干故事就是“情景再现”出来的。导演弗拉哈迪要求主人公纳努克放弃使用比较现代的捕猎方式,而采用古老的方法来捕猎海象,“搬演”了历史上爱斯基摩人的劳作场景。十年之后,中国导演张石川也在其纪录片《上海之战》中,也用同样的方法,在上海昆山的乡下挖壕置景,“搬演”了1932年日军在中国制造的“一·二八”事件。尽管弗拉哈迪和张石川的传统受到直接电影的否定,但不久这一传统还是被人继承下来。
纵观历史,纪录片所走过的就是一条从允许搬演到否定搬演再到肯定搬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道路。真实和虚构问题始终伴随着纪录片的创作,是是非非,一直纠缠不清。从纪录片大师格里尔逊最早给定的界说里,纪录片就已经埋下了“搬演”和“重构”的种子。格里尔逊说:“我们把所有根据自然素材制作的影片都归入纪录电影范畴,是否使用自然素材被当作区别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关键标准。凡是实地拍摄的影片都被称为纪录电影”。[11]格里尔逊还将纪录电影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12]在格里尔逊的这个权威定义里,显然包含着合理搬演和重构之意,而他给予弗拉哈迪影片的高度赞赏就是最好的注脚。美国电影学者帕·泰勒也认为“在纪录片中早早就播下了虚构的种子”,[13]他认为格里尔逊之所以赞赏弗拉哈迪的影片就是因为弗拉哈迪对事实进行了“重新安排”而使之成为了“叙事散文式影片”:“纪录片仿佛处在艺术和实况纪录之间的分界线上,因为纪录片首先必须尽量简洁地和逻辑地安排一系列既有顺序的事实,并符合上面提到的作为科学知识的要求。当然,我们有时在想象力特别强的纪录片中看到,对事实的逻辑安排变成了重新安排,造成一种几乎是诗的而不是逻辑的顺序,用文学语言来说,就是成了讲真人真事的高级叙事散文。当初使格里尔逊钦羡不已的正是弗拉哈迪早期作品中这种流畅的叙事散文式影片:使人感到是在处理一个不仅真实,而且是美的题材。”[14]
在弗拉哈迪和格里尔逊之后的多数时间里,“情景再现”的手法其实经常在被人们运用,尽管人们常常以客观、真实自诩。即使是在极力排斥搬演的“直接电影”或“真实电影”中也无法真正做到他们所自诩的“绝对真实”,就连美国被称为“直接电影”大师的怀斯曼都不无感叹地说:“我无法表现总体真实”。[15]这是因为,在直接电影里,处在一定机位的摄像机镜头永远只能拍到事物的局部和外在表象,难以揭示内在本质;镜头捕捉到眼前发生的景象也往往缺乏历史的深度。
由于“绝对真实”近于神话,于是伴随着上世纪末后工业时代电子信息技术的日臻成熟,一种颠覆性的“新纪录电影”主张悄然登场。由于计算机技术可以炮制画面,摄影机也可以“撒谎”了,照相和摄影“已不再是奥利弗·文德尔·荷尔姆斯称作映照着物体、人物和事件的视觉真实的‘有记忆的镜子’,而是对真实的歪曲和篡改。”[16]当“镜子”映照的内容可以被计算机修改而至“撒谎”的时候,“镜子”也就没有了记忆。新纪录电影宣称:“许多有关当代纪录电影的真实主张的讨论,焦点都集中在了反省和挑战从前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表现真实的技巧上……电影无法揭示事件的真实,只能表现构建竞争性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识,我们可以借助故事片大师采用的叙事方法搞清事件的意义。”[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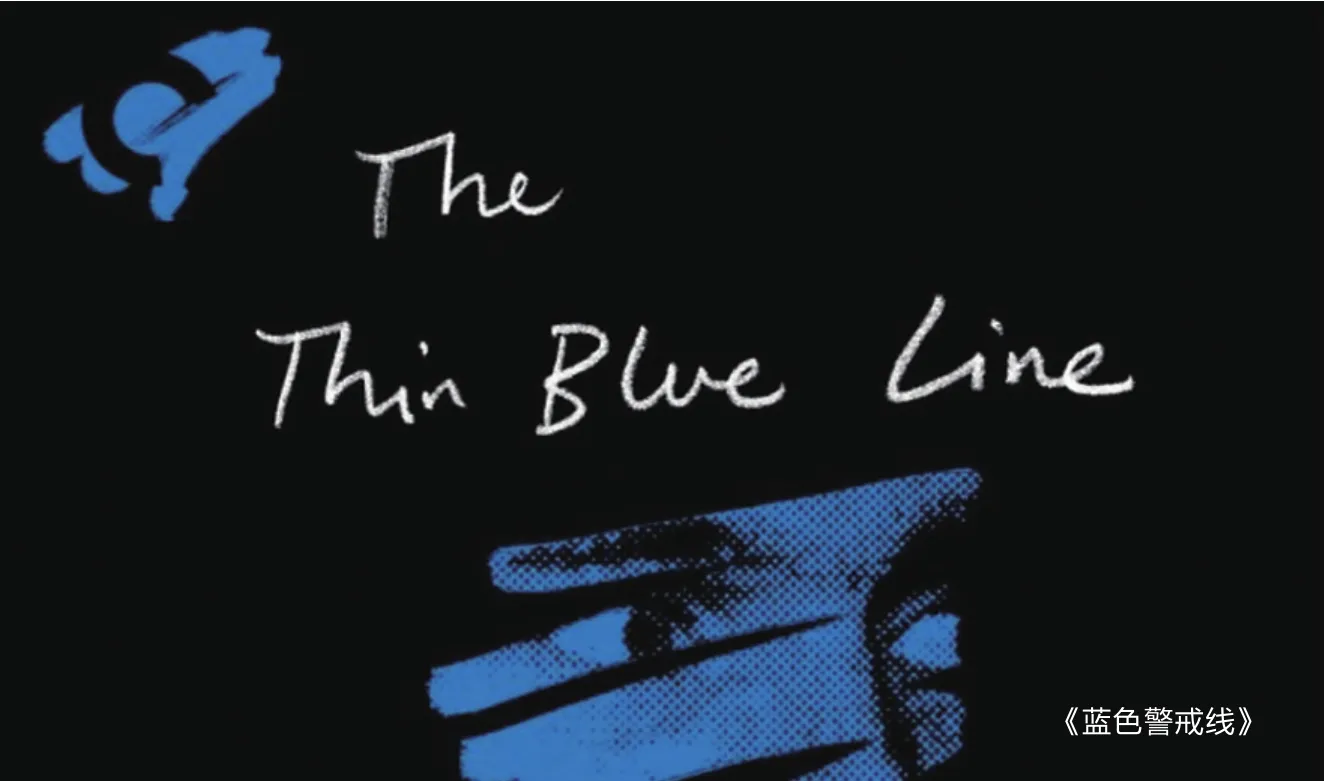
《蓝色警戒线》
显然,这一主张明显地违背了直接电影或真实电影所信奉的捕捉眼前正在发生事件的创作原则。在新纪录电影中,真实是可以被构建出来的,如艾罗尔·莫里斯的《蓝色警戒线》和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所表现的那样。《蓝色警戒线》表现一宗被错判的杀人案。1976年美国达拉斯警察罗伯特·伍德在执行公务中遇害,凶手被判定为一个叫伦德尔·亚当斯的流浪汉。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凶手就是原告大卫·哈里斯。导演莫里斯一反“真实电影”的客观和中立的风格,亲自介入案件的调查和追访,发现见证人和当事人的说法充满矛盾。最后在与原告的近乎心理分析式的自由交谈中,原告自己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承认杀害警察的罪行是自己所为。影片成功地修正了一宗被错判的案件,使无辜者获得自由,而罪犯被绳之以法。影片放弃真实电影纪录眼前发生事件的原则,采用故事片的手法搬演了大量的场景。如比较典型的有谋杀场面的情景再现:随着谋杀的枪声响起,用慢镜头表现一杯冰淇淋被抛起来,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后再伴着音乐溅落到地上,遇害警察慢慢地倒在血泊之中。这个再现的戏剧化场景反复出现在影片中。显然,这些搬演场景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本身,而是导演虚构的,但在追寻事实真相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与《蓝色警戒线》相似的是,朗兹曼的《浩劫》也用到“搬演”的策略,在现在重复过去的罪行,从而使历史复活。电影学者威廉姆斯在研究了莫里斯和朗兹曼的作品后指出:“莫里斯和朗兹曼以‘强制的’调查者特有的好奇心、独创性、冷嘲和执着精神,在通过现在的影像再现过去的过程中,并未过多采用表现过去的直接影像,这正是他们作为后现代纪录电影作者与众不同的地方。”[18]莫里斯和朗兹曼的作品让我们看到,后现代纪录电影是怎样采用虚构的手段和策略来达到真实,为我们展开各种各样的“镜子”,揭示出真实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回响的深度。
现在,在一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情景再现”几乎已成为一种国际通用的手法了。如中央电视台花巨资摄制的《中华文明》、《丝绸之路》、《复活的军团》、《故宫》等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都大量采用情景再现的方法,将遥远的历史图景“复活”在当代观众眼前。《复活的军团》一个突出的表现手法,就是以考古证据和历史研究为依托,借鉴故事片的表现形式,大量使用“情景再现”,表现两千多年前秦国的军队统一六国建立庞大的秦帝国的过程,揭示了秦国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的历史真相。其中的主要人物秦始皇、秦国军队以及记述历史的司马迁都由真人扮演;几次大战役的战争场面也都是搬演出来的,尽管这些扮演和搬演还只是做做样子。就连一向严谨的NHK,在它的历史纪录片中也不得不采用情景再现的办法来“复活”历史中的某些情景。
不过纪录片人必须牢记的是,“情景再现”永远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而已,决不能突破“导演的极限”,滥用“情景再现”。就是说,情景再现是有条件的:
首先,纪录片所要表现的事件已经成为历史,无法进行现场纪录,这是进行情景再现的前提条件;但在可以进行现场拍摄的纪实性纪录片中,则须采用现场跟踪的拍摄方法,尽可能不用“情景再现”。否则,纪录片将失去自己最珍贵的本质。前面提到的NHK“木斯塘事件”中,尽管影片并没有捏造事实,但由于影片是一部跟踪纪行式的纪录片,用的是“现在进行时”,当然应该拍摄眼前正在发生的事件,所以“搬演”不是一个妥当的选择。

日本NHK历史纪录片《故宫的至宝》
其次,在进行情景再现的时候,搬演和重构的事件必须符合历史真实,有文物考古或历史研究的权威根据可资求证,绝不可凭空想象、弄虚作假、伪造历史事件。如日本NHK八集历史纪录片《故宫的至宝》以北京和台北两地故宫博物院所保管的文物为线索,讲述历史上的趣闻故事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影片第四集《书心》在谈到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雅集、流觞赋诗的故事时“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其依据显然来自王羲之《兰亭集序》中这样一段文字:“又有清流激荡,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 ,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如果没有这段记载,纪录片所搬演的“情景”,就成了一段毫无意义而且可疑的画面。纪录片的搬演和重构不等于故事片的表演和虚构。毕竟纪录片是以其真实性而取胜的。
以上我们对与纪录片叙事相关的本事和故事以及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的纪录片的真实问题作了深入探讨。由此可知,所谓本事,即发生在生活中的事件和行为;所谓故事,就是叙事所描述的内容,它是由“一连串事件(行为、事件)加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存在的东西(人物、环境)”所构成的整体,是以特定方式表现出来的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事件。纪录片的故事来源于本事,其特点在于它是真实性的,而不是杜撰的。纪录片的这种真实性来自于纪录真实和叙述真实两个方面;而在实际创作中,纪录的真实又存在两种情况:照相般的“自体复现”和人为搬演的“情景再现”。对于真实性问题,不同流派的纪录片作者存在不同认识和做法。坚持“直接电影”理念的人只使用“壁上苍蝇”式的纪实摄影方法,让生活事件在镜头前“自体复现”出来;但是其他的纪录片作者则认为“情景再现”并不妨碍真实的表达,有的甚至主张积极介入生活,促成某种真实的潜在可能性的发生。
注释:
[1] [美]Paula Rabinowitz. 谁在叙述谁:纪录片的政治学,第45页
[2] 鲁迅全集. 第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394
[3] [法]让·米特里. 论一般影像. 载《世界电影》, 1988(3)
[4] 艾柯. 电影符码的分节. 载《世界艺术与美学》第七辑,第222页注释
[5] 林旭东. 影视纪录片创作.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56
[6] [法]拉法艾尔·巴桑、达尼埃尔·索维吉. 纪录电影的起源及演变. 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18
[7] [苏联]吉加·维尔托夫. 维尔托夫论纪录电影. 见单万里主编. 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510
[8] 同上,第517页
[9] [匈]巴拉兹·贝拉∶ 电影美学.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44
[10] [美]W.米勒. 非虚构影片的写作. 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437页
[11] [英]约翰·格里尔逊. 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 见《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第500页
[12] 参见[英]弗西斯·哈迪. 格里尔逊与英国纪录电影运动. 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32页
[13] [美]帕·泰勒. 故事片中的纪录技巧. 见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第400页
[14] 同上,第402页
[15] 参见《我无法表现总体真实》,纪拉德·皮瑞采访,载法国《正片》杂志, 1998(3)
[16] [美]林达·威廉姆斯. 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 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576页
[17] 同上,第584页
[18] [美]林达·威廉姆斯. 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 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588页
(作者系武汉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温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