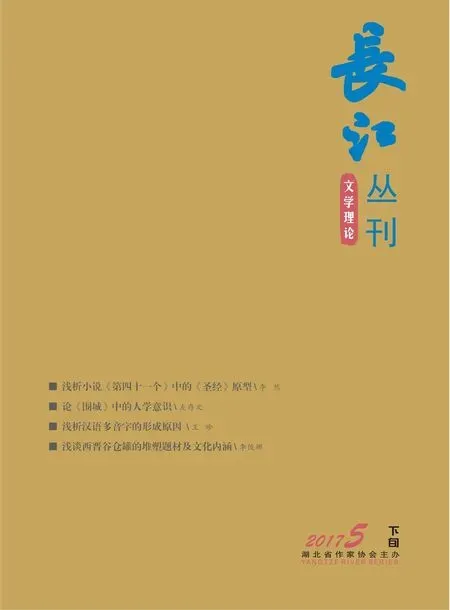文化领导权与苏东剧变
王晨阳
文化领导权与苏东剧变
王晨阳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当今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受到了文化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高度重视。这篇文章将对东西方社会结构进行具体而深入分析,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凸显出来,由于东西方市民社会地位的不同,从而导致东西方在选择革命道路上出现了差异。
文化领导权 市民社会 知识分子
安东尼奥…葛兰西(Аntоniо Grаmsci,1891—193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意大利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之一。他主要活动于20世纪社会大动荡的20、30 年代,他那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是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好诠释。在1926年葛兰西深陷监狱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在理论上的思考,他历尽艰辛写下了长达2844页的书稿和论文,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狱中札记》,在这部书中他进行理论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此书中涉及了极为广泛的理论问题,如历史唯物主义和许多其他的哲学问题,意大利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知识分子等问题,以及工人阶级政党、阶级和阶级斗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等问题。葛兰西在监狱中,创立了“文化霸权”、“市民社会”、“阵地战”、“知识分子”等一系列知名理论,成为了身陷重围的无产阶级的航行标和明亮的灯塔,照亮了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命志士前进的道路。
一、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的凸显



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构成了葛兰西的西方革命观的核心,市民社会在东西方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东西方革命道路的不同。市民社会并不是葛兰西的独创,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有其独特之处。我们知道中世纪末期的城关市民是市民社会的最初阶段,在那时他们以简单的手工业加工和商业贸易活动为主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关市民也就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阶级观念相对淡化的今天,市民社会又与公民社会又近乎相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认识到,市民社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与物质生产领域或者经济领域密切相关,因此,当我们在谈到市民社会时,它所隐含的因素就是“四大关系”即财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它并不具备政治上的含义。市民社会与国家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观念的外化,国家产生市民社会。而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主宾倒置法颠倒了黑格尔的国家观,认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1],“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2]。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在葛兰西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认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国家。在社会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国家功能的发挥,最终在政治上也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并同时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通常被认为是政治社会的强制机构。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国家观上的对立实质上反映的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世界观在国家形成理论上的根本对立。葛兰西最大的突破就在于他并没有局限于唯物与唯心这种对立的二分中,而是随着这种突破,市民社会从社会存在领域上升到上层建筑领域,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并列共同从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市民社会实质上也因此成为了政治活动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缓冲地带,“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2]这就决定了国家行使职能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往国家传统的统治方式已经不再适应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也要求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方式只能是领导而不是统治。葛兰西把领导和统治区分开来,并进一步强调了领导的作用。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上的范畴,它是商品经济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葛兰西认为,东方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商品经济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所以东方社会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在西方国家发展却相对完备且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东西方市民社会地位的相异的决定了东西方国家的性质和差别,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各自革命道路的不同。正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暴力革命观即西方革命观。争夺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是西方革命观的核心,而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实质上就是文化领导权,因此争夺文化领导权就成为了西方革命的核心。“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形成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3]我们从这段论述中能看到在一个市民社会相对完备的国家中,对市民社会的领导实质上占据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市民社会成为国家更具内核性的因素,并且思想意识形态一旦占据人的头脑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是思想的“物质性”甚至比物质更加坚固的一面。思想意识形态对人头脑的控制,是文化领导权最重要的一面。
葛兰西认为,谁能掌控文化领导权谁就有可能赢得并巩固政权。一个社会集团只有首先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即在精神文化领域、意识形态上取得“霸权”地位,才能最终掌控政权。西方无产阶级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客观上革命条件的不成熟,而是在于工人运动不能强有力的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渗透和控制。葛兰西认识到了文化领导权在现代社会中的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在一个市民社会相对成熟的国家里,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与统治阶级争作坚决的斗争去夺文化领导权。对于统治阶级本身来说,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一个通过暴力革命取得统治地位的国家,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统治阶级往往忽视获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就是东欧乃至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苏东剧变的启示
英国在1825年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证明了马克思所预测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但出人意料的是,不管经济危机的破坏性有多大,没有一次能够威胁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统治地位。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深受灾难而没有崩溃,根本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通过“文化霸权”对“市民社会”的控制,而文化霸权归根结底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领导的权利也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西方文化主要维系的自由、民主、平等能够追溯到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国之本,在资产阶级获得统治前及稳固统治后,贯穿于其文化始终的基本精神始终没变,围绕这一自由、民主、平等的主线来进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用了巨大的艰辛努力去夺取文化领导权以及在文化上的统治,资产阶级在其历史长河中已经形成其文化的灵魂,并依靠它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心。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反观无产阶级,从爆发工人运动至今,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内核,更不用说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念深入大众的内心。因此,在整个历史大背景下资产阶级就牢牢的掌控着文化领导权。这个外在的历史背景就构成了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受挫的客观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无产阶级对自身文化的建构仅仅迈出了一小步,相对于夺取葛兰西所认为的文化领导权来说,无产阶级的文化更是具有后天发展的严重不足。 夺取文化领导权,很多人往往把重点放在了人身上,反而忽视了文化本身的重要性。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领导权的根本特征是一种“软权力”的“同意”,“‘同意’是对某种社会政治秩序、某一种政治决策、某种政治行为或某一领导者的认可、赞同、或支持。”[4]很明显,这种“同意”具有自发的非强制性,它比那些外在的强制暴力更具统治力。

东欧剧变以及苏联的解体一方面的原因就在于国家领导人对文化领导权的忽视和误解。不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各国社会经济都相对落后,甚至有许多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壮大到足以推翻本国的封建统治,还没有坚固的实力去夺取国家的政权,更不能去夺取在文化上的领导权。苏军的铁犁铲除的只能是封建势力的外部工事,却忽视了潜藏在内部城堡中的毒瘤,当苏东领导人忙于经济建设时,毒素开始扩散,最终蔓延至整个地区,时刻准备瘫痪整个国家。因此,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文化传统上看,封建反动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仍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其次西方国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演变,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建立开始时,西方国家自始至终就从来没有放弃或遗漏过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入渗透,占据着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占据,对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导权尚未建立的初生时期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但苏东恰恰又忽视了文化领导权,这也是导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应该认识到,这些都是外在的客观原因,不足以主导整个局面的发展。 其根本原因就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决策上的严重失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以后,领导人将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这符合当时的特殊国情,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在不断的形成,市民社会的地位在不断凸显,很显然这一点又被党的领导人忽视了。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但其他社会事务却相对的滞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其有限,一旦经济的发展遇到瓶颈,即使稍遇挫折,也会造成社会的极大动荡。经济斗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对局限性,而意识形态有时却发挥着物质性的政治力量,这也是资产阶级政权在饱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轰击下毅然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首先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对文化领导权的占据缺乏重视,其次党内的领导人对文化领导权有极大误解和看法。他们不能理解占据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葛兰西认为“文化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它懂得自己的历史和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力和义务。”[5]人和动物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塑造了人内心中的人性的部分,一个人价值的依托和归宿就是文化,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领导权的“同意”这一根本特征。徐崇温说:“群众信奉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思维方式的合理性或真实性的真正的批判和检验。”首先一种文化之所以被称之为文化它必须是通过了人民群众自觉的“同意”,其次是人民群众对其文化的自觉信奉。当人们开始自觉地信奉一种文化的时候,文化的稳定性与物质性的力量就能显现出来。因此,统治阶级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把重心放在创造真正符合大众需要的文化上,而非利用统治权力来钳制人民的思想。苏共和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将党的领导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建国初期这种措施确实有其必要性。但这种外在的“全方位的领导”却给自身造成一种牢牢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假象,仅仅依靠制度上的强制措施及大众传播媒介形成一种表层的霸权文化,这完全无法掩盖人与社会深层的根本的内核性的缺失。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主导文化的断裂将整个社会推入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面对这种文化窘境也就不难理解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短期内纷纷丧失政权。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人民群众会对社会主义缺乏认同感,就连共产党内的一些重要领导人的社会主义信念也不够坚定,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以及众多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会自己主动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原因。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脆弱到不堪一击,这种近乎专制的文化统治策略不仅扼杀了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也阉割了自身的生命力,将文化的领导变成了粗暴的统治,对统治阶级文化的这种心照不宣的不接受,只需要一根很小的导火索就足以结束一切。因此,社会主义的生命必须以维系文化的建设与文化领导权的占据为根本。
三、当今文化知识分子使命探究
意大利文”еgеmоniа”翻译为“文化领导权”,这个词所表达的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两个方面,“文化领导权”指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领导权,现阶段对于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人们认为其重要于文化领导权。当然这与当今的国际局势紧密相关,不可否认的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文化领导权的忽视确有舍本求末之嫌。在东欧与苏联革命的教训之下,应该引起世人的警醒。卡尔…利维认为在葛兰西那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是一种对意识形态领域即文化的启蒙和拓展。因此,在葛兰西的内心深处,革命的行动和革命的政治实践并不是以夺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最终目的的,他认为是要通过革命对人民群众进行启蒙运动,也就是创造崭新的新文化,创造新文明,创造新人类。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仍有不足,没有真正的达到文化发展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建设不全面、不牢固、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葛兰西所提出的“市民社会”也在不断地日益显现和成熟。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显著。通过一系列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渗入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党领导的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重要部门。葛兰西认为:“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错误便是在知识分子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这些活动(以及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团体)正是以此在社会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6],在此我们能看到,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不是在掌握知识的多少,而是在于相对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及其他所要担负的责任和作用。一方面人民大众需要知识分子的引导,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应该融入大众,从人民大众中不断充实武装自己。知识分子不仅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的,积极地介入现实社会,深入大众的现实生活中,而且还需了解大众的精神疾苦,探索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去创造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食粮。其次我国的知识分子要勇于担当传播文化知识先锋,这是知识分子不容推卸的责任。知识分子不能弃人民大众而不顾,自己却沉溺于学术研究之中,不能不进行社会实践,而在书房中享乐。最后“学科边界的消解和公共领域对知识分子的呼唤,要求知识分子从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走向广阔的公共领域,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或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7]可见,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对知识分子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但知识分子也只有承担这些职责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从文化的批判到文化的创新再到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的基础性因素。
文化满足的是人的精神性和超越性的需求,文化领导的基础是人民大众基于自身需要的一种认可,所以它必须以人为本,在文化建设中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也只能从人本身出发。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
[3]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王晓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葛兰西,李鹏程.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和磊.葛兰西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