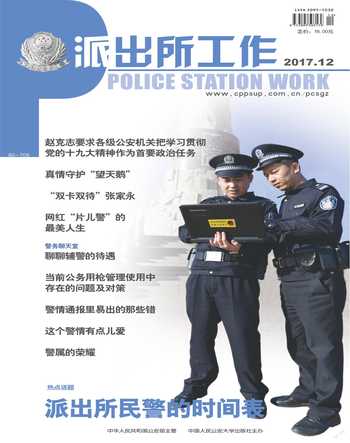警属的荣耀
王菲
2015年在准备我自己的婚礼用品时,我与母亲到了齐齐哈尔。刚从客运站下车,母亲就看到了一座很显眼的建筑物,并开心地指着上面的警徽说:“看,公安局!”我很是诧异:“妈,您又不是第一次看到公安局,怎么到了外地看见它还这么高兴?”母亲回答说:“因为我既是警察的妻子,又是警察的母亲,还将是警察的丈母娘。”说完这话,她自己一下子乐了。看着母亲一脸的荣耀感,我其实心里是难过的。
母亲在24岁的时候嫁给了父亲,虽然同在一个地区,但父亲所在的灵泉派出所离家有段距离。在那个出行基本靠自行车、找人靠打公用电话的年代,往返回家是非常不便的。于是乎就变成十天半个月父亲才能回家一次,所以母亲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娘家。一方面年纪轻、胆子小,另一方面也怕被打击处理过的人报复。有一次,原本是父亲回家的日子,母亲也早早地在家准备好饭食,而父亲却因为案子走不开只能打电话到邻居家的商店。我母亲接到电话后,看到外边黑咕隆咚的天,想到又不能回娘家,也没有别的去处,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那个时候,父亲年轻肯干,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忙活。挑水、买面、买米之类的力气活根本指不上父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母亲临产的日子。
或许是因为多了个我,母亲的胆子大了许多,家里有没有父亲在也成了无所谓的事情。而父亲依然过着单位为主、家庭为辅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他下班回來,正好看到我坐在桌子底下往嘴里塞那五颜六色的不知名的药片(后来知道那是耗子药)。父亲一个跨步,抱起我就抠我的嘴。看我实在吐不出什么东西,马上去了医院。大夫看着我也很为难,因为太小而且精神状态也很好,洗胃还真挺遭罪的,就询问我:“小朋友,你哪里不舒服?告诉叔叔,不然你爸爸都要急哭了。”我一脸愤怒地指着父亲向大夫控诉:“他不是我爸爸,他是坏人,他抠我的嘴。”孩子的话语是无心的,但却戳中了父母的心。一旁的母亲想到了从结婚到现在所过的日子,眼泪就飞奔出来。我扑到妈妈怀里:“打坏人,打坏人,坏人一回家就惹妈妈哭。”妈妈赶紧说:“爸爸不是坏人,爸爸是抓坏人的人。”
经历了这件危险事件后,父亲申请了工作调动,调到了离家几百米远的红卫派出所,母亲一个人撑家的日子也算熬到头了。
没过几年,父亲又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到了东风派出所。有一次因为要出差到外地抓人,来不及通知母亲就让同事张叔到家里转告。张叔看到我的母亲,张口就说:“铁哥走了。”母亲的脑子轰的一下就乱了,哆哆嗦嗦地说:“怎么走的呢?”张叔一看我母亲的样子才发觉自己刚才用词不准确,赶紧解释道:“不是走了,是出公差了,到外地抓个人,十几天就回来了。”母亲“扑通”一下就瘫坐在了地上。很多年后,母亲想起这件事,还在感慨以前过的真是提心吊胆。再后来,有时候父亲开玩笑说:“人家的老头儿出门,电话都不断,你怎么也不给我打电话呢?”母亲就板着脸说:“打啥啊?有事你同事就来通知了。”然后俩人就一起想到张叔那个乌龙事,哈哈大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是一种“活着就很好”的满足。
正是因为母亲知道干警察的不容易,顾不上家不说,还要时时面对复杂的执法环境,所以在我报考志愿时,非让我报一个二本的师范院校。我嘴上应付着但还是报了提前录取的学校,普通院校都是空白。等收到警校录取通知书,母亲和我大吵了一通,很长时间都不和我说话。开学了,母亲送我到了呼和浩特。看着我报完名,她转身就走,一刻都不愿停留。我看着那微弯的背影,追上去抱住母亲,哽咽地说:“你就没啥和我说的吗?”母亲故作坚强地说:“胳膊腿断了别给我打电话说你想回家。”这句话的效果以至于大一的上半学期,我咬着牙也没给她打过一个电话。每次舍友打电话向家人撒娇的时候,我就躲出去。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哭起来,毕竟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就算咬碎牙也要坚持下去。直到现在,有时母亲还会酸溜溜地说:“有轻快的工作不去做,偏偏要干这个没人理解的活儿。”
知道我处的男友是警察时,母亲又被气着了,戳着我的脑门子说:“为什么我说的你都不听?偏要再走一回你妈的老路才肯罢休?”那时我还不以为然。结婚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年轻时妈妈的无奈:明明说好的回家,或者约好的出行,总会因为案子被延期。等到想起之前的承诺时,黄花菜都凉了。我知道,我这个警属做得不够格。我做不到母亲那种为了父亲热爱的事业可以牺牲自己一切的程度。
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老公两人依然忙着各自的工作,母亲“抛弃”了父亲,来帮助我俩带孩子,同时被“扔下”的还有我那年迈的姥姥。每次母亲给我姥姥打电话时,话里话外都是充满了愧疚和苦涩。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女人,自己受苦受累从来不说,反倒关心自己身外的一切。
警属的苦和难,在那庄严警徽的映照下,渐渐化作了一份荣耀。这不是社会给予的荣誉,而是长时间由自豪和委屈沉淀而来。
(作者系内蒙古阿荣旗公安局新发朝鲜民族乡派出所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