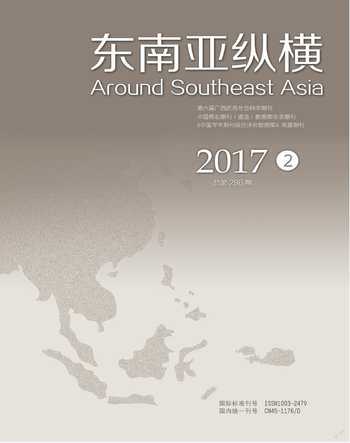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研究:现状、问题与未来
武香君
摘要:中国与东盟之间开展的安全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起步,目前已经形成多层级的安全合作机制,安全合作涵盖多个领域,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已经臻于完善。实际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存在着安全合作实践性欠缺、双方安全合作预防能力不足、当前安全合作缺乏核心机制、双方的互信也有待加强等问题。中国与东盟之间开展的安全合作在未来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加强:中国与东盟要重点加强互信建设;建立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促进中国与东盟携手维护南海安全;促进中国与东盟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
关键词:中国;东盟;安全合作;问题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7)02-0060-08
Abstract: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has started in the 1990s. Currently, China has developed multi-level 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with ASEAN, and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covers several areas. However, all these achievements do not mean that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s perfect. In fact,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has following issues: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has the lack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practices, preven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core mechanism in the current cooperation situation, moreover, the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lso need to be enhanced. In the future,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an be enhanced in four areas: firstly, China and ASEAN need to focus on building mutual trust; secondly, they should build a core mechanism to lead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thirdly, China and ASEAN should secure the safe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ogether; fourthly, China and ASEAN ought to secure the safety of sea channels together.
Key Words: China; ASEAN; Security Cooperation; Issues
從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东盟所在的东南亚地区于中国有重要意义。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中的越南、老挝、缅甸接壤,与这3国的边境线长达4000千米。因而,中国与东盟开展安全合作对确保中国西南部边境安全、确保边境经贸往来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海上与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确保南中国海地区海上秩序稳定、海上通道畅通,而且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中国与东盟之间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安全合作, 经过20多年的合作实践,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安全合作在机制建设与合作内容上都取得了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安全合作已经臻于完善。本文通过对双方安全合作机制和内容的考察,认为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并对未来如何深化双边安全合作提出几点思考。
一、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现状
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包括高层领导人会晤机制、部长级会议机制、 工作对话机制、 东盟地区论坛机制(ARF)等。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的内容亦较为全面,涉及海上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反恐、禁毒以及公共卫生等。
(一)中国—东盟安全合作机制
1. 高层领导人会晤机制。中国与东盟的高层领导人会晤机制是指1997年12月15日首次举行的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3)和同年12月16日举行的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1),其中“10+1”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机制,涉及双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由其做出。截至2016年,中国已与东盟举行了19次“10+1”会议。在“10+1”机制内,中国与东盟颁布了一系列与安全相关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2002年11月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10月签署的《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2010年10月签署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等。这些法律文件为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确立了基本规范框架①。在基本规范框架中,包括以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分歧或争端等为内容的核心原则,和以非正式进程、微区域制度、共识性决策等为内容的决策程序。
2. 部长级会议机制。部长级会议机制是对高层领导人会晤机制的重要补充。目前,中国与东盟分别在12个领域内建立了部长级会议机制,包括外交、商务、文化、交通、海关署长、总检察长、卫生、电信、新闻、质监、打击跨国犯罪、国防等,其中与安全领域直接相关的有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以及双方的国防部长会晤机制。中国与东盟国防部长会晤机制建立于2011年,目前每年均在当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举办。该机制弥补了双方一直以来在国防领域缺乏高层次交流的缺憾,对于双方增强战略互信、推进务实防务合作的开展具有积极影响。
3. 工作对话机制。中国与东盟建立了5个平等对话机制,分别是中国—东盟经贸联委会、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中国—东盟科技联委会、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及东盟北京委员会。其中,中国—东盟高官磋商成立于1995年,每年举办一次会议,轮流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举行,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政治与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在这一机制内,中国与东盟多次就南海问题进行磋商。在2015年6月举行的第21次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中,双方再次就南海问题深入交换意见②。
4. 东盟地区论坛机制。成立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是包括东盟与域外共27个国家在内的官方多边政治和安全对话合作渠道。ARF每年在东盟轮值主席国举行外长会议,中国从第一届起就参加了会议。每年ARF除了举办一次外長会议之外,还举行一次高官会、一次安全政策会议、两次建立信任措施与预防性外交会间辅助会议(ISG)、4次会间会(救灾会间会、反恐与打击跨国犯罪会间会、海上安全会间会、防扩散与裁军会间会)和3次国防官员对话会(DOD)。在2014/2015年度,中国积极参与ARF相关活动,出席了高官会、ISG会议、DOD会议、海上安全会间会、打击海盗研讨会、应对毒品挑战地区合作研讨会、打击极端主义研讨会等。在2016年,ARF在中国举行了5次工作组级别的会议,议题涉及跨国犯罪、 绿色航运、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预防性外交等③。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与ARF以及东盟开展安全合作的积极性,ARF是中国与东盟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
(二)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内容
1. 海上安全合作。中国与东盟为了共同维护周边海洋秩序,确保海上安全,主要在维护南海秩序及打击海盗方面开展了安全合作。
南海海域涉及的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一直是中国与东盟相关成员国在发展双边及多边关系时绕不过去的话题。中国向来秉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11月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东盟通过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机制、中国—东盟高官磋商等机制进一步商讨南海问题,又后续出台了《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10周年联合声明》《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并在2015年7月举行落实《宣言》第14次联合工作组会和第9次高官会,继续为早日解决南海问题做出努力。中国与东盟为了维护南海现有秩序,还在各国海上搜救机构间建立热线平台及外交部门间应对海上紧急事态热线、举行海上联合搜救沙盘推演等。
中国—东盟海上安全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打击海盗。东南亚地区海盗问题十分严峻,严重影响到了域内海上通道的航行安全,对东南亚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利益、海上航行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早在1999年就开展了打击海盗的合作,先后破获了“露易莎”号、“天裕”号等6起跨国海盗大案。在2006年10月,中国签署了《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ReCAAP),该协定由东盟10国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于2004年11月缔结,2006年9月正式生效,其目的在于加强亚洲地区预防和打击海盗及武装劫船方面的区域合作。根据协定,各国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信息交流中心,负责报告海盗活动、调查海盗事件和缔约国间分享资讯①。
2. 经济安全合作。经济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要维护经济安全需要不断发展的经济贸易,也需要稳定的金融货币市场。
中国与东盟开展卓有成效的经济安全合作始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从1998年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到2000年的《清迈协议》,表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信在不断深化,双方为了维护地区经济、金融稳定做出了切实的努力。当2008年再次爆发金融危机时,双方能够冷静对待、携手面对,表明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已较为成熟,这对于维护双方经济发展、增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3. 信息安全合作。中国与东盟在信息安全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主要包括签订相关协议,参加东盟举办的网络安全应急演练(ACID),举办相关研讨会等。
在2005年5月举行的“中国—东盟电信周”上,双方发表了《中国—东盟建立面向共同发展的信息通信领域伙伴关系北京宣言》,宣布将在这个宣言的指导下,建立“中国—东盟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处理协作框架”②。2009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电信部部长签订了《中国—东盟电信监管理事会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合作框架》。
自2007年中国受邀参加ACID第二次演练后,2008年中国再度受邀参加第三次演练,此次演练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各应急组织在Web攻击事件方面的研究、处理、协调和配合③。
2011年,第四届中国—东盟网络安全研讨会举行,各方计划进一步建立双边合作机制,增强信任关系和互助,共同维护区域内的互联网安全④。2013年,第五届中国—东盟网络安全研讨会举行,会上特别肯定了双方网络安全领域的良好合作及取得的丰富成果。2014年,第六届中国—东盟网络安全研讨会举行,与会各方探讨了如何深入开展中国—东盟国家的网络安全应急合作⑤。2015年举行的第九次中国—东盟电信部长会议支持中方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东盟国家计算机应急响应组织合作机制的倡议,一致认为该机制是加强双方网络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⑥。2016年,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应急响应能力建设研讨会举行,与会代表就国家网络安全新挑战、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最佳实践和技术平台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⑦。
4. 反恐合作。中国与东盟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且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有相互勾结的趋势,并都与ISIS有联系,因而中国与东盟必须开展反恐合作。
中国与东盟早在2001年的“10+1”会议上就通过了《反对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将联合反恐列入重点合作范围,并提出一系列反恐计划。次年通过的《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声明》将恐怖主义列为“严重关注”领域。
2004年9月,中国与东盟10国的反恐领域专家齐聚苏州,举行反恐研讨会,就反恐形势及对策措施、反恐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建设、反恐情报工作和执法合作等领域进行交流①。2008,中国军事科学院举办了首届“中国—东盟高级防务学者对话”;2010年,“中国—东盟高级防务学者对话”更名为“中国—东盟防务与安全对话”;2011年第二届“中国—东盟防务与安全对话”举行,此次对话会的主题是“中国与东盟:安全、互信与合作”,探讨了亚太安全环境变化、双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等议题。
中国与东盟的反恐合作除了举行防务、安全会议的形式,还有开展反恐演练、举办专业论坛以及在ARF框架下开展反恐合作等形式。2013年9月,中国参加了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首次反恐演练,中方派出的18人分队参加了包括实兵演练和室内推演在内的全部演练。2014年9月,首屆中国—东盟警学论坛在中国广西南宁举行,论坛重点在湄公河流域的执法合作,打击跨国人口拐卖、毒品犯罪、电信诈骗犯罪及加强国际反恐警务合作等方面开展交流②。2015年,中国承办了第13届ARF反恐与打击跨国犯罪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反恐、禁毒、境外追逃、打击网络犯罪、边境管理等议题展开探讨,并对《反恐与打击跨国犯罪2015~2016年工作计划》(草案)进行了讨论③。
5. 禁毒合作。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开展了禁毒合作,与东盟则是2000年开始在禁毒领域进行合作。
2000年10月,东盟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配合下,在泰国曼谷举行了包括东盟成员国和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及欧盟等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的禁毒合作国际会议。会议出台了《实现2015年东盟无毒品曼谷政治宣言》以及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禁毒合作开始的《中国—东盟禁毒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加强双方的禁毒合作,并通过双方的合作,帮助东盟实现到2015年成为无毒地区的目标。根据该计划,中国与东盟将建立打击毒品犯罪的合作体系以及对合作进展进行评估的机制,并在加强社会禁毒意识、遏制毒品需求、加强禁毒执法工作和杜绝毒品生产等4个领域开展具体合作④。
2005年,中国、东盟和UNODC共同主办了第二届禁毒合作国际会议。会议回顾了2000年以来本地区各国禁毒工作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功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禁毒战略和行动计划。各国部长正式通过《北京宣言》、更新后的《东盟和中国禁毒合作行动计划》和本地区打击苯丙胺类毒品犯罪联合行动的倡议⑤。2013年,中国与东盟在缅甸仰光举行禁毒协调会议。会上肯定了中国与东盟在禁毒执法领域的合作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的贡献,并肯定中国政府与老缅泰3国共同推进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发展,摧毁了糯康武装贩毒集团,倡议开展了针对湄公河流域的“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有力打击了跨境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⑥。
6. 公共卫生领域合作。2003年爆发了席卷中国和东南亚的SARS疫情,同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问题特别会议”,会议签订了《中国与东盟防治“非典”联合声明》,由此拉开了中国与东盟在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的序幕。
2003年还爆发了禽流感疫情。针对疫情,2004年3月,中国与东盟举行了“中国—东盟防治禽流感特别会议”,会议签订了《中国—东盟防治禽流感会议联合声明》,在声明中提出了7项应对措施。
2004年发表的《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将公共卫生合作定性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功能合作,具体谈到了公共卫生合作机制的建设问题,提出要建立防控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一体化机制,建立联合检测和控制机制,探讨建立中国—东盟卫生检疫合作机制等①。
2006年,首届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在缅甸仰光举行,此次会议确定了双方卫生部长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2008年6月,东盟与中日韩传染病信息通报网站正式开通,中国与东盟国家实现了在新发传染病领域的疫情信息共享。
2012年7月,第四届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举行,会议确定了双方卫生合作优先领域,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关于卫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②。
二、当前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存在问题分析
通过以上对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机制与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无论是在合作机制建设还是合作内容拓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已经成熟完善。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还存在着合作实践性欠缺、预防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机制、互信程度有待加强等问题。
(一)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实践性欠缺
通过上述对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内容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与东盟开展的安全合作主要是签订各个领域的“联合宣言”“行动计划”“备忘录”等,对双方开展安全合作做出一个模糊的规划,为了具体落实这些规划,则需要继续举行会议,从而制定落实这些宣言的具体计划。这样一来,当初制定的“联合宣言”“行动计划”“备忘录”不能够被及时付诸实践,其时效性就打了折扣,这就导致中国与东盟落实安全合作措施的周期变长,在应对某些安全威胁时就不够及时有效。且中国与东盟目前开展的安全合作形式以举行会议,举办研讨班、论坛等为主,这样的一些形式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仍然是“说的多,做的少”。这样的形式为双方交流安全领域的实践经验、互通有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固然必不可少,但是在打击海盗、反恐等这样一些需要开展实战演习的领域,双方却并没有开展足够的实践。
中国与东盟的打击海盗合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但是纵观双方近年来的合作,还是以举行会议、交流经验、分享信息为主,实际举行的反海盗演习鲜见报端。
中国与东盟早在2001年就通过了《反对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提出一系列的反恐计划,而在之后的实践中,双方的反恐合作还是以举行会议为主,直到2013年中国才首次参加由东盟举办的反恐演练。而上海合作组织从2005年就开始每年组织一次“和平使命”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同中亚国家面临着“三股势力”的共同威胁,中国与东盟同样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而中国与东盟却没有开展相应的反恐演习。这表明,中国与东盟在安全合作中的实践性还远远不够。
(二)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预防能力不足
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预防能力不足是指双方的安全合作缺乏预警机制建设,对突发性安全事件缺少预报且反应不够及时,应对效果不佳。
中国与东盟开展的公共卫生合作是在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后,这表明此前双方并没有将公共卫生领域作为合作的重点,没有给予其应有的重视。这反映出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有着一定的滞后性。之后,中国与东盟在应对禽流感疫情时就提出要“为建立传染病确认和控制的预警系统而努力”。然而至今,在中国与东盟的公共卫生领域合作中,依然可以见到要加强对疫情进行防控的要求,双方合作的重点还是加强疫情信息交流与共享,经常开展的实践则是中方培训东盟成员国相关技术人员。因而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中国与東盟还是没能建立起完善、有效的传染病确认和控制预警系统。
在安全领域中,不仅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建立防控预警机制,打击海盗、维护经济稳定、保障信息安全等领域都需要预警机制。中国与东盟2009年签订的《东盟和中日韩(10+3)合作应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联合新闻声明》中,就提出要“加强地区监测机制建设”以“监督地区和全球经济形势”;在2015年举行的第九次中国—东盟电信部长会议中,中方提出建立中国—东盟国家计算机应急响应组织合作机制,该机制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提升全局网络安全威胁的分析预警能力。这都表明,中国与东盟已经开始重视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加强对预警机制的建设,也说明在中国与东盟已开展的安全合作中,预防能力是短板,亟待加强。
(三)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缺乏核心机制
中国与东盟开展安全合作有高层领导人会晤机制、部长级会议机制、工作对话机制、ARF等不同层次的机制。其中高层领导人会晤机制有“10+3”和“10+1”两个;部长级会议机制有12个,与安全直接有关的有2个;工作对话机制有5个,与安全直接有关的是中国—东盟高官磋商;在ARF机制下,中国参加了几乎所有级别的会议。如此多的安全合作机制表明中国与东盟开展了非常广泛的安全合作,安全合作从层级上、内容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此多的安全合作机制也凸显出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存在机制过于分散,缺乏一个能够进行统筹控制的核心机制。
缺乏统筹控制的核心机制一方面使得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呈现分散化的局面,各个领域的安全合作没有相互连通;另一方面也导致双方安全合作实践性欠缺,签署的“联合宣言”“行动计划”难以落到实处。
分散化的安全合作带来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实践性不强。以部长级会议机制为例,多数部长级会议一年举行一次,在本年度会议结束之后,由谁来具体落实会上提出的各项计划?即缺乏一个能够继续跟进的实质机构。因而会出现今年会议上提出的举措在下一年依然出现的情况,这不排除是由于实际情况变化不大导致的,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该举措根本还没有开始落实。当然,要在12个领域都建立专门的执行机构操作性欠佳,所以就需要一个统筹规划、执行力强的核心机制来负责各项计划的跟进与落实。
(四)中国与东盟互信有待加强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安全合作之所以存在实践性不足、预警机制迟迟未能建立、缺乏推进合作的核心机制等缺陷,其本质原因还是在于双方的互信程度不够深。开展安全合作意味着信息共享,这些信息不仅仅是关于安全领域现状的一些分析数据,更多的是关于先进技术的分享,甚至是国防军事领域一些尖端科技的共享。没有彼此高度的互信,这种透明化的举措很难实现。
目前,中国与东盟各方面合作势头良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足够信任彼此。虽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落实良好,但在南海争端彻底解决之前,这仍然是双方的一个“心结”,且相关国家还是会偶尔挑起争端,并求助域外大国企图在南海问题上压制中国。作为东盟邻居的中国,近年来愈发显现出大国风范,这让东盟国家喜忧参半。“喜”的是随着中国全面发展、经济实力增强,与东盟的经济往来不断增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硕果累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东盟国家的发展大有裨益;“忧”的则是与一个崛起大国山水相连,其是否会谋求称霸本地区、压制自身?这些担忧使得东盟在与中国广泛合作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合作。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与东盟积极开展安全合作,但是东盟仍然对中国不信任,需要借助域外大国对中国加以制衡。中国与东盟在互信构建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
三、中国—东盟安全合作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中国与东盟需要重点加强互信建设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之所以存在诸项不足,最深层的原因就是双方互信程度不够深。东盟仍然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在与中国开展密切交往的同时,也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展多项合作,此举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东盟国家与美日等国开展合作除了谋求自身发展的意图之外,不可否认地还存在着制约中国的战略意图。东盟对中国存在不信任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东盟与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导致了东盟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存在担忧。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差异难以根本消弭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需要通过加强政治安全对话来打消双方的疑虑。目前,双方的政治安全对话渠道多样,对话内容也较为丰富,要进一步消除猜疑,整体实力较强的中国需要为东盟提供经济与安全公共产品,也要尝试利用新途径来加强与东盟的实际性互动,在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深化互信。
1. 中国应积极向东盟提供经济与安全公共产品。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区域大国,有责任将自身的发展红利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惠及周边国家,从而以发展促安全, 共享亚洲和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将借助“一带一路”建设,“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①中国向东盟提供的公共产品应主要是贸易优惠、发展援助、投资便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保障等①。
2. 中国与东盟可联合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除了向东盟提供公共产品以消除阻碍双方互信的障碍之外,还可以与东盟通过一些新途径来加强互动合作。例如,中国与东盟可以一起参加联合国组织的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在这些联合行动中增进相互了解,协调彼此行动,理解各自的行为方式。中国从1990年就开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截至2015年,中国已参加联合国24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30178人②。且中国设有国防部维和中心和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培训中心,为维和行动培训专门人才。在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举行时,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在“东盟共同体:一体化的新起点”分论坛发表演讲时提出,倡议建立东盟维和部队。如果能够建立维和部队,为自然灾害或发生冲突的地区提供人道主义的帮助,在患难中同舟共济,无疑能够加强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③。若东盟维和部队成功建立,中国可与其商讨共同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通过这一途径增进彼此了解,在实际行动中深化互信,为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不断深入开展扫清猜忌与疑虑。
(二)以中国—东盟中心为依托拓建安全合作机制
中国—东盟安全合作中缺乏实践性以及具有重要作用的预警机制迟迟未能建立,不仅是因为双方互信不足,还因为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机制太过松散,缺乏一个能够统领双方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
中国与东盟开展的合作涉及经济、文化、旅游、科技等许多领域,但并非只有安全领域的合作存在实践性欠缺、需要建立核心机制的问题。若上述每个领域都建立一个统筹规划、致力于落实“联合宣言”“行动计划”的核心机制,那么不仅操作上难度巨大,且会出现机构重复、核心地位缺失的现象。所以,与其说要建立一个统领双方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不如说要建立一个统领双方合作的核心机制,该机制具有落实安全合作各项措施的职能。
可以以2011年11月成立的“中国—东盟中心”为核心开展机制建设。目前其定位是“中国和东盟十国政府共同成立的唯一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东盟中心致力于促进贸易、投资、教育、文化、旅游五大重点领域务实合作。”④从其定位中,可以看出中国—东盟中心目前所涉及的领域是贸易、投资、教育、文化和旅游。中国—东盟中心前任秘书长马明强表示,中国—东盟中心是“信息、 咨询和活动的核心协调机构”,并“将努力推动中国—东盟各领域的务实合作”⑤。
由此可见,中國—东盟中心非常适合成为统领中国与东盟各项合作的核心机制:首先,其级别够高——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次,该中心自成立之初就将推动双方务实合作作为重要任务,只是目前该中心并没有将安全纳入工作范畴。在未来几年里,中国—东盟中心可以开始适当拓建安全领域的功能,建议:
1. 可以在中心建立“早期预警与反应系统”,在监控市场波动、预报自然灾害、防治传染病、预警网络攻击等方面发挥作用。
2. 可以尝试建立“中国—东盟待命部队”或“中国—东盟快速反应部队”,为及时、有效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做好准备,以便能够迅速控制事态发展,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
3. 拓建中国—东盟中心,致力于在东盟各成员国和中国的其他地区设立分中心。这些分中心的设立将为中国—东盟的“早期预警与反应系统”效用扩大化产生积极影响。若该系统得以成功运作,那么在其成熟之后,可在各分中心特别是湄公河、马六甲海峡、南海海域以及中国的广西、云南等与东盟国家紧邻的边境省区设立与中心同步运行的“早期预警与反应系统”,使得中国与东盟的预警机制建设能够覆盖面更广、效用更大。
(三)促进中国与东盟携手维护南海安全
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之间存在的南海争端不仅影响到中国与相关当事国的双边关系,也深刻影响到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就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后续就落实《宣言》达成了共识,遵循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在南海地区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态势。但是近几年来,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不断在南海海域制造事端,特别是所谓“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的出台更是将南海问题进一步激化。加之域外国家美国、日本、印度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积极介入的姿态,使得南海海域安全受到威胁,也使得南海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
使南海问题不断“东盟化”是南海声索国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因为这些国家认为自身在中国就南海问题组织的双边谈判中难以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政府间组织,致力于维护东南亚国家的团结与发展繁荣,不可能对部分成员国“言听计从”,因而在南海问题上,中立与和平是东盟的基本主张。东盟中的泰国、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等成员国都不希望东盟卷入南海的主权争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曾表示过对南海争端持中立立场,在东盟历次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中也强调,东盟在南海问题中持中立立场。且东盟一贯主张通过和平与对话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这与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维护者的定位相符合,同时也与中国一贯的主张相吻合。
因而,在目前南海问题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抓住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切合点,首先扩大双方的共识,突出在非主权争议事务上的合作,给双方关系做“加法”,共同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安全。其次,中国与东盟应继续就南海问题保持现有的良好互动,中国坚持一贯的立场不动摇,东盟也保持中立,不在相关声索国与中国的双边争端中扮演“挑事者”的角色,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只有在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相关国家才能够开展卓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争取早日在南海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促进中国与东盟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
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过程中,中国应当致力于成为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责任国。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量巨大,且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加之海域的封闭或半封闭特点,海洋运输对海上通道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①。因而,海上通道的畅通与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东南亚地区有着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进口、向中东、非洲、西欧运输货物的重要海上通道,关系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此外,中国通往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货物运输则依赖巴士海峡、龙目海峡和巽他海峡。上述重要海峡皆位于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为了争夺对这些海峡的控制权曾发生过多次战争,其重要性从古至今不曾减弱。但是,目前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基本上置于美国的战略控制之下,这对中国的海上通道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不仅如此,日本、印度也早已开展了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的安全合作,通过双边军事合作、双边军事演习等加强自身在马六甲海峡的军事存在。
面对中国在上述海上通道面临的被动局面,中国应当积极开拓思路,加强自身在维护上述海上通道安全中的作用,在作为重要使用国的同时,也成为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责任国。这不仅是为了保障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鉴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已经与海峡沿岸国开展了多样化的合作,那么,留给中国继续拓展的空间实际非常有限,加之这些域外国家开展此类合作的意图之一就是抑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存在,中国一味地重复这些合作形式则既无意义也难以引起海峡沿岸国的兴趣。故而,中国不妨与东盟开展维护区域内海上通道安全的合作。
积极参与ARF框架下的多层次交流。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始终都是沿岸国的重要安全考量,在东盟历次外长会议以及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中亦是重要议题,其中,ARF更是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作为多次论坛会议的重要议题,并且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中国向来都是ARF的积极参与者,并且与之开展了良好的合作,那么就可以以此为平台,参与到东南亚地区海上通道的维护中来,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作为与东盟开展安全合作的重点内容。在此之前,中国可以同东盟共享打击海盗、海上反恐的相关情报信息, 加强双方在打击海盗、 海上反恐、 海上搜救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可以对东盟相关人员提供培训,并给予物资上的援助,让该领域的合作逐步展开,为日后双方开展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巡航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杨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