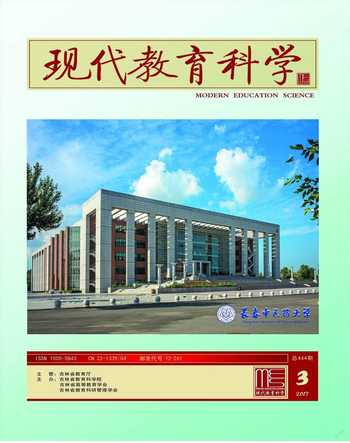蔡元培教育独立思想探源
李丽丽
[摘要]蔡元培的教育独立思想与西方的学术自治思想如出一辙,这种本土的先进教育理念对20世纪初和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实践是多方原因共同作用形成的,探明蔡先生教育独立思想的来源,对现今的教育思想改革也是一种历史的关照。
[关键词]蔡元培;教育独立;背景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7)03-0112-04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703023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针对民国时期的教育现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独立”的思想。
蔡元培倡导教育独立于政治。他认为教育的本质首先在于帮助学习者开发自己的学习潜力,授予知识,提高技能,健全其人格之用,而非带着强烈的功利性去把被教育者当成器具去应用以达到本人或本集团利益。“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1]。
蔡元培主张教育脱离教会。他认为:“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凭着前人的成绩,更加一番努力,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的:无论怎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公同的……都没有什么界限。教会是差别的……等等派别的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2]
蔡元培坚持教育经费专用。蔡元培在《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中指出,教育经费意欲保持独立,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便是把它纳入总理的政纲之内。1927年12月,蔡元培与孙科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交了轰动一时的《教育经费独立案》。此法案提出:“通令全国财政机关嗣后听有各省学校专款及各种教育付税暨一切教育收入,永远悉数拨归教育机关保管,实行教育会计独立制度,不准丝毫拖欠亦不准擅自截留挪用,一律解存职院、大学院听候拨发。”[3]
蔡元培坚持教育内容独立。自古以来,学校与政府之间就存在着教育权利之间的博弈,由此不断地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鉴于教育的发展需要受到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人口状况的影响和制约,蔡元培坚持提倡教育内容独立,反对政府对教育内容把控。此外,他认为教育方针也应该同样的保持稳定,而不应因为政权更迭而随意地变换。
一、思想成因之一:民国的时代背景
毋庸置疑,蔡元培教育独立思想的提出与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蔡元培出身商贾之家,身处封建王朝,后来却成为了民主革命的开拓者和实践者。蔡元培少年得志,成为清朝翰林,后因戊戌政变失败转而弃翰林身份而去。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一职,后来由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蔡元培遂开始游历西欧,达四年之久。1916年黎元洪政府邀请其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以此为契机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大学。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让蔡元培深切地感受到了民国政府更迭频繁给教育事业带来的危害。
民国初年既已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北洋军阀政府政权频繁更迭,教育随风飘摇。这是蔡元培教育独立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时的教育不仅未能根本改变依附政治的局面,还遭遇到了因军阀混战和政权频繁更迭所导致的行政不独立以及经费无着落的情况。1921年蔡元培在美国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针砭时弊地指出:“国家金钱,不用以兴利举废,而为兵所消耗,武人拥兵自雄,杀人盈野,以吾人脂膏,尽充军饷,全不想国家若危,己焉能安。”[4]由于教育经费奇缺,高等学校各项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招生人数更是受到严重限制,不能全数收纳。如何使得教育经费与军用经费划清界限,互不干扰,继而使得全国教育事业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唯有教育独立。随后,1922年2月的全国学生教育独立会成立并发表了以下宣言:“教育事业,不仅为一国之文化所系,亦即人类精神生活之所寄托也。近年以来,兵燹频仍,政潮迭起,神圣之教育事业,竟飘摇荡漾于此卑污龌龊之政治军事漩涡之中,风雨飘摇,几濒破产。此同人不能不作‘教育独立之呼声,以期重新建设精神生活之基地也。”[5]教育因政治的牵连,而变得朝不保夕。教育唯有脱离政治的频频干预,走向独立,才会有希望。在当时列强侵略与国内政党政权更迭频繁的年代,如果教育权交给当时政党,那么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等等也要随之而变。如此一来,这种频繁变动无疑会给教育发展造成巨大伤害,难免造成文化断层,教育断层的局面。蔡元培指出:“政党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6]
二、思想成因之二:西方教育思想的触动
其实在清末中国已有教育独立思想,如清末章太炎在其文《代议然否论》中提出了关于教育独立的独特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于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7]严复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中提出了“政、学分途”的主张 [8]。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提出了学术独立的主张:“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9]但更为使蔡元培深受触动的是其在西欧留学期间接受的思想洗礼。
1919年6月蔡元培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道:“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10]1919年9月,蔡元培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重申民主治校的理念:“德國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11]随后,秉持着“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为尊”的信念,蔡元培一生前后赴德3次,历时5年之久。在游历德国期间,蔡元培着手翻译了柏林大学博士包尔生著名的《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他认真研究德国教育制度,马不停蹄地考察莱比锡大学、汉堡大学、柏林大学。他发现了德国大学的一个亮点便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注重学术研究,实行教授治校。德国教育次长贝克曾说道:“德国大学在学问上、研究上完全自由……大学设有评议会,由校长、院长、前任校长及各系推举的教授组成。”[12]德国大学之自由精神和民主化的管理方式,深深地触动了蔡元培。洪堡认为:“公共教育应该完全处于国家作用范围之外。”国家总是赋予教育一定的政治色彩,希冀培养符合国家要求的“标准公民”,来追求社会安定,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公共教育的自由,使得整个社会“缺乏任何对立力量,因而缺乏任何均势”[13]。针对中国教育的历史现实,蔡元培开始思考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独立思想。
三、思想成因之三:传统科举制积重难返
中国传统教育是统治者进行封建统治的附庸。在教育内容上主要突出儒家经典,着重历史知识、写作书法。且偏重于伦理道德,忠孝节义等思想的灌输,是“既不教数学、自然科学,也不教地理学及文法,极端封闭且墨守经文的教育”[14],是一种“具有传统主义的、伦理的”教育[15]。科举教育采用以教师灌输为主,强调死记硬背,而忽视思维训练和培养创新精神的教学方法。最终不过是为封建统治者培养忠君的奴才。循规蹈矩、毫无生气、书呆子、创新能力低下成为科举制度下所谓“人才”的标签。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并实施新学制,讲授内容从传统的四书五经转为以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为主。废除科举制,所培养的人才不再以科举仕途为目标,而是转向社会发展需要的不同类型的岗位。但是,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太久。
四、思想成因之四:教会学校侵蚀主权
近代教会学校的存在也是蔡元培教育独立思想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据1920-1921年度统计,天主教会所属男校3518所,学生83757人;女校2615所,学生53283人。由此可知,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迅速[16]。中国近代的教会学校无论是基督教教会学校还是天主教教会学校,都同时具有宗教、教育、政治三重属性。谢卫楼在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对教会学校作用进行了阐述:“教育是未来中国的一种力量,基督教会必须为了基督使用这种力量。教会必须积极办教育……这样就可以使基督徒占据有势力和有影响的位置,在政府里做官,做传授西学的教师,当医生,当商人,或在中国早已开设的大企业中当督办。”[17]通过教育活动来进行布道宣传,既可以吸引众多的民众皈依基督教,又可以消除民众的敌意,一举两得。传教士戴洛在《我们英语教学目的》中说道:“英语学习乃是作为引诱中国学生的香饵。……交给学生宗教知识是我们学校的最终目的,英语不过是宗教药丸的糖衣而已。”[18]教会学校开设课程的目的是借助宗教教育变相地使得“中国皈依上帝”,并且假借传播基督福音和传授科学知识之举来堂而皇之地“推进上帝的事业”,其本质是使中国人成为西方列强的奴仆[19],从而来组建“耶稣基督对世界的统治”[20]。
此外,教会学校还严重侵害中国的教育权。教会学校有自己的序列,享有特权。譬如可以自主制定完备的教学体系和正规的学校制度,校长由教会直接任命。教会学校向外国政府注册,且高挂教会学校主办国国旗,不受中国政府束缚,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此种情景中,任何人想要独立自主的发展教育事业都无出路可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外来文化渗透使得中国教育出路狭隘,想要拓宽教育道路,获得中国教育主动权,坚持教育独立于教会势在必行。
五、思想成因之五:民族救亡迫在眉睫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把中国国门打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家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头。此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代表人物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21]。此时,教育已经被提高到救亡图存的高度了。民国时期的教育救国思潮表现的更为突出。由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政治改革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政治改革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由此教育改革的作用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众有识之士,譬如胡汉民、陶行知、黄炎培等人认为“共和国主权在民,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实属大多数,更不知民主政治为何物” [22]。由此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之最要手续” [23]。黄炎培等人认为教育乃是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唯一方法,为此需要全力以付诸实施。且辛亥革命之后国家由于战争频繁而陷入极大的财政困难之中,蔡元培明确主张:“筹划贫民生计,须提起彼等独立的精神,授以适当的知识与技能,这非使先受一种职业教育不可。”[24]随后以知识阶层为主要代表的晏阳初、陶行知、王光祈、李石曾等人再起掀起了教育救国的高潮。教育救国思潮主要包括从文化角度出发的乡村教育思潮,从社会现象角度出发的工读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实业教育思潮等。此时的教育救国论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贫穷落后,备受西方列强欺凌,其根源在于人才缺乏,换言之即教育落后。因此蔡元培积极提倡把发展教育作为挽救民族危亡、彻底改造社会状况、提高人民素质的最佳途径。
参考文献:
[1][2][5][6]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585,375,169,585,585
[3]蔡元培.蔡元培教育文集[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433.
[4][2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89-190,215
[7]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06.
[8]严复.严复集:第一卷[M]中华书局,1985:89.
[9]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39
[10]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32-633
[11]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405
[12]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80
[13]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4-75
[14][15]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49,149
[16]李东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478
[17]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09-310
[18]王炳照,阎王,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五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397
[19]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69
[20]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26
[21][22]冯祖贻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759,10
[2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51
Abstract: The Education Independent Thoughts of Cai Yuanpei is exactly same with the thought of western academic autonomy. This kind of local advanced education idea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later generations. The 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this kind of thought is formed by the joint action of many reasons. It is also a historical concern to prove the origin of CAIs independent thought of education for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thought.
Key words: Cai Yuanpei; education independence; background
(责任编辑: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