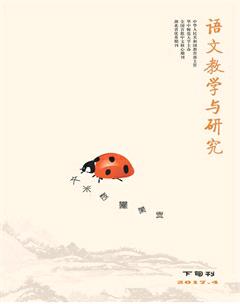最好的生活
杨徵羽
能拥有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
这是哥哥带我去清嘉弄时说的。出门前,他拉着我的手和爸爸大吵了一架。我茫然地被他拽着,直到我们坐大巴来到清嘉弄的弄口,我才慢慢问哥哥:“放弃一个很好的工作,偏偏要出国,值得吗?”他沉默了一会儿,才有些认真地看着我说:“这不是我很想要的生活。”
处暑快要结束了。小弄的那头来的是活水,河流绵延流向西,仿佛没有尽头。哥哥领着我去戏楼听戏。我听不懂戏曲的词调,一边剥瓜子一边问:“戏什么时候结束。”“要一下午呢。”我瞪大眼睛,“不累吗?她会唱坏嗓子的呀。”哥哥说,那是谋生之路。她谋生的方法复杂却又简单,就是让她的戏曲飘进人们最本真最热爱的地方。哪怕是轻触一下心弦,她就不累了。
我厌听戏,硬拉着哥哥离开了小楼。那戏台上黄的红的幕布,被风吹得轻轻摇摆。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感觉,哥哥要和我分別,他说他要去寻找最好的生活。我紧紧牵着他的手,紧得不想松开,他的手心暖暖的。
我们默默地顺着河岸走。清嘉弄虽是旅游景点,可这时不是旺季,倒也出奇地清净。平日哥哥没事常来这里写生,听戏。我知道爸爸对他一直都不大满意,有时候会唠叨几句,后来就不再管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要离开这里的原因。
正想着,哥哥的脚步停下了。我们面前的小摊边上坐着一个老妇,微微笑着,眼神很安静。她注意到了我们,便起身招呼,“吃西瓜咯——一大个五块钱,便宜咯。”我和哥哥随地坐下,地很干净。她收了钱,把西瓜切成两半。我抱着西瓜啃的时候,哥哥拍拍我的肩:“让奶奶给你介绍一下这里的特色。”奶奶好一会儿才听懂,说:“都是特色。”我不解地皱眉。她指着天说蓝,指着水说清,指着门前清嘉弄的青石板街道说古——最后楼上有人招呼她,稚嫩的嗓音唤“奶奶”。她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对我们说道,“我上去看看我的孙女,你们吃好把勺子留下就行咯。”
我和哥哥在暮色中登上弄口的钟楼。钟已经没人敲了。夕阳下的老钟,呈古铜色,融入薄暮,线条变得柔软模糊。从看台上俯视清嘉弄,弄里人家陆陆续续亮起了灯光。渔樵晚山,万家灯火,时间在这里,亘古不变,又“如同蜂翅般微微震荡”。现在想来,那时我与哥哥都一定萌生过永远停留在此的念头,但只是转瞬即逝——仿佛“黑夜里吹动树下青草的一阵悠风,你大可不必将它确定,因它是生活中神圣的偶然”。我握住哥哥的手,又马上松开。我忍不住地质问他:“那个老妇、那个戏子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他们待不够,你为什么——”
他缓缓地收回快要融入暮色的眼神,有些无奈地看着我:“这是她们的生活。她们有她们想要的生活,在这里安安静静一辈子,照看后辈、卖卖水果,唱唱戏。你不明白……我不是这样。”
离开清嘉弄的时候,我没再牵着他的手。我知道我长大了——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每一分每一秒,其实我们都在成长。
我记得那夜回家时亮着的等候的灯光,也记得送哥哥离开时他其实是流了泪的,却顷刻间被黎明的风抹干。我长久坐在机场的大厅里,透明的玻璃上我看见了那个钟楼。
我希望每个人在寻找自己所爱的——不仅仅是生活——路上都有人启发、有人支持、也有人阻碍:可能是给戏子上妆的那双手,把彩粉描画得妩媚;可能是老妇孙女那稚嫩的童声;可能是保护我又将我推进风雨中的哥哥;或者任何人。
这便是最好的生活。
学校: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实验中学;导师: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