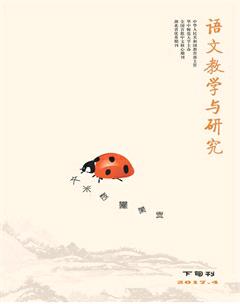旧日红
董桥
我偏偏好说我是遗民。最近坊间邂逅几柄美丽的旧折扇,有两柄分别是阮性山和郭若愚画的墨梅。寒梅幽雅,灵石清癯,这么的风月当是边远的绝响了。配起时下这满城新潮和满街俗物,不啻在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浑似千瓣心香。
一年孟冬,老师亦梅先生来香港过年,礼拜六下午到我家谈天,说起他早年镇宅之宝王冕墨梅册页,最近有人出美金重价要买,弄得他心境不宁。那本册页我曾翻过好几回,还经老师逐页给我指导,册页所附历朝文士的题咏后来也都影印在老师诗集的附录里,八成以上我都背诵得出。我劝老师不要卖,老师说:“这不是第一回的引诱了。你该还记得萧姨吧?她耳提面命要我留给子孙。”
萧姨跟老师同龄,常年穿着浅色丝绸旗袍,斑白的头发梳得丝丝服贴,圆圆发髻永久插着一枝翡翠发簪,宽宽厚厚油绿得谁也舍不得雕刻,只沿着四围阳刻一道细致的花边。我忍不住赞扬两声。萧姨乐透了:“傻小子,等你讨个俏媳妇儿萧姨送你做聘礼!”萧姨天天拜佛画画吟诗吃燕窝,滑腻的粉红肤色衬着精致庄重的五官,简直是钱慧安的淡彩工笔仕女。
老師说,上海当年有个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团社叫星社,社里骚人墨客都是萧姨父亲的诗友画友,萧姨家里藏了一柜子清末民初大小名家的精品。一天下午,老师刚在书房里给我改好一首七律习作,萧姨来了,随手拿去一看,夸我终于摸出旧诗的门道:“轻愁写得够古秀了!”她那天兴趣好,硬拉老师和我到她家喝下午茶。天气清爽微冷,萧姨一身粉蓝旗袍,套上一件薄薄的墨绿毛衣,连老师都说她漂亮:“冷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
萧姨家在城郊清静的斜坡上,深宅大院方圆花木万千,像个小植物园。正宅是荷兰洋房,大厅当中挂着颜文梁一幅大油画,画江南水乡人家,浓浓的油彩抹成粗粗的笔调,远观竟成一片迷茫的雨景,石桥两旁的树影人影都在动,小船过处,滟潋的灯影立时浮起宋词元曲的娇韵。我在她家后园的书斋“春绿馆”里果真看到了不少当时名流的书画扇子。
萧姨誊录了一小本藏品清单和书画家生平,亦梅先生认为有些参看价值,要我借去抄写一份。七十年代,我在伦敦的学院图书馆里借了诸多鸳鸯蝴蝶小说散心,翻出那份清单,竟像旧爱重逢,深切极了。这几十年来混迹市廛,心境迟暮,寄情玩物,收了印石、竹刻、砚台、玉器,收字画、收折扇,那份清单固然残破含混了,心中倒是印得深深的,碰到萧姨春绿馆里那些似曾相识的姓名,总是横不下心任由他们流浪坊间。文化遗民的痴想显是越老越浓了。
去年早春,开书画店的友人收到一柄黄淡如的淡彩工笔张骞泛槎图折扇,我又想起萧姨手头那柄浪子燕青夜会李师师的细笔扇子。我年轻喜好《水浒传》,只顾把玩半晌不忍释手。“傻小子,这把不能给你,”她说,“萧姨改天写信到上海找人请房虎卿替你画一柄武松打虎!”我到目前还只买到房虎卿两柄折扇,一柄画清秋佳品,一柄画云龙山虎,心中暗怨萧姨当年敷衍我。
那个礼拜六下午,我问亦梅先生萧姨还常不常来函?老师说她两年前下世了:“春绿馆里那批书画也全泡汤了!她儿子不懂这些国粹,苏州有个远房亲戚说是能够卖个好价格,她儿子真的全运回去了。”老师频繁摇头叹气。“那里头有仇英,有董其昌,有八大山人……萧姨头上那支翡翠发簪倒在美国卖了好几万美金。那叫春风又绿蕃国岸!你知晓那春绿馆取的正是萧姨宝爱那支翡翠的心意吗?”
我知晓的事情少得很。老师和萧姨那一代人一走,月光下的茶也凉了,害我这么的半吊子旧派人熬过了大半个世纪还嫌自己旧得不够地道。
老师回厦门三四个月了,突然寄来一柄残旧的折扇,是民初名头不大的画家画的武松打虎,还有一封短简说:“偶得此扇,忆起三十多年前春绿馆中往事,代萧姨买下送你。”那几天,我时常想起萧姨的粉蓝旗袍和墨绿毛衣。
(选自《旧日红》)
——传统与现代风格的巧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