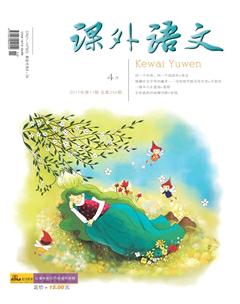隐藏在文字里的魔术
同学们,我们每天都要刷牙,刷牙前要挤牙膏。你注意过你们一家子是怎么挤牙膏的吗?
也许,你是直接从牙膏顶部挤的,你妈是从牙膏底部一点一点向前挤的,你爸是从中间挤的。每个人挤牙膏的部位、快慢、多少都不一样。这就是细节。
细节在生活中,也在工作中。
有一个报道,说郑州有一个神探,很多人仰慕他的神力。他告诉记者,自己只是注重细节而已。有一次,二七纪念塔旁边有个小饭馆夜里失火了,人和物都烧得面目全非。公安人员请他也去看看,他得出一个和别人完全相反的推论:杀人后纵火。他观察到小饭馆里有张桌子全烧黑了,但抽屉的铁挡板在桌上扣着,桌上有一块没有完全烧黑。他从这个细节判断:很可能是盗贼来抢钱财,开了这个抽屉,把铁挡板放在桌上,然后和主人发生了争执。后来深入调查,发现果然如此。
细节自然也体现在文学作品里,把以上细节写下来,就可以是一篇有生活气息的文章。请同学们看一段金庸先生《射雕英雄传》中的文字:
两人去轩辕台路上遇雨,郭靖道:那么咱们快跑。黄蓉摇了摇头:靖哥哥,前面也下大雨,跑过去还不是一般的淋湿?郭靖笑道:正是。黄蓉心中却忽然想起了华筝之事:前途既已注定了是忧患伤心,不论怎生走法,终究避不了,躲不开,便如长岭遇雨一般。当下两人便在大雨中缓缓行去。
这段文字写得别有味道。郭靖一生为国为民,堪称侠之大者,明知前路风雨如磐,依旧豁然前行。聪慧的黄蓉虽知前方亦是大雨,但既然靖哥哥说了“正是”,便毅然決定陪他走在风雨中。该段文字通过遇雨这一细节,奠定了两人的爱情和一生:君往我亦往,白首不相离。
说到文学作品中的细节,不少作家有精彩的见解。池莉说:“我偏爱生活的细节。我觉得人类发展了这么多年,大的故事怎么也逃不脱兴衰存亡、生老病死,只有细节是崭新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群,拥有绝对不同的细节。”李准认为:“没有细节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真实的细节描写是塑造人物,达到典型化的重要手段。”恩格斯把“细节的真实”列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基本条件之一。高尔基则把细节描写称为“隐藏在文字里的魔术”。可见,细节描写至关重要,它具有神奇的魔力,足以决定一篇文章的成败。
那么,什么是细节描写呢?
细节描写是对事件发展和人物的肖像、语言、心理、行动以及环境等所做的细腻而具体的描写。也就是说,抓住生活中那些具体的、细微的、富有特色的情节,把它们生动细致地描绘出来,用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物的复杂性格,烘托故事的氛围,推动情节的发展等。一篇文章,有了成功的细节描写,才能赋予文字生动感和真实感,给读者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感受。
写好细节描写,是有章可循的。
一、化概括为具体
有的同学写文章,特别爱用成语等非常有概括性的词语,觉得这样写显得词汇量多、有水平。比如写班上的同学聪明,有位同学这样写:
我班的王凡雪可以说是机智过人、冰雪聪明、见多识广、伶牙俐齿、精明能干,怎么说呢,就是一句话,太聪明了。
这段话是否让你哑然失笑?用了这么多成语,读者还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这个王凡雪同学到底有多聪明,更无法让大家喜欢上这个人物(不过,倘是以搞笑的方式作为开头还算可行,因为后面还是要安排具体的细节)。
再来看这段话:
在气氛欢快的语文课上,常常会出现一些课本剧表演和分角色朗诵。在这种时刻,当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章小黑总是第一个举手。在上《吆喝》这堂课时,章小黑要学街上的大伯大妈扯开喉咙喊,我正想看笑话,没想到他挠挠头,马上酝酿好了:“卖麻糍——卖麻糍咯——”这东阳的方言竟然说得比我还要标准!明明他刚来东阳不久啊!真是牛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阿秋老师让我上《好嘴杨巴》这课时,我安排了一个课本剧,有意让章小黑上台表演。在课文里,杨七杨巴可是要磕头的啊!我看他能用什么方法解决。
章小黑和另一位同学上台了,念台本念到磕头的地方,章小黑用手背在地上敲了起来,咚咚咚的声音居然很有磕头的效果。他的脑袋跟着一起一伏的,没多久,手背都拍红了。我着实吃了一惊,看来章小黑的应变能力真是不可小觑啊!
——选自学生陈佳瑶《牛人章孜勤》
陈佳瑶同学的这段话,把人物放在具体的情节和环境里,章小黑吆喝卖麻糍的声音和以手代头咚咚咚的磕头声,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细节描写要慎用成语,慎用“很”一类的程度副词,尽量多用直观感觉的词。
再请同学们欣赏古龙小说《三少爷的剑》中的文字:
浓雾、流水。河岸旁荻花瑟瑟。河水在黑暗中默默流动,河上的雾浓如烟。
凄凉的河,凄凉的天气。
谢晓峰一个人坐在河岸旁、荻花间,流水声轻得就像是垂死者的呼吸。他在听着流水,也在听着自己的呼吸。
流水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可是他的呼吸却随时都可能停顿。
这段话通过描写环境来衬托人物孤独绝望的心情。细节的呈现非常有力度。换作我们来写,也许就直接成了:他来到河边,河边有很多花。看着流水和花,他空前地绝望。
花是有名字的荻花,流水声像垂死者的呼吸。如此一具体,文字的味道和人物的心境全部跃然纸上。
接下来,请同学们看一篇本人写的《七月》。
七月
他的视线被一望无际的稻田吸引。那是怎样的黄啊,带着明艳,带着清香。他忍不住狠狠地吸了一口。那味道,有些生猛,有些呛人。
可不,没有一丝风,地上就像下了火。爹和娘半蹲着身子,沙沙沙的割稻声很有节奏。他刚走下地,就被爹喝住了:“回家去!凑什么热闹!”
爹就喜欢这样说他。他就是不明白,他都长大了,为什么不能为家里出一份力?
从小,他就被爹当女孩似的养,这活儿不让干,那活儿不让干,到如今,18岁的他,两手还白嫩嫩的,老被同学笑话,说他像个城里人,不晒太阳不干活儿。
小时候,他也有和田野亲近的时光。那时,爹和娘在打稻子。他在一旁捉青蛙。他将右手手掌铺开,做成弓状,往青蛙身上扑。那一跳一扑的样子,好像自己成了一只大青蛙。有时,他还会将脱了粒的稻草堆当滑梯,滑上一遍又一遍。
等到谷子都打下来了,就要扬谷子。他学着娘的样子发出“呜——兮,呜——兮”的声音,娘说,这是说给风听的话,让它过来,把没用的稻叶啊什么的吹走。
说起娘,可比爹通情达理。
娘老对爹说:“孩子像庄稼,需要经历风和雨。”爹脸一沉说:“读书才是硬道理。生在我们农家,哪个孩子不吃苦?人家城里人从小还吃什么牛奶什么麦片呢。农村的孩子,哪个不是田野的风刮大的?我小时候可苦了,现在又有什么出息!”
爹的话砸在地上,发出咚咚咚的声响。下巴上那颗黑黑的痣,好像在打着节拍。
“明年的七月,你就发榜了。今年的七月,你什么活儿也不要干,一心一意地复习功课。爹和娘都还年轻,有的是力气。”爹的话,像田野的风一阵阵地刮。
暑假一来,就意味着他高三了。八月,学校统一安排补课。七月,在爹眼里,就成了抢成绩的黄金时段。
“城里的孩子没有农活儿,天天在空调房里补课呢。”爹说起这话,好像亏欠了他似的。
他带着爹的期望坐在书桌前。这张书桌,是前年七月爹特意请木匠给他打的。当时花了五个工夫。农村里,一天算一个工夫。工资是按天数来算的。为这张书桌,爹粜了三担谷子。他想着爹汗珠子摔成八瓣的辛苦,就抛却杂念,扑到了题海中。
他和爹的日子,像两条平行的河流,在哗啦啦地朝前奔。
突然有一天,河流断流了。
得到消息,他的魂都吓没了。
他见到爹的时候,爹已经躺在医院了。村里的好心人第一时间将爹送到了医院。娘在一旁不住地淌眼泪。
爹的三轮车在运谷子的时候,栽下了两米多高的路基。爹和车和一车谷子一起倒在了稻田里。
爹一直昏迷。世界突然沦陷了。此时的娘成了一张薄薄的纸,被悲伤整个儿浸湿了。他看看娘,又看看爹,眼睛里漫起了雾气。
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爹了?眼前的爹,像村口那棵老槐树,满身的沧桑。爹是那么的瘦小,好像周围的每一寸空气都在欺负他,让他贴在白白的床上,那么单薄,那么虚弱。他想起爹笑的时候,下巴上的痣好像能飞起来。只要他告诉爹得了好名次,爹就会开心得眼睛里漾出光芒,像冬天的炉火温暖而愉快地跳跃。
他的思绪像春芽在长,眼睛里的雾气越来越浓。他下定决心不能让爹这么操劳了。爹干的活儿,他都要学起来干,而且要和爹一样干得漂亮。
不知过了多久,爹的眼睛突然睁开了,睁得很急,好像能听见上下眼皮迅速扯开时发出的吧嗒声。爹的眼神很准确地落到了他的身上,喉咙里跑出一个声音,虚弱得像风中的水珠,却依然坚定无比:“读书!回家去!凑什么热闹!”爹下巴上那颗痣好像突然变大了,正在扑棱扑棱地生气。
他的泪唰地流了下来。
他知道,爹的心里满满的,装的都是他。
他知道,爹从小没上过学,认识几个字的爷硬说自己可以教他,把钱省下来,可以糊嘴巴。晚上,爷在爹的肚皮上用手指慢慢地写字,教他怎么写怎么念,爹困得不行,有时睡了过去,又被爷摇醒。
爹总说,我的孩子,一定要让他上学堂好好念书,砸锅卖铁,我都愿意。
他不知道,其实,他不是爹的亲生儿子。
当年,娘因为一个误会和爱人分手。是爹,让当时绝望的娘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
此时,他看见娘摩挲着爹松树皮一样的手,目光里满是水一样的温柔与疼惜。
他的心,好像停歇在花瓣上,充满了温暖与感激。
这是一篇体现父爱深情的文章,发表于《教师博览》《百花园》等杂志,文章将父爱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细节中:不让儿子下稻田、给儿子打书桌、即使住院了也赶儿子读书去……一个个细节撑起了厚重的父爱。“爹的眼睛突然睁开了,睁得很急,好像能听见上下眼皮迅速扯开时发出的吧嗒声。爹的眼神很准确地落到了他的身上,喉咙里跑出一个声音,虚弱得像风中的水珠,却依然坚定无比”,这样的文字具体形象,富有直观感、镜头感。
二、在关键处驻足
美学家朱光潜认为,记叙文的叙事部分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而细节就是满架的繁花。细节描写的方法之一就是停下脚步描绘和欣赏那“满架的繁花”。
且让我们先欣赏作家宗璞《紫藤萝瀑布》中的文字: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我在开花!”它们在笑。
“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開,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涨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放似的。
作家停下脚步欣赏美丽的紫藤萝,它们像孩子在嬉戏,在欢笑,在嚷嚷。美丽的画面,美丽的细节,成了描写紫藤萝的经典。我们也需要在关键处停下脚步,描绘出应该呈现的内容。请同学们看以下文章:
豆腐西施
王秋珍
老街腰部站着一棵榕树。树冠呈馒头形,叶茂蔽天,老街的人,喜欢来这儿聚聚。
其实,大伙不仅仅奔着榕树而来。榕树边就是豆腐摊,有一家卖主是西西,长得水水灵灵。那皮肤,像鸡蛋刚剥了壳,像能掐出水的豆腐。那手指,简直就是一棵棵的小葱,看一眼,就知道有多滑嫩。
莫非,是豆腐滋润了她?
其实,西西的工作蛮辛苦的。
头一晚,西西将一颗颗黄豆挑拣清洗再浸到桶里。大清早,当大伙还在梦乡里的时候,西西就起来磨豆。
西西家的小院里,长年放着一个石磨,一块石头压在另一块石头上,上为磨盘,下为磨底。磨盘上有洞穿的一孔,磨底有螺旋的石纹。石磨上,绑着一根光滑得发亮的榆木磨杆。人家是一人添豆一人推磨,西西却能自己添自己推。浸泡过的黄豆一点点进入磨眼,随着磨盘与磨底发出的吱吱声,豆香像长了腿一样四处奔跑。
豆磨好了,西西再把大半锅的水烧开将豆浆全倒入水中烧沸。接着,西西支好豆腐架,放上淘箩,将一块方形的粗纱布,也就是豆腐服,抛在淘箩上,形成一个大网兜。西西将熬好的豆浆一瓢一瓢倒入豆腐服中。伴着哗哗的声音,豆腐服下是纯豆腐,里面就是豆腐渣了。为使它炼得彻底些,西西用夹板夹住豆腐渣,将残留的豆浆挤净。
俗话说:“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点卤是关键的一环。卤水少了,豆腐太嫩,结不成豆腐花;卤水多了,豆腐太老、太硬。西西将纯豆浆倒入锅中,加热之后,就拿铜瓢点盐卤。西西一点点地加卤水,就像在蒸蛋上,用调羹慢慢地加酱油。那专注又带点专业的神情,俨然一幅美丽的版画。慢慢地,豆浆结块了,像云,似雪,如花。水越来越清,豆腐花越聚越多。氤氲在豆腐花的雾气里,西西像电影里的西施一样,脸上泛着羊脂玉的光泽。
最后,西西开始压豆腐。西西将木框摆好,将豆腐服放在木框中,将豆腐花一瓢瓢舀到木框里。舀完了,就将豆腐服的四角翻过来,将豆腐花包住,上面压上砧板、钵头过上几分钟。
西西一天只能做一框豆腐。
老是有男子冲着西西说:“豆腐西施,瞧你那白脸蛋,是豆腐做的吗?”每次,西西都懒得搭理。于是,就有人不高兴了。一天,小三黑拿起一块豆腐说,这豆腐,长成啥疙瘩了啊?还要臭美!
话里有话。西西只当没听见。
不过,有好事者拿来了不远处小苏豆腐摊的豆腐。不比不知道,一比还真有问题。你看人家小苏的豆腐,光滑、白嫩,西西的豆腐呢,表面粗糙,白里带点黄。
小三黑总结道,可怜我们被蒙了这么久。
没过多久,榕树下聚的人少了。不远处老是传来打情骂俏的声音。那个长着一脸雀斑的小苏咧着大嘴巴,开心得雀斑都要飞起来了。
西西不急不徐,一脸榕树般的随和。风吹过,一旁的榕树发出哗哗的声响,不知在为谁唱赞歌。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榕树开花了。小小的花儿躲在小罐子似的花托内。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某个午后,不知谁突然发现,小苏豆腐歇业了。
正在大伙纳闷时,小三黑出现了,他神神叨叨地说,你们知道吗,小苏的豆腐有问题。她的豆腐加的是石膏和甲醛,做出来白嫩嫩还保鲜呢。吃了不仅嗜睡还影响视力。我呀,就是受害者。说完了,他又往榕树方向扫了一眼,轻声道,这回,我可算正义了一回。
此后的每一天,西西的豆腐总是早早就断货了。有人建议她再做一框,她笑笑不语。可那眉眼分明在说,人生就像做豆腐,认认真真才是真。
豆腐西施西西如何推磨、添豆,如何熬豆浆,如何点卤、压豆腐,写得相当细致,这么铺陈,一来给文章增加了知识信息量,二来突出了主人公做豆腐的认真。假如这里不停下脚步,只写西西做豆腐很认真,会削弱后文带来的震撼力,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写文章也需要一张一弛,有时需要快一点的节奏推进情节,有时需要舒缓的节奏,来点看似闲笔的细节描写,使文字在一呼一吸中焕发生命的活力。
三、写出“这一个”
细节描写切忌人云亦云、没有个性。写人要如见其人,写景要如临其境。金庸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每一个都成为经典。因为每一个都是独特的“这一个”。我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发现细节,写下细节。
北岛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他在大学里教散文写作,让大家写写童年,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学生会写细节。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差不多的,或者说是模糊的。这非常可怕。对生活的热爱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你笔下的“这一个”才是弥足珍贵的。我们来看这段文字:
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里面盛满了清澈的水,我喜欢把手无力地搭在水面上,享受那种若有若无的漂浮的感觉。水缸和那时的我一般高,我想要玩水了,就搬一条凳子过来,踩在上面把手伸进水里。要是被外婆看见了就会把我抱下来,说:“那是外婆用来洗菜的水呀,怎么能被你弄脏啦?”我就笑着,把脸埋进外婆那条带着蔬菜清香的围裙里。那时小小的我,喜欢抬起头看着外婆在那个石头砌成的台子上洗衣服,喜欢用手接住滴落下来的肥皂水,或是看着水顺着石头的纹路流到草地上。
——选自学生胡籍文《老屋情结》
把手搭在水面上,享受漂浮的感觉;把脸埋进外婆带着蔬菜清香的围裙里;用手接住外婆洗衣服时滴落下来的肥皂水……这是多么独特的细节呀。它就属于作者胡籍文。这是她童年时的独特体验。你的童年,就没有这类生动又可爱的细节吗?写下来,它就是属于你的“这一个”。
美国新闻学家雷特狄克认为,在人们的心里,蕴藏著各种各样的记忆,如果你能唤起他们心中的这些形象,你的描述就具有了激动人心的力量。我们要写出独特的“这一个”,需要写出人和物的神韵,要赋予描写的对象生命感,写出蕴含其间的精气神,而不能只追求形似。请同学们看看我的学生陈颖的作文:
大红门
泪,抹不去伤痛,却挽留了最初的记忆。——题记
天空,黑色在渐渐蔓延。昏黄的路灯下,昔日的喧闹似乎早已不复存在,小雨稀稀落落。窗户虽关着,我却分明感受到了丝丝凉意。依旧是古城肖像,却找不到昔日的温暖。泪,划破黑夜的痕迹,记忆,却依然清晰。
在如此寂静的夜里,我在思念着你。
记忆里,你蹒跚的背影依旧清晰,你的话语不多,你的笑容却诉说了许多,愉快,悲伤,寂寞,时光似乎被拉長了,回忆渐渐被它抹去了棱角。你慈祥的微笑还是暖在我的心里。可当我再次漫步雨巷,却没有了往日的愉快。
也许再次漫步田野,我还可以寻找你的身躯所在之地——那个小坟包。但是它,已快被时光渐渐踏平。泥土,划过的一瞬间还是没有一点温度。外婆,你是否还记得我,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还有那熟悉的大红门?
小时候,你掌心的温度便是我最留恋的,你大大的手掌握住我小小的手掌,我就好似握住了生命的依赖。还记得那旧得已经掉漆了的红门吗?它不引人注目,却让我的童年十分快乐。还记得那只大大的花斑狗吗?趴在红门前的那只大狗?还有那槐花的芳香?也许你都不记得了,也许你已经释然了。
我最喜欢你拉着我的手,带我去红门。
这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但对那时的我来说是儿时的乐园,因为它一打开便是热闹的集市。我常常拉着外婆去集市上玩。买一串珠珠儿,嚼两颗麦芽糖,拿着糖水棒冰,带着愉快的笑声回家。不知道为什么,红门前总是卧着一只大狗,懒懒地趴着,似乎永远都不会起来。每次路过我都会远远地躲着。外婆说,不用害怕,狗也有自己想守护的东西呢!
“那外公呢?他会不会有自己想守护的东西呢?”年幼的我突然问道。外婆的鼻子红了,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守护的东西啊!我们家颖颖想守护什么呢?”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不说一句话。
后来我就去了另一个城市,对那里的事情一无所知。
直到外婆,你的去世。
我又去了红门。
红门已经不见了,据说已经被拆掉了,留下了记忆残缺的碎片。
那只狗也不见了,据说是被城管打死了,守护再也不存在。
我分明感到,我的眼角湿了。
我的记忆,也被打湿了。
作者撷取红门这个地方,来回忆和外婆相处的点滴。作者小小的手掌被外婆大大的手掌握着,买一串珠珠儿,嚼两颗麦芽糖,拿着糖水棒冰,带着愉快的笑声回家。那只趴在红门前的大狗也是文章很成功的细节。作者还让狗有呼有应,使文字和情感都得到了妥妥的照应。作者的思绪和感情走在逝去的时光里,走在如今已经拆掉的红门里,读来让人有种淡淡的忧伤。这篇文章是陈颖同学七年级时的作文,我们却分明地感觉到她文字的凝重和细节的出彩。
综上所述,只要同学们在细节方面下足功夫,就能给看起来平凡的素材写出动人的一面。
当然,注重细节描写,并非把拉拉杂杂的任何人、事和物都往细致里写,也不是搬用修辞堆砌辞藻,更不是为了凑字数让文章冗长。所有的细节描写都必须为主题服务。任何无益于表现主题的旁逸斜出的描写,不管多么优美、多么细腻,都应果断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