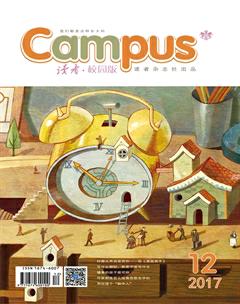听说你的栗色鬈发下落不明
闫晓雨
高考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烫了鬈发,并漂染上一层不那么正宗的栗色。
听说镇上理发店里的理发师都是从北京学成归来的,一时间,那两家理发店做出的发型,蛋卷头、道姑头、梨花烫,齐肩的内扣,外翘式荷叶头,成为每个少女捧在心尖儿上的秘密花园。
我所读的高中是不允许在校学生烫发、染发的,连指甲都要接受检查。学校入口处的宣传栏里,张贴着男女生的各式“标准发型”。每个周六下午都会有老师“组团”随机出击,检查每个班级的不合格发型。
学校的理发室就挨着医务室,几乎每一个被直接剪成“标准发型”的同学出门后都飞奔着逃离大家的视线,去宿舍里一个人静一静。
我没有那样的胆子,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都是留着规整的“三齐头”。青春类小说里,把这种齐耳、齐脖、齐刘海儿的发型叫作“童花头”,听起来很有“气泡感”。但一款发型跟随一个人十余年,就算再喜欢也会腻。那个时候,从学校门口书店借来的小说和漫画里,总能看到女主角长着大眼睛,穿着百褶裙,留着一头柔顺的长发,或直如素尺,或弯如彩带,那才是女孩从纯真走向成熟应该有的样子呀——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去烫个时髦的发型。
说到烫发,还有个有意思的小插曲。
那一年,我的好朋友聂小姐说她想留长发,烫个“大菠萝”。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菠萝表层鳞片密集的样子,有点像电视剧《西游记》里的佛祖,不由感慨她那异于常人的勇气……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人家说的原来是“大波浪”。
我曾经试探着把想烫头发这个心愿婉转表达给我妈,不出意料地遭到了她的强烈反对。在她看来,高中时期的女孩子就应该把心思都放在准备高考上,打扮这种华而不实的事情,只会让我分心。但她转眼看到我落寞的表情,大概又是不忍心泼太多的冷水,索性许下诺言,等高考完,会把自由从头到脚还给我。
是烫成仙女还是炸成妖怪,她都不会再有任何干涉。
在距离高考还有三个月的时候,我总是一边抄写着数学题的公式答案,一边幻想着告别。夏天来得很快,我们收起试卷脱下校服,站在主楼的阳台上,眯起眼睛兴奋而不舍地告别,告别我们最好、也是最丑的时代。
我带着忐忑跑回家里,等着我妈兑现她的承诺。我一直想去同学们常去的理发店烫头发,因为我坚信,只有那里做的头发最适合成人礼。在聽完我急切的诉求后,我妈说:“不就是烫个头发嘛,去哪家不都一样,我带你去张阿姨那里烫吧。”张阿姨是我妈的老朋友了,她的理发店名叫“蓝梦发廊”——一个带着20世纪80年代迷幻色彩的非主流名字。
可惜,这家发廊的生意一直不好,学生们都不太喜欢沉闷的发型师,以及无论做什么发型最终都能做成同一款的老气横秋。
我妈给出两个选择,要么别烫,要么就去张阿姨那里烫。在她的威逼利诱之下,我很没骨气地选择了后者。事实证明,当我看着镜子里那个和韩剧里的“欧巴桑”差不多的发型时,整个人都崩溃了。
高考都没让我崩溃,那个发型竟瞬间让我的世界土崩瓦解。回家的路上,我黑着脸不和母亲说话,她倒先开了口:“你为什么想烫头发?”
我答:“因为烫头发是长大的标志,我不是小孩子了。”
她笑着说:“当你不再佯装大人、不再期望成为大人的时候,就真的长大了。”我承认,此刻坐在这里,怀念起当年那个“三齐头”少女的时候,我认为我妈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