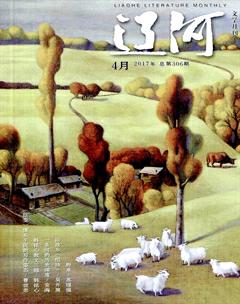八级疯儿
素弦琴
这个名字是口口相传的,估计没有人想过要写出来。我猜正确叫法应该是“八级疯儿”而不是“八级风”,堡子里大小孩儿伢叫起来都是带着儿化音的。这“八级疯儿”不是风,而是我家前街一个疯婆娘的外号。
印象里,她与我家住前后街,是个蓬头垢面的女疯子,我从来没敢仔细瞧过她的模样,连打个照面的勇气也没有。从她家孩子大小推测,她年龄应该在三十多岁。这个“八极疯儿”疯得可是极有特点,就是专门与卖豆腐的过不去。从她攻击的对象上看并没有固定在哪一个人,倒好像是与那细皮嫩肉的大豆腐有着解不开的深仇大恨。每当有卖豆腐的从家门前经过,若是赶巧被这个疯女人一眼瞧见又逃之不及,她就会立刻破马张飞、舞了嚎疯地扑过去,最少把人家一板豆腐给抓得稀烂。久而久之,卖豆腐的就绕着我家那趟街走,渐渐也就不来了。
那是七十年代后期。每到周末,在城里上班的父亲,会在晚霞满天的黄昏,会在我们姐妹眼巴巴的盼望里,蹬着一辆大二八自行车风尘仆仆地从城里赶回与全家团聚。迎接父亲是我童年最有想儿头的一件事。父亲的皮兜像个百宝囊,那些来自城里既解馋又稀罕的小嚼谷儿让我们兄妹几个享受着浓浓的父爱。还有一件美事——就是我们可以借父亲的光每周吃到一次白嫩嫩、滑溜溜、香喷喷的大豆腐。通常母亲会用一个坑坑包包却擦得锃亮的小铝盆儿,盛上半盆圆滚澄黄的豆子,一脸幸福地打发我或姐姐去豆腐房换豆腐。若是赶上正好时候,那大豆腐还冒着腾腾热气,软颤颤的散发着一股令人馋涎欲滴的豆香。豆腐房在生产队旁边,要是不想绕远就得从“八级疯儿”家门前路过。去的时候我通常小心翼翼跑得一溜烟,回来时端着豆腐盆的我是恨不得长出翅膀,嗖一下飞过“八级疯儿”家门前那道坎儿的。记得有一次,眼看就要到家了,竟然一眼看见了八级疯儿,她那蓬松乱发的脑袋刚好从墙头露出来,瞅架势正往门口走,慢几步就能跟她正撞一块儿。我小小的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没留神就被道旁柴火垛探出的一截树枝给绊了个狗呛屎,把好好一块大豆腐都给扣到了连泥带土的小道儿上,身子正哈在上面给压了个稀巴烂。我的眼泪当时哗哗就下来了,心提留到了嗓子眼儿又憋着不敢大声哭,捡起小盆撒腿就往家里跑……从此,那块被摔得稀巴碎的大豆腐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一抹深深的阴影。
那时我还小,只知道“八级疯儿”是个让人害怕的疯子,至于她为什么专门和卖豆腐的过不去,我没想过。“八级疯儿”的家里,有三个和我们兄妹年岁相仿的孩子,他们看起来胆怯而孤单,因为他们的母亲,我们都用看怪物的眼光,像生怕传染了瘟疫一样与他们保持着安全的距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用在“八级疯儿”家不算贴切。可是她家的孩子确实立世很早,在春耕时候也懂得在几个远亲的帮衬下,刚懂事的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妹妹把房前屋后的小园子胡乱种上些茄子、辣椒、黄瓜、地豆儿,虽然伺弄得差强人意,日子也能将就着紧紧巴巴地往前拱。而隔着那些树枝夹成的树障子和矮矮的泥墙,我和姐姐常常一边在房前玩游戏一边听妈喊着“快麻溜进屋把饭吃了再玩儿!一会该凉了!”不知道從何时开始,我们在家里吃饭到尾声时,时不时会有人笑着整一句“一二!加进去!不给你爸留!”然后散开一片快乐的笑声。据说这也是口口相传的段子,半梦半醒的“八级疯儿”和她的孩子们吃饭时经常会喊这句口号。
时光荏苒,一晃从乡下搬到城里已近三十年,每日为了生活忙得颠颠倒倒,总是少有机会回乡下去看看。其实路程倒是真不算远,关于故乡的记忆却已渐渐远了也渐渐淡了。
周末休息去看老妈。年已八十的母亲神清气爽,老太太给我们蒸了一屉南瓜,说是舅舅从乡下特意给捎来的老品种。南瓜甜甜面面,入口即化,佐着一卤盐的小咸黄瓜拌上香香的辣椒油,吃得那真叫一个倍儿爽。屉上还剩下最后一块的时候,大家开始推让,姐姐突然说“老三,你咋吃不胖,一二!加进去!”听着这久违的口号,突然,心照不宣的笑声就在这冬日暖暖的屋子里绽放开来,慈祥的老妈也跟着呵呵地笑,感慨“这八级疯儿应该早就没有了吧?真是一个苦命的人唉……”
孩子听得摸不着头脑,睁着好奇的大眼睛非得缠着姥姥给讲讲“八级疯儿”是怎么回事。伴随着母亲的回忆,我们走进了一段令人心酸的陈年旧事。
“八级疯儿”来自苏杭,年轻时是个一等一的江南美女。皮肤白晳,鹅蛋脸,不描眉擦粉儿也比画片儿上的明星还美。说话不多慢条斯理,性子有点倔强。当初为了憧憬中的美好爱情,不顾爹妈的强烈反对,在小布包里就装了一身换洗衣裳,死心踏地跟着那个会预算会画图的工程师,踏过千山万水来到了东北这穷乡僻壤安了家。这美女媳妇估计是指望千里迢迢嫁个吃皇粮有技术的如意郎,就算不吃香喝辣,也能被当个宝贝掌心里宠着,衣食无忧。可万万没想到红颜薄命,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这工程师竟不可思议地变成了个败家老爷们儿,说是在城里迷上了耍钱。拿回的家用是越来越少,只要回来还把自己家的东西不停地往外倒腾。小媳妇生下第三个丫头片子的时候,男人带信说太忙没空回来。小媳妇心里像被猫掏了一样,她怀念着那烟雨江南画一样的故乡,可是那里的娘家人老早就断了消息,当初她一意孤行跟着男人跑出来,恨恨的老父亲是放了“就当没养过你!”这个狠话的。孤立无援的小媳妇咬紧牙关,从坐月子第二天就开始自己下地做饭、洗衣服。。。
男人昔日的好儿和甜蜜的承诺,一想起来还会叫人脸颊上升起幸福的红云呢,那些指天指地发过的誓总不成是假的吧?男人不会是变了心成了挨千刀的陈世美吧?小媳妇心里见天乱糟糟的,干着活儿往往就走了神儿。看着三个幼小的孩子,这小三子啥时候才能离手啊?真应该去城里看看,当家汉子一走就没了影子,他到底是在忙什么?不会是出了为难招灾的啥事情吧?可日子还得捱着往前过,她不得不背柴火拾茬子地挑起了生活重担。听说她当姑娘时在娘家可是被娇惯着呢,哪里遭过这些样罪哦!她的风华也就渐渐磨损了,那水灵劲看起来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忽然有那么一天,有从城里回来的好事乡亲,不小心给说吐噜了嘴,寄托了小媳妇无限希望的当家汉子,竟然在她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就和一个卖豆腐的女人好上了。其实这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村里有不少人见过那个“豆腐西施”,都说那个娘们儿长得模样一般,脸上还有疙瘩,但是打扮风骚,眼睛像钩子,一张巧嘴可会说话儿呢,不吃饭能送人十里地。小媳妇当时就眼睛发直,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起来安排吃喝,嘱咐大孩子带好小孩子,然后一个人去了城里。两天后失魂落魄地回来了,水灵灵的大眼睛哭得红肿不像样子,衣服上脏兮兮一块一块还烂了俩三角口子,布片耷拉着像一大一小两张呐喊的嘴,不吃不喝不说话直着眼睛流泪在炕上死了一样的躺着。
那个春天,村子里经常刮起脏兮兮的大烟风,有经验的老人说大风最少能有八极。三个孩子守灵一样围着妈连哭带喊,最小的孩子扒在她身上咿咿呀呀饿得直哭,有两次小媳妇暴躁起来推搡那还屁不懂的小三子,孩子吓得哇哇哭着差点骨碌到炕下边去。后来,小媳妇终于喝了米汤下了炕,但是从此以后,眼睛总是直勾勾的,也很少梳洗,一阵糊涂一阵儿明白,看到卖豆腐的就会没命地往上冲,连挠再抓。
又有几年没见到“八级疯儿”了,那个曾经水灵灵的江南女子,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