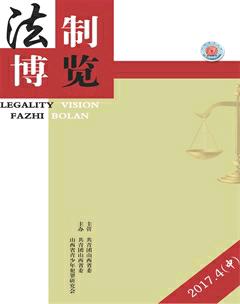论煤矿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
摘要:随着时代变迁,采矿权转让制度已呈现出它的弊端,由此产生的纠纷也日益增多。在“于某等人诉董某等人采矿权纠纷”一案中,当事人在对煤矿转让的标的物认定上产生了争议。从合同解释理论和事实来看该协议应认定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并非个人合伙份额转让合同。在效力认定上,首先,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办法》规定,案件中该采矿权转让合同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再则,当事人双方不符合采矿权转让的资质条件,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该采矿权转让合同应认定无效。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支付的转让款。
关键词:采矿权;合伙份额;转让
中图分类号:D922.32;D9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11-0106-02
作者简介:胡永丹(1993-),女,汉族,四川万源人,西南科技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民商。
一、案件简介与争议焦点
(一)基本案情
2010年5月1日,原告于某等三人与被告董某等三人签订了煤矿转让协议,约定将被告开办的关田坝煤矿北翼655煤井的资源及资产以220万元转让给三原告①。三原告经营该煤井自负盈亏。同日,于某作为三原告的代表与关田坝煤矿签订了入股协议,成为其合伙人。原告向被告三人支付款项后,投入资金对该煤井进行改造。在改造期间得知该煤井早已确定为后期利用井口,严禁生产经营。井口被整改后,由原告方经营直到该井口在2012年被确定为非法井口被永久性关闭。原告方受让煤井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为此于某三人以被告以欺诈方式与其签订合同且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返还价款赔偿损失。
(二)案件争议焦点
一审认定该案件是一件采矿权纠纷案件。支持原告合同无效返还价款的请求。但原告方也存在过错应当为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审认定该案件是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支持了上诉人即原审被告的请求,该协议有效,撤销原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案件结果千差万别,原因在于对该转让协议转让标的物的确认,是采矿权还是合伙份额?
二、案件评析
(一)该协议不应认定为合伙份额转让协议
1.合同不应解释为合伙份额转让合同
二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为有效的合伙份额转让合同。笔者认为从案件事实以及法律上分析该案件不应认定为合伙份额的转让。从合同目的因素来看,当事人目的在于转让采矿权。从文义因素来看,协议载明将煤井转让给原告,真实意思不明。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当文义解释的结果与当事人意志不符时,应舍文义取目的,结合证据来看,转让的是采矿权而非个人合伙份额。
2.原告未成为企业的合伙人
本案关田坝煤矿是一个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的本质在于“人合性”,因此法律上最大保障合伙人的自治,如转让合伙企业的财产、接收新的合伙人入伙等事项上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才发生效力②。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受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受让人成为企业的合伙人,从而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资格③。然而原告方与第三人签订了《入股协议》后,第三人并没有收到原告方的转让款,而是原告以655煤井的资源和资产估价220万元入股,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对于该煤井享有所有权。原告在接受煤井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其进行改造,在经营的煤井处于亏损而关田坝煤矿处于盈利的情况下,原告也从未参与关田坝煤矿的分红与管理。可见原告并未成为合伙人,更没有享受到合伙人的权利。
综上所诉,笔者认为二审判决缺少证据支撑,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同时撤销原审法院的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使过错较小的一方承担了全部的损失,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公正的精神,因此笔者不赞同二审法院的判决。
(二)该涉案协议为采矿权转让协议
从合同的解释理论来看,该合同应为采矿权转让合同。2004年,三被告经营的655煤井被整合到第三人关田坝煤矿中,成为关田坝煤矿的合伙人之一,该煤井一直由三被告开采经营、自负盈亏。事实上关田坝煤矿的生产系统主井、南翼和北翼分别由不同的合伙人独立开采经营、自负盈亏,但矿业权登记在合伙企业名下。对于转让采矿权的主体为合伙企业时,法律法规对此作了两种情况的划分,一种情形是在认定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标的物前,首先要明確采矿权的所有权人,是属于合伙企业还是属于合伙人。如果是在合伙企业取得采矿权后转让作为合伙企业财产的采矿权的,那么可以明确确定该合同是采矿权转让合同。通过对本案的分析,采矿权是合伙企业的合伙财产,因此该合同应为采矿权转让合同。原告于某作为代表与第三人签订入股协议以资源作价220万元入股合伙企业,证明入股前该资源已经属于原告,同时没有以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和参与分红。结合一系列证据和法律分析,可以看出该协议实为一份采矿权转让协议。
(三)该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
本文认为采矿权是一种受公法调整较多的用益物权,在此基础上,采矿权的取得、转让、抵押须遵循用益物权的特性这一原则④。因此本案中的转让合同除符合物权法对其的相关规定外,同时也要符合《矿产资源法》等相关法律法其规所作的规定。就本案而言,该采矿权转让合同从以下方面分析,该合同不符合合同生效的要件,该合同无效。
1.本案采矿权主体不符合法定转让条件
作为一种受公法限制较多的用益物权,采矿权关系社会的各个方面,国家对于它的流转管理严格,设置了限制条件。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的主体条件均不符合法定的转让条件。就被告而言,转让方须满足《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的前置性条件,在本案中,矿业权登记在关田坝煤矿合伙企业的名下,采矿权属无争议,被告只是合伙人之一,并不享有采矿权,没有转让采矿权的资格。另一方面,采矿权的受让人同样要具备《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前置性条件。而原告系自然人,不符合法定的矿业权转让受让人的资质条件及安全生产条件。因此该合同当事人双方均不符合转让采矿权的主体条件,违反了《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七条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采矿权转让双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条件,因此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转让合同符合无效合同的规定,应属无效的合同。
2.该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规定,采矿权转让须经过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案涉的煤矿转让协议从成立到案件起诉之日止,一直未向主管部门申请批准,该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然而对于未经批准的采矿权合同的效力认定,学者们对这一看法不一。在司法活动中,不同法院对于该类合同的效力认定也不一,综合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对此规定的观点,本文认为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对于无效合同的规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何为强制性规定?一般认为,强制性规定包括两种: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有关法律解释指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该如何在具体司法实务中判断该规范为效力规范,有学者认为,若该规定明确载明违反该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那么此类规定确定无疑是效力规范。除此以外,这一类的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违反此规定会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继续履行会对公共利益产生损害的,法律上也应将该规定划定到效力规范中。对此笔者表示赞同,违反了效力性规范后,私法上会否认该法律行为的效力,表现为合同无效的情形。而违反管理性规范的后果后,公法上会对该法律行为进行制裁,并不一定导致合同无效⑤。《矿产资源法》等法律的立法目的来看,设立批准程序是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因此该规定属于第二类的效力性规定。因此案涉未经批准的采矿权转让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无效。再则,本合同系采矿权的部分转让,《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采矿权部分转让,该规定是效力性规定。该合同将采矿权进行部分转让,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合同无效。
3.该合同为规避法律的合同
该双方签订的名为煤矿转让协议、实为采矿权转讓合同。合同协议中的条款内容理解分歧较大,表面上该合同是一份转让合伙份额的协议。事实上,原告于某、朱某、柳某和事后入伙的陈某并未以合伙人参与企业的管理,也未参与分红。关田坝煤矿的生产系统事实上被分割成三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部分,主井部分由第三人经营,剩余部分由不同的人经营,存在将采矿权非法出租的现象。所以,该协议以合法的形式非法转让国家的矿产资源,掩盖了将采矿权分割的非法情形。在签订转让协议时,也未将该井口属于关闭井口这一重大事实告知原告,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在原告方经营煤井期间发生过几起矿难事故,因此合同的继续履行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将国家资源非法转让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因此该采矿权转让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应属无效。
综上所诉,该采矿权转让合同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合同自始不发生任何效力,当事人一方由此获得的利益应当予以返还。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的转让款适用法律正确。同时,原告明知不符合采矿权受让人资质条件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过错原则原告的赔偿损失之诉不予支持。综上所诉,笔者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注释]
①(2015)年达中民终字第362号.
②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02.
③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09.
④李显冬.中国矿业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66.
⑤白莉,江钦辉.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研究[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2(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