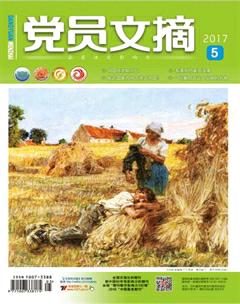中国经济的出路在改革和创新
周其仁
低廉的制造成本和明显的比较优势,助力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下谱写了“中国故事”。但如今,印度、越南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便宜,欧美的科技比中国更发达。在外需萎缩、经济下行的环境下,怎样寻找中国经济的突围之道?
外需萎缩
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但偏偏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更大。
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增长的原因,要先理解全球格局。
打个比方,从前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有10万元资本,300人。穷国有10元资本,3000人。前者类比欧美和日本,后者类比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体中间由一道蓝墙隔开,穷国没资本,经济进步缓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拉大。
后来,改革开放把那道蓝墙打通了,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001万,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增加了10块钱,但是却多了3000人来抢,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的麻烦是,劳动者从300人变为3300人,劳动者的竞争也加强了。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两极分化严重。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制造业蓝领工人、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超过了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中国的产品相对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现在的全球格局,发达国家GDP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中国在提高。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升到现在的8000美元,深圳更是达到25000美元。反观美国,从1978年的13500美元升到现在,也才5万美元。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得大家优势趋同了。
如今,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开始发生作用了,比如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制造紧张的国际局势。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但偏偏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更大。
成本优势减弱
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的产品,成本低要价就低。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变化。
让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但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有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先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需要组织,而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而有了体制改革,才有后面环环相扣的故事。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2002年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后来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主要是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现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没有什么大帽子,但小绳索挺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就大了。高速增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摩擦的力量就凸显出来了。
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就必须降低体制成本,同时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
那么,如何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和创新。
想赢得竞争,要么成本比对手低,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产品。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地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就必须降低体制成本。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下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所以,中国要继续改革突围。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即使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因为,人均GDP从200美元到8000美元,再到几万美元,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
如果一家企业的人工费居高不下,而它却还一直生产低附加值的商品,那它的投入产出比一定高不起来。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另一個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引进新产品,改变现有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立它们的研发中心,它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而中国,也必须如此。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摘自《商界》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