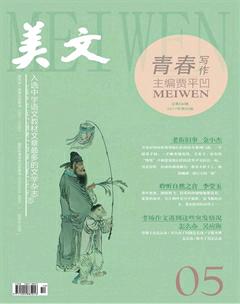老街旧事
金小杰 女,1992年生于山东青岛,菏泽市作协会员,菏泽市青年作协理事及签约作家。曾参加“2016《中国诗歌》·新发现”夏令营,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时代文学》《诗选刊》等。
一
马兰村没有马兰。
马兰花遍地的时候是在六百年前,当时荒地还只是荒地,远远近近方圆几十里都见不到炊烟。直到第一户金姓人家挑着担子移民至此,马兰村的故事才得以开始;而我,就是众多子孙中的一个。
上溯七辈,我的太太太太太爷爷就住在这临街的三进大院里。家门口是当时顶繁荣的一条商业街,有布店、粮油店、小饭馆、药店、祠堂、马车店和寿衣店。一进门洞,东壁邻着的三间临街房留给自家开了一个小饭馆,门洞西壁的两间房则租给刘姓的赤脚医生开了间药店。向阳的土坯墙上开着五个亮堂堂的棱格木头前窗,头顶则是一律的青檐瓦当。西邻祠堂,屋脊上还坐着几个青瓦烧制的狮子辟邪,每当下雨的时候,太太太太太爷爷都会担心它们引下雷来。
布店的生意是极其惨淡的,这里的家家户户都会种棉纺线。月光好的时候婆婆媳妇们把纺车搬到门前,一手摇着手柄,一手顺着棉花线。月光下,纺车的“嗡嗡”声和婆婆媳妇们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煞是好听。纺成的棉线顺在一根木头转子上,渐渐缠成一枚巨大的“茧”。棉花纺完了,日子过得穷一点儿的人家便会带两三个这样的“茧”,拜托家里有织布机的亲戚把棉线织成棉布。过年的时候,家里五六个孩子的新衣服全都要从这块小布上出,但布店并没有因此而倒闭。
布店主营棉纱绣花。被面大的原色棉纱用一个四四方方的木头架子绷紧,四个媳妇围坐在周围,举着一根小巧的绣花针,针脚翻飞,在那用做帐子的棉纱上绣凤凰、孔雀、大开的牡丹。绣完一副帐子大概要七八天,完工后送回布店,然后再领取新的花样和帐面。一副帐面的工钱也不过几个铜板,当地人都喊她们“穷绣娘”。过个把月,布店就会把收来的绣花帐面送到城里的店面出售,这些穷绣娘们绣的帐面就会陆陆续续出现在大户小姐或小少爷的卧室里。
二
房子邻着马车店不远。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西侧是一溜马厩牛棚,里面养着十来匹马并着两头一老一少的骡子,院子北侧和东侧是两溜儿平房,赶大车的车把式就住在那里面。
马车店是村里的生命线,冬天拉煤,夏天的时候捎卖蔬菜,平日里还兼送书信。赶车的里面有个叫老赵头的,是个脾气犟不服输的主。那年夏天几个人坐在马车店前的磨盘上乘凉,几个人说着说着就打起了赌。有个车把式说,咱院里的“大红眼睛”脾气烈没人能驯得了。老赵头听了一拍大腿,说:“咱们赌十个袁大头,我能驯得了那个鳖孙。”消息传了出去,有人说老赵头能赌得赢,有人说老赵头赌不赢。
打赌的那一天,马车店里的小学徒牵出“大红眼睛”。这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一面喷着响鼻,一面“哒哒”地跺着前蹄,警告着不相熟的人。老赵头趾高气昂,一边走一边同人群中的熟人打招呼:“哎哟,您也来了!”“您今天可看好吧。”“肯定赢!放心”……
赌场设在村外的打麦场,看热闹的沿着南北小路一字排开。老赵头接过缰绳,“大红眼睛”歪着头打了一个响鼻。这匹大眼睛的枣红马虽然拉过车,但脾气烈得从来不让人上身。车把式们也都知道它的脾气,平时传个口信也都挑其它几匹。
老赵头先拉低缰绳,用手拍了拍它的脖颈,随后又搔了搔它的鬃毛,摆弄了大概半袋烟的功夫,趁“大红眼睛”不注意,一个利落的飞身上马稳稳地落在了马背上。“大红眼睛”受了惊,扬起前蹄冲进了庄稼地。见沟越沟,见坡上坡,马背上颠得紧,老赵头把身子压得很低,但这样还是被“大红眼睛”甩下来了十多次。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个鳖孙。”老赵头咬着牙根上马、落马,反反复复。“大红眼睛”撒开马蹄使劲跑,跑得一身枣红色的皮毛泛着水光。老赵头的破布小褂早就被树枝刮破,鞋子也跑掉了一只,但他伏在马背上,两条腿仍然紧紧夹住马背。折腾了三四个时辰,“大红眼睛”的步子明显慢了下来,两个鼻孔“呼呼”地喘着粗气。老赵头扯了扯缰绳,让“大红眼睛”由飞蹿变成慢跑。
“成了!”人群一阵骚动。老赵头骑着“大红眼睛”晃晃悠悠地朝人群跑来,仿佛是一个英雄。在离人群十步远的地方,老赵头翻身下马,脚一落地腿一哆嗦差点儿趴倒在地上,眼活的小学徒跑上去接过“大红眼睛”的缰绳。老赵头深一脚浅一脚,一直走到人堆里,在一个人的面前伸出了一只手:“俺赢了,给俺十个袁大头。”
賭赢了的老赵头鼻青脸肿,“大红眼睛”也没好到哪去,一身湿漉漉的皮毛仿佛刚从河底打捞起来。虽然被驯服了,但它只让老赵头骑,其他人仍近不了身。
三
我家西邻祠堂。祠堂前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院子中间有个烧香的大鼎。往前走是八根合抱粗的红漆木柱,柱子后面藏着十几扇高大的雕花木门。院子东侧是一溜儿客房,客房里的桌椅板凳齐全,比一般的住家条件还要好些。西侧的屋子里则住着守祠人的家眷,夏天门上挂着竹帘,冬天挂着棉帘。村里人都喊这个守祠人叫老金。
一进冬月,祠堂里就热闹起来,老金也开始准备过年上供的祭品。先预定这家的猪头,那家大红冠子的公鸡,然后去马车店托几个车把式捎回几条新鲜的大鲤鱼。除夕当天,老金的媳妇早早把祭品刷洗一遍,整整齐齐摆在案上。最惹眼的就是那只洗得花白端放在长案正中间的猪头,肥头大耳,一看就是养得足年的大肉猪。
除夕是老金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太阳一落山,老金把牌位前的长明灯点亮,端着饭碗靠着祠堂的木门胡乱扒拉两口。大殿是一时半会儿也不能离开的,一是怕风把长明灯刮灭,二是防止那些嘴馋的孩子把供奉的糖果瓜子偷走。半夜,村里迎财神的鞭炮声响过后,祠堂这边的鞭炮声开始。一家兄弟几个在老太爷的带领下摸黑往祠堂赶,没成家的提着烧纸和鞭炮,成了家的左手拉着困得站不稳的大儿子,右手抱着早已睡过去的小儿子,步履匆匆地想要去祠堂上第一炷香。隔着祠堂还有一段距离,就能听见“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今年又让人抢了先,明年要早来!”老太爷一定会这么说。
午夜十二点过,祠堂前挤满了人。两根长竹子做成的放鞭竿子根本腾不出空,这边的鞭炮才刚刚点燃,那边的竿子又挂上一串新的。放完鞭炮的用手掸掸衣服,乐滋滋地跨进大门,没放的挤在门边等着竿子腾空。院里烧香的大鼎前摆着一个盛馒头用的大圆簸箕,权且充当香火柜。入了门的人自觉站成左右两排,走到大圆簸箕前往里扔钱,有碎银,有铜板,还有袁大头。天亮的时候,簸箕里的钱都盛不下,一个劲地往外淌。放完鞭炮,扔完银子,上完香,按照左进右出的规则,这才依次跪倒在祖宗的灵前磕三个响头,求祖宗保佑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家和人兴。拜祠堂到这里才算是暂告一段落。
四
东邻居建房的时候屋檐探进我家院子一尺,于是我家的屋檐被挤得探进祠堂的院子一尺。
这一年祠堂大修土木,先后找来五六个风水先生。这些风水先生端着罗盘在祠堂转了一圈,然后无一例外地指着我家屋檐,说要把这里修平,不能探进来,也不能凹进去。村里的几位长辈犯了难:地契上清清白白地写着,这一小块土地归我太爷爷所有。
老金提着点心盒子找到我太爷爷,两人坐在我家一进院的葡萄架下你来我往说了大半个时辰。太爷爷觉得房子和院子是祖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业,不能因为族里大修祠堂就损了自家的利益。老金无奈,撂下一句“等我们回去再商量”,走了。
隔了大半个月,族里的长辈和老金一起挤进我家院子。一位长辈指着我家凸过去的屋檐说:“我们回去商量了,这一尺见方的地我们决定用钱堆过来。”“堆过来?”太爷爷有些迷糊。老金一拍桌子说:“这你还没听明白吗?这一尺的地用一吊吊的铜钱往上堆,屋檐有多高,钱就堆多高。这买卖下来你可赚了,这地儿少说也能堆一千吊。”太爷爷用食指反扣着桌面,梆、梆、梆……“你们让我想一下,这毕竟是祖传的宅基地。”“好,给你三天时间,我们先回去筹钱。”
用钱堆屋檐的消息不胫而走,都说我家发了财。这三天,太爷爷茶饭不思,深更半夜披着衣服爬起来,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块屋檐又是叹气又是摇头。祠堂里的人这几天也没闲着,他们搬出钱柜,把成柜的铜板倒进大圆簸箕里,“哗哗哗”全是铜板碰击的声音。他们坐在周围,夜以继日地数钱,一枚枚铜钱被穿在麻绳上,铜钱与铜钱撞击发出脆响。太爷爷三天没睡,隔壁客房数铜钱的声音也响了三天。
第三天早晨,鸡才叫了头遍,老金他们就开始叫门。太爷爷披着衣服开门,被门外黑压压的人群吓了一跳。所有人都想看钱堆屋檐的壮举。老金他们站在人群前面,最前面是并排放着的四辆手推车。每个手推车上都捆着两个大长编篓,编篓里堆满一串串的铜钱。
“想好了没?钱都给你带来了。”有人开始催。太爷爷在四辆车前走了两圈,鞋底同地面摩擦的声音格外清晰,终于开了口:“这地,不能卖!我不能让子孙后代戳着脊梁骨说我变卖家产!”人群瞬间骚乱起来,太爷爷面朝外做了一个长揖,“各位,多有得罪。”屋檐虽然没有卖,但金家屋檐用钱堆的说法却在村里经久流传。
后来,这条街上的布店、药店、祠堂、小饭店都陆续消失了,最后消失的是馬车店和粮油店。整条街都荒凉下来。人民公社的时候,在粮油店的旧址上又开起一家农村合作供销社。供销社里的东西少,只有生活必备的烟酒糖醋,偶尔有油纸包的青岛饼干,那是唯一的点心。扛着锄头去地里上下工的农民从门前经过,透过两扇破破烂烂的木门,可以看见柜台后的“公家人”嗑着瓜子聊着天,即使这会儿有人上门买东西,也不一定答理你。全村唯一的公社小饭店,也远远地搬到了另一条街上。
再后来,父亲谋了另一块宅基地,在宅基地上建起一座红砖大瓦的新房,我们全家终于搬离祖祖辈辈生活了七八代的老房子,也告别了曾经熙熙攘攘如今荒草三尺的老街。搬去新居不久,父亲就以六百元的价格将临街的两进院子卖给了一个外乡人,三进院子则留给了大伯。现如今,钱堆屋檐的故事也鲜有人知,老街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也渐渐模糊,全族拜祠的场景也早已作古,只剩下野草,只剩下这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的野草,长在曾经的布店、粮店、药店里,长在祠堂曾经的大殿里,长在人睡过的冬日里暖烘烘的坑头上,长进人的记忆,记忆里荒草萋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