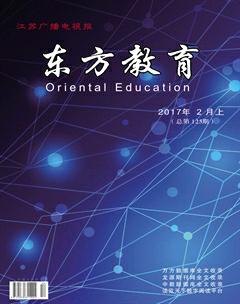浅析文学翻译中的人、诗与社会
边航+杨帆+Altergul
(1.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金华;2.浙江师范大学 初阳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3.汤溪高级中学 浙江金华 321000)
摘要:借助索绪尔“语言结构”的逻辑,将文学作品《春晓》的社会背景,即隐居扬名;以及作品反应的人性进行解析,为译者提供了新的翻译思路。
关键词:语言结构;文学;翻译
十九世纪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出版著作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指出语言学应当是一门共时研究,其主要研究对象为语言结构,至此为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索绪尔的贡献之一在于,他从众多资料中归纳出了一个科学框架。有价值的研究依赖于清晰的研究框架,即研究对象彼此之间泾渭分明的关系,这一点对文学翻译批评鉴赏研究是同样适用的。
一、社会
(一)《春晓》中的社会背景
“孟浩然一生都在仕与隐之间矛盾挣扎”,《春晓》作于诗人隐居鹿门山之时,“这一阶段……一方面醉心山林,一方面希望通过隐居扬名,走荐举的路子入仕。”(李嫣然,2014:4)
上述的背景知识,若用来理解诗人性格,则是再合适不过的史料。孟浩然隐居的事实让我们无视时空的阻隔,对诗人的惆怅郁闷产生了一丝同情。这份同情超越了个人的主观情感,是隐含在文学作品里的客观人性,而人性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是最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如果有人利用上述的背景知识而轻率地下了判断,认为正是因为官场失意,诗人才得以写出《春晓》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诗,否则这首诗的灵感就将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事实上他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就是错把政治事件当成文学创作,拿政治事件背后的历史必然性来解释所有文学的价值。郑振铎在《文学大纲》的序言里说到:“所以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我们如有了空间的或时间的隔限,那末我们将自绝于最弘富的文学的宝库了。”(郑振铎,1986:2)读文学不应有时空上的隔限,更不该有社会政治上的隔限。单凭政治背景来推测人物性格,这在考场应试中是常见的、合理的,但在真正的翻译批评与鉴赏里却成了抹杀灵感最锋利的匕首。因为这否定了文学创作中人的自由,把人当作社会机器里的一环,從而推导出一个看似无可否认的结论,那就是任何文学都不过是政治的反应。这显然是个谬误。
二、诗
(一)《春晓》原文赏析
1. 词语赏析
有人认为诗作里“不觉”一词用得妙,一来表现诗人清晨醒来的自然之态,二来侧面烘托春天自然之意。解析十分精彩,可难逃过分主观之嫌。诘难者会问:“‘不觉一词何来烘托春意之故?子非鱼,又焉知诗人睡醒乃一番自然之态?”面对如此诘问,我们一面苦笑于发问者之于文学大门而不能入,一面却也为之惊醒而意识到,任何文学上的解析似乎都难逃主观之嫌。真正的问题在于,主观意识因人而异,不同的知识背景、相距甚远的人生阅历都能在最后导致千差万别的理解。因此,纯粹的主观分析只能做赏玩之用,于师生间交流而体悟文学之美,于友朋间畅谈而领会词句之妙,却不可作严肃的文学研究之用。
严肃的文学研究应当于主观之外见客观,由个别现象总结成普遍经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国维,2013:6-7)先生不拘泥于词语本义,跳脱出来,看见了意境。何为“意境”?先生说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敝见认为,境界就在一个“真”字,而所谓的“真景物、真感情”就是上文提到的“人性”。
对于同一个“闹”字,钱钟书在《七缀集》的《通感》一文里作了别样的赏析。先生写到:“……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是‘通感(synaesthesia)或‘感觉挪移的例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钱钟书,2013:64-65)
王钱二人的赏析有一共性,即均摆脱了单个词语的情感与意义,前者探寻迷蒙的哲思,后者发现客观的感官联系。看似不在讲“人”,实则处处讲“人”,但讲得是“人性”,或者说“真人”。
2. 语句赏析
语句赏析有着很大的难度,难度在于语句不是单个词语的堆砌,好似两个人组建了家庭,家庭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夫妻二人的居所,而被赋予了更多道德上、哲学上的意义。对于这隐含在词语间的联系所能带给人的感觉,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有过评述:“……我们完全可以用普通而精准的语言来描述普通的事情……纳博科夫(Nabokov)就有这样的本事,用一段看似无关痛痒的对话,让你读后脊背发凉,并感受到艺术上的享受……”。
以下摘录的句子望能给予上文更好的佐证:
We started back to her house I was going to spend the night. We had the whole day to look forward to. We had plenty of candy.(何兆熊,张春柏,2013:59)
本文题目为Fun, Oh Boy. Fun. You Could Die from It,作者意在说明快乐同任何情绪一样,是种稀缺的、可遇不可求的情感。摘录的四句话,措辞平实、句式简单,却道出了身为孩童最无忧无虑的时刻。语句之所以精彩,来自词与词、词与句以及句与句之间的有机联系,而翻译最要紧的就是保留下这层联系。
(二)诗的意义
作品在完成的一瞬间起就不再属于作者,而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这句话是十分公允的,其意义不仅在于保证了原文可以存在千万种解读方式,而非仅限于作者创作时的意图,更在于清楚地划出“作品”与“人”的界限,即“作品是作品,人是人”。王国维曾钟情于文学,到后来却哀叹道文学不过是一场空,从而走入了最为现实的史学研究。我不敢对先生的决定作任何臆断,只能揣测,也许是先生没能把作品和人分清。因为所有作品都是人创的,从一开始它的性质就是虚构,无论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虚假的。但是,包含在作品里,同作品实则分离的“人性”,却是真实存在的。
参考文献:
[1]F.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王德峰.哲学导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6-7
[4]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13:64-65
[5]郑振铎.文学大纲[M].上海:上海书店,1986:2
[6]何兆熊,张春柏.综合教程3[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