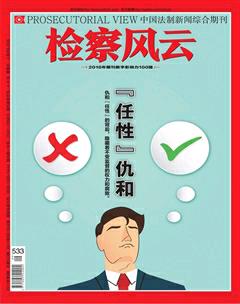题茗随记
吴秉衡
旧时,厌倦了古文、八股、馆阁体的读书人大多好读上篇儿“子不语”,把玩个儿案头清供,同时也乐得做点子有趣、显学问的消遣。这些年来被新闻媒体津津乐道的“京城大玩家”——王世襄老先生即是旧日读書人的最后一缕清芬。
早已登仙的王老爷子当年不经意流露出来的米癫遗风,通过一些个儿旁人撰写的“深情回忆”“沉痛缅怀”之类的长文,借着“俪松居”旧物拍卖火爆行情的东风,着实令不少被物欲闹得六神不宁的当代精英耳目一新,生出如同在由朝阳群众24小时把守的某座筒子楼下,邂逅到一位操着纯正铁岭口音的仁波切那般的兴奋。
毕竟,单论古董级竹雕、铜炉、佛像、明式家具时下的价位,可真是贼贵、死贵。在那些个鲜衣怒马的精英眼中,它们是艺术品,是收藏品,是秀品味的奢侈品,更是回报可观的投资品——唯独不是王老先生终生挚爱的玩物儿。
作为一名靠单位每月“铁杆庄稼”度日的凡人,精英的桂冠暂时落不到在下头顶上,所以我纵有一份对旧日书生雅癖的向往,也是真真切切玩不起新时代里精英的新爱好,所以只得效仿“一休哥”手指轻揉天灵盖,绞绞脑汁,另寻出路。
说来也巧,我十年前充任“书店巡检史”时,曾购进本由一对璧人合著的休闲读物——《喝遍好茶》。这本书,自己从头到尾读过两三遍,也曾感慨过“遍喝好茶”的幸福。然而,十许年前要找齐书中提到的那些名茶着实不容易。直到近几年电商大兴,这才终遂己愿。
喉吻既润,我不免起了“搜枯肠”的念头。虽然不才没有“文字五千卷”的积淀,但自忖中学时打下的文言文底子尚未消磨光,故而拿起铅笔在《喝遍好茶》上题下了品茗的体会:
熙春者,出越州。入汤后,其嗅兰,色清亮,味甘绵柔。甚耐泡。
蒙顶甘露,滋味胜过洞庭碧螺春一筹。忌用沸汤沏之。配以小壶、小杯,最妙!
雨花茶者,得名自金陵雨花台。今,江浦、六合等处亦引种,浴汤稍久,有栀子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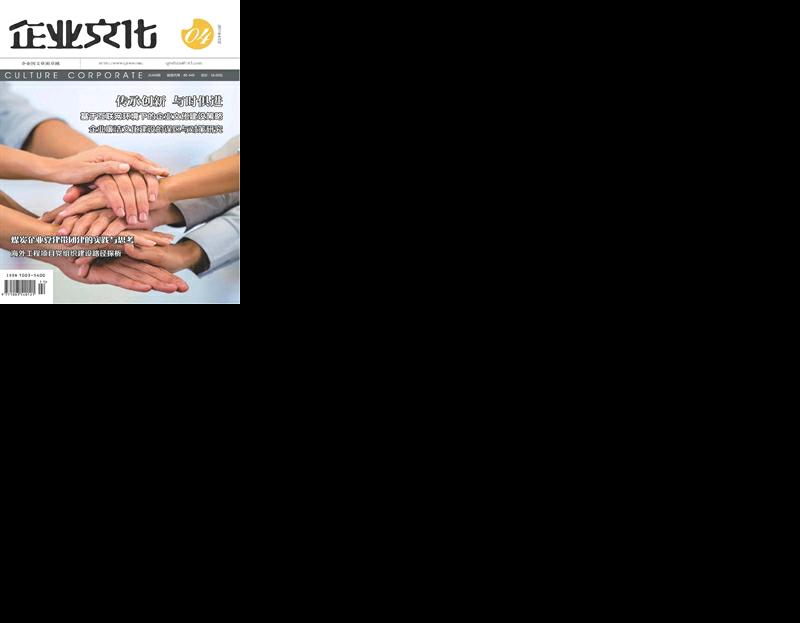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留给那本书的独白渐渐多了起来,附带着也成就了些许谈资。有一回午休,我和底楼办公室的两位前辈谈到了饮茶,分享了各自寻觅佳茗的经历,说起了对每一款茶的感受和体悟。聊到兴浓处,其中一位前辈从身旁的低柜里,取出心爱的青磁茶盏,递给我共赏。
“哎,你手中的这只茶盏虽然也漂亮、也精致,但我总觉得它比起书上那些个儿宋代的茶盏差了好多,”前辈她微笑着继续说道,“尤其是和天目盏一比较,高下立见,特别有意思。”
对我而言,“天目盏”并不陌生,毕竟个人也有收藏。然而,以前把玩时,从没咂摸出过它的好来。只觉得黑黢黢的小碗普普通通。直到去年我从大阪的茶道具商人手里,收到一件大正年间(1912—1926)的黑漆素面天目台后,方得一二分天目盏之美的精髓。
所谓天目台,其实是日人对于自中土浮海而来的盏托这一器用的称谓。依据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徽宗御笔《文会图》透露出的信息,宋人在使用天目盏时,是须臾不可离盏托的配合。这是因为天目盏多施釉不到底,若无盏托的帮衬,则茶盏很可能因为朴拙的外观而突兀了茶宴的高雅格调。
但,当二者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日光的萦绕下、在玄色的主持下、在汤花的簇拥下,漆器的大气端庄与瓷器的质朴无华相得益彰,默默地诠释“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意味,引领观者的心灵飘向远方的自然芳迹。个人在此间体会到的两物妙处,甚难用文字道尽。
后来,我索性为它俩拍下写真,并上传到微信,用作朋友圈的封面。再后来,有位爱茶的朋友又给那封面点了赞。说起这位茶友,我记得他在微信上的个性签名读来挺幽默:“我虽来得晚,但幸好未错过。”这话说的,真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