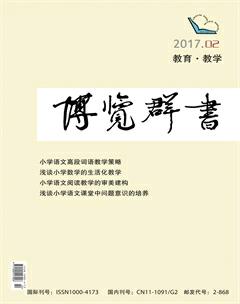逻辑实用主义的心理学方法论蕴含
李芳?向往
一、奎因与逻辑实用主义
1.简介
奎因生于1908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有《语词和对象》、《本体论的相对性》等。 《语词和对象》被誉为本世纪两部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之一,另外一部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奎因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但后来转向实用主义,并且把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逻辑实用主义。奎因对二十世纪后期哲学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他对分析和综合这一传统区别的批判,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观点,几乎成为讨论中的常识。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说:在《词语于对象》发表后二十年,美国大学里的哲学系研究生,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讨论“翻译的不确定性”。奎因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分析哲学中,也波及认识论和本体论。
2.对分析-经验命题二分的批判
奎因的最重要的几个论点,一个是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分析-经验命题二分法的批判,一个是对本体论的批判,另一个是“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奎因指称在分析命题和经验命题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线,还原论也同样不能经得起检验,他在文中说:
在现代经验论大部分是受两个教条制约的。其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我将要论证:这两个教条都是没有根据的。正像我们将要见到的,抛弃它们的一个后果是模糊了思辨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假定分界线。另一个后果就是转向实用主义。
针对分析命题和经验命题的二元划分,奎因巧妙地论证,所有试图论证存在着分析命题的方法都是有漏洞的,人们根本没有办法来证明分析命题的存在。奎因的论证过程不是很容易理解,如果要用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来阐述,我们可以参考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中的解读。施太格缪勒指出,奎因否定存在分析命题的实质是否定存在内涵。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所有的分析命题都是同义反复,除了“A是A”这种极端的同语反复之外,像“黄金是黄色的”这样的命题也可以视为同义反复,这个命题是康德提出来的,实际上分析和综合命题的划分还能够追溯到康德之前。在“黄金是黄色”的这个命题中,黄金的内涵就包括其颜色属性,或者说黄金的意义中就包含黄色,那么“黄金是黄色”的就是一个分析命题。还有如“所有的单身汉都是男的”、“马铃薯就是土豆”和“water 就是水”等。每一个词语都有一个内涵,如果两词A和B内涵一致,那么“A是B”就是分析的关系。而事实上,经过科学的发展,纯金实际上是白色的,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黄金是黄色的”变成了一个错误的命题,中间的问题出现在哪呢?
词语是人们对事物的命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始终在不断发展,人类认识中的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模拟,而不是完全没有信息损失的严格映射。在世界和不同的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简化映射,比如有人是色盲,只能区分黑白两种颜色,那么一个红蓝相间的物体在他眼中只具有灰色的属性,而在正常人眼里有两种颜色的属性。换而言之,内涵本身是不确定的,受生理的限制,人类认识的世界是一个简化甚至扭曲的世界,人们认识到的事物的内涵并不一定是准确的,而且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这一事物什么样的形象才是它最本质的形象,即使有一天,所有物體的原子结构都能被我们的肉眼所感知,我们也不能证明我们接收到了物体本身所蕴含的一切信息。这样一来,传统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分析命题是建立在内涵的概念基础之上的。现在奎因说,内涵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就不存在分析命题和经验命题的区别,所有的命题都是经验命题。比如说某个地区称之为“马铃薯”的东西,和另外一个地方称之为“土豆”的东西,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证明这是同样一个东西,很有可能有一天我们发现这两个对象的微观结构并不相同。
3.对还原论的批判
至于对还原论的批判,可以看作否定内涵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科学哲学还原论的著名代表为德国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卡尔纳普。他应用还原论研究逻辑语言的分析问题,主张可以从直接观察到的物体来给一切科学理论下定义或进行解释,复杂的知识经验体系都可分解为简单的因素,科学规律等同于许多观察报告的组合。而奎因则认为:
每一个语词要有意义,就必定或者是一个感觉材料的名字,或者是这样一些名字的复合,或者是这样一个复合的缩写。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较为合理的看法是,把整个陈述看做我们的有意义单位——这样就要求我们的陈述整体上可以翻译为感觉材料语言,但不要求它们逐个语词都是可以翻译的。
简而言之,还原论认为每一个词语有一个确切的对象,而在奎因看来,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永远没有终点,或者说不能证明已经到达了终点,所以我们对某个指称词的定义是不可能被证明完全正确的。比如说“黄金”,在历史上它的对象是含有杂质的一块金子,而现在它指称的对象可能是金元素的结晶体。我们用内涵来定义一个词,并且企图用这些内涵来界定一个唯一的外延,现在内涵被否定了,那么这个唯一合理的外延就是不存在的。对还原论的批判,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整体论。奎因说:
还原论的教条残存于这个假定中,即认为每个陈述孤立地看,是完全可以接受确证或否证的。我的相反的想法基本上来自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里关于物理世界的学说,我认为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还原论的教条,即使在它的弱化形式中,也和另一个认为分析和综合陈述是截然有别的教条紧密地联系着的。
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是最准确的,在世界和不同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映射关系,每个人认识到的世界并不相同,很有可能外界对象A在1的头脑中映射为A,在2的头脑中映射为B,我们不能说A对还是B对,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A在1的世界中与其它概念是逻辑融洽的,B在2的世界中也与其它概念是逻辑融洽的。我们只能运用一种整体的观点,在主体与世界之间,不存在严格的一对一的严格的完全没有信息减少的映射,我们只能求整体的相似,求实用的最大化。
4.翻译的不确定性
蒯因在《语词和对象》这部著作中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这一论题非常形象地阐述了他的整体论观点。翻译的不确定性,指在两门语言之间,不能够论证存在词语之间的严格的一对一准确翻译,换而言之,两门语言的词汇表之间不存在一簇平行的射线,将一个词指向另外一门语言中的另外一个词语。很有可能,一段话中的一个词,可以翻译为另外一门语言中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并且逻辑融洽。如前文所言,每一门语言中的单个词语,其内涵都不是确定的,与外在世界的对象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人们运用的语言体系,只是对世界体系的一种简化映射,在映射中,我们只能够追求整体的最大相似,实用的最大化。语言之间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追求翻译的整体相似,很有可能,一个词翻译为两个不同意义的词都能获得意义的整体最大相似性。换而言之,意义的最小单位不在于单词,至少也应该是一个句子,一个完整的陈述,追求单个字词的意义是毫无意义的,单个字词的内涵根本就不能被确定。
二、对心理学方法的启示
1.整体实用的观点
奎因给我们一个启示是,单个字词的概念对科学来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比如说“动量”一词,在牛顿的力学体系里定义为质量与速度的乘积,但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却作出了修正。实际上,人们可以修改动量的定义,也可以维持原来的定义,但这样就要修改其它概念的定义以确保整个体系的逻辑性。词语之间存在意义的联系,这些联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联系的存在才能够形成整体。我们观察世界,构建理论体系,追求的是这个体系最大程度契合世界体系,而不是某个概念精准地界定了外界某个孤立的对象。
不光是心理学,对整个科学界来说都是这样,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形成体系,将不同的概念联结起来的过程。即使学科越来越细分,但这些学科的分枝和其母学科、其它分枝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觀心理学,不得不说离成熟还非常之遥远,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概念支离破碎,心理学家没有办法在不同的概念之间架起桥梁,构建其联系,这极大地损害了它的应用性。
对心理学家来说,不应该将精力仅仅放在验证一两个孤立的观点之上,而要更多地研究这些观点之间的联系。比如说对于“内隐记忆”,很有可能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我们用奎因的观点来看,这些定义可能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必要花精力去论证哪一个定义是最准确的,或者贡献一个新定义,我们需要的是勾连起这个概念和其它概念之间的联系,然后论证由这些联系带来的整个系统的实用性。
实用是目的导向的,但其前提是能够最大程度符合客观实在。某种程度上说,符合实际的最实用,所以,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换个角度来看,人类的进化过程,处处体现了实用主义,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只感知到可见光,因为可见光对我们存在的意义最大。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是简化的,这种简化由感官的局限带来,导致我们脑中的世界也只是客观世界的一种简化形象,我们过滤合并了不必要的信息,只接收最重要的信息,最后构成了这个映像。即使我们现在借助语言和工具,构造了一个更契合实际的对世界的描述体系,但这仍然只是一种简化,这种简化仍然是以实用为导向的。当然,因为符合实际的最实用,所以我们也是以实证为导向的,只是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清楚,我们要证实的不是单个的概念,而是整个有机的体系。
2.跨文化的观点
根据“翻译不确定性”的观点,不同语言体系的词语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同指称的词在不同语言中可能有不同内涵,同内涵的词在不同语言之中可能实际上有不同外延。按照心理主义的观点,内涵是一个词在一个人脑中产生的某种状态,按照这样的观点,不同文化的人之间,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心理结构。当我们是在研究外在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一种整体最实用的描述,但当我们研究人类本身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不同文化群体对同一个事物,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不同文化的人运用不同的语言,语言的结构很大程度上代表认知的结构,认知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基于头脑的构造。换而言之,不同文化群体,在神经结构上可能产生了某种分化,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在推导一些普适性的观点的时候,往往要考虑文化的不同,比较不同之处,往往更能够找到底层的相同之处。
比如弗洛伊德通过梦的分析,认为儿童具有仇视父亲、依恋母亲的“恋母情结”。母亲是儿童里比多的对象,但是父亲却成为儿童的“情敌”,因此儿童的梦境中经常会出现父亲意外死亡的内容。这表现了儿童潜意识中对父亲的仇视。但是对处于母系社会的巴布新几内亚群岛上的土著人的研究表明,那里的儿童在梦境中仇视的对象不是父亲,而是舅舅。父亲是母亲的情人,舅舅是儿童行为的管教者。为什么土著儿童不仇视自己的“情敌”,而仇视与母亲没有情欲关系的舅舅呢?这说明儿童潜意识有一种摆脱权威控制的愿望,谁代表了这个权威,就成为梦境中的牺牲品,与儿童的情欲发展无关。跨文化的研究为纠正弗洛伊德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佐证。
——充满艺术的实用主义者Eva S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