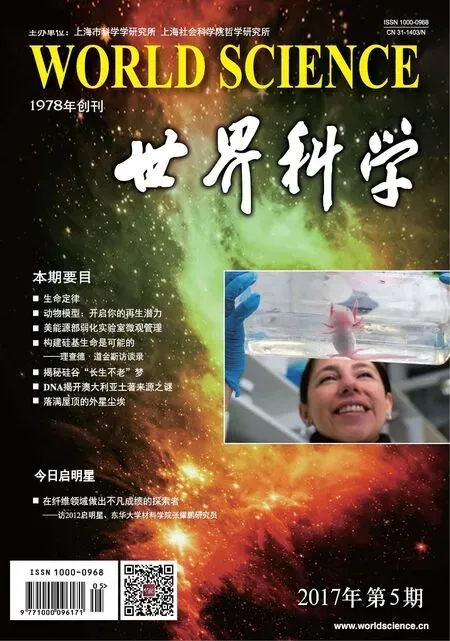再生医学亟需跨学科合作
赵梓钧 马晋平/编译
再生医学亟需跨学科合作
赵梓钧 马晋平/编译

● 斯蒂芬·巴迪拉克认为,科技进步的发展已经跑赢了我们对器官发育和损伤应答的理解速度,是时候该重新评估这一切了。
虽然组织器官工程前景广阔,但遗憾的是目前医学科学还不能将这些实验室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最初用于制造可替代组织的设计样板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该样板中,细胞在一副具有人体某器官形状的可降解支架上培养,继而将培养后的组织植入受者体内。不计其数的报道声称利用该技术可以重构出耳朵、血管、膀胱和人体其他部位,这些报道激发了人们的探索热情。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组织工程学应运而生。
但是,除了少许特例,大部分替代器官还不能移植入人体,原因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普遍存在的监管、生产以及费用报销等方面的问题。虽然大部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还是拖了该领域的后腿。一个关键的问题可能是,通过上述方法制造出的组织缺少很多维持细胞生存和功能的支持元素。器官和组织的存活,需要有正常功能的血管、淋巴和神经网络,但这些既没有被纳入到现有的设计样板当中,移植器官在死亡之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实现有机发展。此外,组织工程师也没有考虑到细胞的微环境,包括机械因素、pH(酸碱度)、氧浓度以及嵌入细胞外基质的信号分子。因此,一旦这些精心设计的组织被移植入体内,它们就会被当作是“异己分子”。最终,这些移植物不仅不会成为生长良好的直接替代组织,反而会因为缺少营养、适当的生长因子和神经支配网络而迅速死亡。
此外,免疫系统对于组织工程学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免疫系统是人体中免疫监视、防御和高度调控的系统,比如支配和协调人体组织器官发育、损伤和感染后的机体应答、对异种细胞的反应以及组织的修复和重建。这些机体的反应过程在生物学家、免疫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组织工程学界却忽视了免疫系统会不可避免地对支架以及人造组织进行识别这一事实,直到组织发育晚期他们才意识到这一点,而在免疫抑制的啮齿类动物模型中进行这类试验,也根本没有考虑到免疫系统在后续临床实践中给组织工程带来的潜在影响。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基因组图谱、3D细胞打印、干细胞生物学、生物材料学和生物反应器设计等领域正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但我们却还一直“墨守成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高端影像学技术制作出的模具,一个病人耳朵的3D打印复制品就可以由不同种类的细胞逐层打印来得到。当这种3D结构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个事实:在这个复制品中,对于细胞间通讯至关重要的细胞连接尚不见踪影。
不难发现,人们没有考虑到这些机器化技术对细胞存活以及细胞表型所带来的影响。这些技术忽略了胞外基质分子,而且3D打印技术无法“打印”出合适的感觉神经、运动神经以及淋巴系统。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构造只能带给人们视觉上的冲击,并成为前沿科技中没有实际用途的反面教材。
为了让组织工程学向前更进一步并且履行该领域的承诺,人们需要做些什么呢?现在是进行跨学科合作的绝佳时期。通过跨学科合作识别并攻克那些阻碍功能性替代组织和器官创造的难题。这些挑战并非难以逾越,但必须予以承认。
让人感兴趣的是,在人类基因组中,组织和器官再生具有潜在的可能性。人们已经从蝾螈体内得到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蝾螈在受伤之后,可以完成身体部分的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再生过程,先天免疫系统在发育与再生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巨噬细胞(一种长期被认定为与慢性炎症有关的细胞种类)对于蝾螈肢体再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需求表明,人们也许可以通过与天然免疫系统合作来重新激活人体中类似的再生信号,而不是试图去逃脱或抑制宿主的免疫应答。成功的组织替代手术就是这么简单:将嵌入生物学信息的合适模具置于意向解剖部位中,并利用人体本身作为最终的生物反应器,而并非试图在体外重新创造出器官或组织。
组织工程学和再生医学领域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现在是该有所修正的时候了。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许下的诺言仍然可以兑现,但这取决于组织工程师群体是否有意愿确定有益于该领域发展的制作流程以及剔除各种先天不足的思维方式和技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纳入正常的哺乳类动物发育和再生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组织工程学和再生医学的未来才能充满希望。
[资料来源:Nature][责任编辑:松 石]
本文作者斯蒂芬·巴迪拉克(Stephen Badylak)是宾夕法尼亚州匹茨堡大学McGowan再生医学研究所的外科教授。他还担任《NPJ再生医学》杂志的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