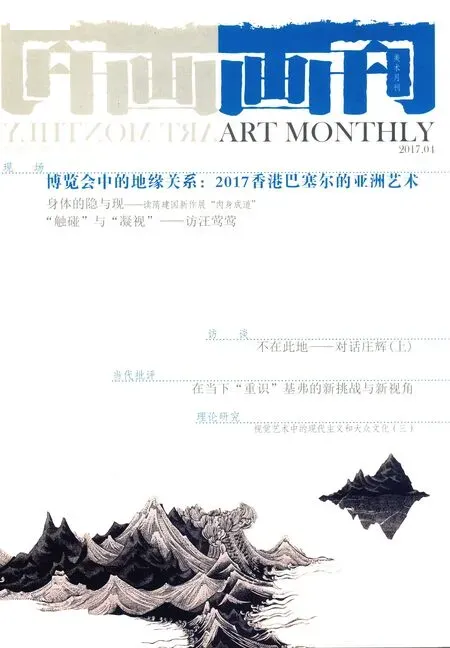不在此地
——对话庄辉(上)
杨 青 庄 辉
不在此地
——对话庄辉(上)
杨 青 庄 辉

《东经109。88’北纬31。09’》 庄辉 黑白数码打印照片、录像 尺寸可变 1995-2008年
编者按:从1992年创作第一件作品《为人民服务》开始,庄辉的艺术一直持续关注个人身份和集体主义的关系。城市、农村、工厂不仅是他在首件作品中设置的三个场域,也成为他二十多年艺术创作的视觉重心。从工厂到城市,再从城市到农村,庄辉在三者的时空关系中穿梭游荡,探讨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种种问题。然而,近两年来,庄辉的艺术发生了一些具体的变化,艺术家的注意力渐渐由人群投向荒野,由社会转向自然。 常青画廊正在展出的《祁连山系》,即呈现了庄辉的艺术转变的最新动向。在展览现场,庄辉用影像、绘画、装置搭建了一个与祁连山对话的空间。通过作品的呈现,庄辉将观众的视线和情感引向一个更为广阔、未知的自然世界。
为了更好地理解“祁连山系”展览和庄辉近年的艺术变化,《画刊》特邀媒体人、策展人杨青与艺术家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谈。话题涉及庄辉艺术的方方面面,分两期刊登,以飨读者。
(一)
杨青:你最近的个展“祁连山系”引起了很多关注,表面上看和你以前的作品有很大的颠覆和突破,但是我觉得从头梳理的话,很多变化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我想和你从最初的经历开始聊起。你是从1979年进入工厂工作,在“文革”结束以后,当时的工人身份意味着什么?
庄辉:当时工厂已经不再招工了,如果是工厂的子弟,上一代人退休了你可以顶替,有“接班”一说。那时候工人的身份正好从老大哥到无产阶级转型,工人已经没有什么优越性,铁饭碗在瓦解,我进工厂的时候正好大锅饭开始出现裂缝。
杨青:那个时候除了当工人有没有别的选择呢?
庄辉:还有一个是当兵,也可以考大学,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当兵我眼睛视力不够,只有当工人这一种途径。
杨青:当工人可能是当时大多数人的选择,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会有不满足或者别的想法吗?
庄辉:别人我不太了解,反正我对当工人没有太多的兴奋,真的是无所谓的心态。我进去的第一个工种就是翻砂,翻砂和下煤窑差不多,进去的时候把工服换上,出来的时候要彻底洗一遍,每天的鼻孔都是黑的。而且主要是吃不饱,还没到下个月发工资就没有生活费了。
杨青:从1979年进厂到1992年创作第一件正式作品,这当中十几年的时间,你的主体身份都是工人,用艺术创作来表达是如何从这漫长的工厂生涯中孕育出来的?
庄辉:这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涉及我对艺术对绘画一些最初的热爱。早期的启蒙和我父亲有关,他是肩背照相机到处行走的一个摄影师。那个时候没有照相馆,背着相机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的露天钉一块布景,有兴趣的人就会过来拍照。我们在马克吕布很早的照片里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生活影像,我父亲在1949年之前是这么一个角色。
杨青:到处行走,算不算居无定所呢?
庄辉:应该算,他们的生活是比较流浪的。我后来听别人说,1949年以后要修建兰州到新疆的兰新线铁路,我父亲当时在洛阳,他顺着这条铁路修建的进程先后去了西安、天水、兰州,都是这样一边行进一边给人照相,最后一直到乌鲁木齐。他觉得玉门这个小镇很安静,没有太多的人,也没有照相馆,就在这个地方安家,跟别的老乡刚开始合作搞了一个玻璃房子的照相馆,后来变成公私合营。我从小特别喜欢去他的照相馆玩儿,我记得父亲老的照片是玻璃底片,最有意思也最吸引我的是冲洗照片。把帘子拉开再合上就算是用自然光曝光了,放在盘子里的底片,一会儿就会有人影慢慢显现出来。而且父亲经常被请到附近戍边的兵团拍照片,父亲给他们拍合影,也拍单独的照片,都是由连队组织。这是我7岁以前的记忆。
杨青:你后来的《大合影》很像复制你父亲当年的行为,只是把你自己放进去了。
庄辉:所以我得往前回溯和你分析,所有的事都跟前世有渊源。
杨青: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庄辉:玉门那个地方寸草不生,受到的文化影响比较少,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启蒙。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小时候画的都是革命英雄,记忆最深的是连环画《英雄小八路雨来》。另外有机会接触画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革”,“文革”意味着没有经济生产,都是文化艺术在革命。
杨青:精神生活特别亢奋。
庄辉:对,特别亢奋。尤其是小孩,我们在小学每天上课的时间不是很多,挖防空洞和办黑板报都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事。
杨青:“文革”发动了各种宣传工作,全国上下都投入进来了,好像人人都受到一种历练。
庄辉:刚才说的是幼时受到的影响,到了13岁我跟随出嫁的姐姐从甘肃回到洛阳。回去以后我们住在筒子楼里,邻居是一个画国画的老师,我就开始和他学画。老师也不让我拿毛笔,只是让我画素描,画小石膏球或者是三角形,有时候拿着工农兵形象丛书临摹,慢慢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训练。后来社会上开始有了考大学的美术培训班,我白天工作,晚上就去工人文化宫这样的培训班去画画,基本上基础是这样打成的吧。

《公元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日洛阳市一拖公司七号幼儿园全体师生合影纪念》 庄辉 黑白照片 67.5cm×19cm 1997年
(二)
杨青:你1992年做第一件正式作品《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和由来是什么?是什么驱动你要做这件事?
庄辉:当时有一个大的环境,经历“八九”以后,整个中国的艺术界、思想界都掀起了一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从改革开放到1985年这个期间产生出来的很多思潮,忽然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八九”之前现代艺术运动实际上非常活跃。
杨青:以“89现代艺术大展”为界。庄辉:“89现代艺术大展”是终结。中国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关口,如果当时一直沿着对西方全盘拿来的路线,现在看起来也是行不通的,否则不可能出现这么纠结的局面。艺术上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显得一片寂静,原因一方面是被压制,另一方面大家也在反思。“89现代艺术大展”我没有任何的参与,但也不断地通过《中国美术报》《江苏画刊》《美术》杂志等等有限的渠道看到现代主义思潮的美术运动。渐渐我觉得非常不满足,那就是在艺术上产生的所有东西,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和我们个体在今天遇到的问题也毫无交集。如何面对我们的现状,这个时候就显得特别迫切。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文革”当中渡过的,因为我们经历过“文革”,所以仍然有一种强烈的社会的主人公意识,尤其是还当过这么多年工人,总觉得这个世界所有的变化要跟自己的行为和命运联系到一起。1992年我做《为人民服务》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的,这个作品实施的时候分为了农村、城市、工厂三个部分。
杨青:是有意识分成了三个场域吗?

《倾斜11度》 庄辉 铁、铜、不锈钢、烤漆 300cm×904cm×150cm 2008年
庄辉:对,分成三个场域,对应三个时间段。
杨青:为什么在一个时间轴上铺陈这么长时间,大概都有三四个月了?
庄辉: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意识,自己当时没有多想,就是觉得要战线拉得长一点,后来发现我做事好像是有这个习惯。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和时间发生同样的事情,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
杨青:你做完《为人民服务》之后又被约谈、搜查,对你进一步做作品会有什么影响?
庄辉:这个我倒不会受他们太多的影响,因为我当时和外界有比较多的书信往来,比如北京、昆明,比如说朱发东。
杨青:当时这种艺术创作还是很地下很实验的吧,大家也没有公开地展览和传播,你又是在洛阳那么内陆的城市,彼此怎么知道的呢?
庄辉:知道的方式不同,那时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网络,可是我们会有一些通信。这个圈子很小,有所了解之后如果彼此很有认同感,大家就会互相推荐,这样就渐渐形成一个艺术家圈子。其实这些信件送到我手上的时候都已经被拆开审查过了,控制的方式很粗暴,赤裸裸地丝毫不加掩饰。1992年做完《为人民服务》之后,我拿着这一堆做好的资料就去武汉和这些朋友们见面。我记得当时住在周细平家里,他家在武汉东湖边上的一个渔村。细平带我们去见了艺术家任戩、理论家赵兵和他太太未明,到任戬的工作室时看到他们正在做波普邮票类的作品,细平也在讨论波普艺术,还有现在川美的院长庞茂琨也从外地去武汉和我们聚会,他们后来又给我介绍了上海其他的一些艺术家。那趟行程我先到武汉,后来又去了南京、上海、济南、北京,到处就这么游走。
杨青:外出这么久,岂不是要经常请假吗?
庄辉:对,正常请假是不可能的,我通常都是先把假条给我的工友,让他们第二天再帮我递交,反正厂里知道的时候已是既成事实了。我虽然懵懵懂懂,但是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我不在此地,我有其他的愿望。
杨青:但是当时做这种艺术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是这么一种地下的状态、被压制的状态,又没有市场。
庄辉:有没有未来和市场我都不关心,仅仅就是喜欢。除了艺术还是活着的意义之外,其他都和自己的生命无关,这种热爱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那时我上夜班的时间是从晚上12点到早上8点,下了夜班已经很累,但是仗着自己年轻,一下夜班就和朋友约着到郊外去写生。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秋冬交季我和朋友骑车到洛河边上画风景,两个人各自画各自的,过一会儿他画完了叫我,我已经在那个土窝子里累得睡着了。
杨青:既然不好好工作,工人这个身份在你身上发生过太大作用吗?我听你这样说,觉得你在情感上肯定是没有接受这个身份的,好像是寄居在这个名义之下,身心都不在这里,所以要经常逃出去。但是我想这么漫长的工厂经历,应该或多或少都有烙印。
庄辉:实际上我跟这个工厂没有那么多的联系,和工友也比较少来往,下了班都是约画友一起画画,我们后来还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做画室。现在也活跃在北京的几个艺术家,比如白宜洛、练东亚、李铁男,都是那时洛阳拖拉机厂的工友。
杨青:能够在工厂里找到这么多志趣相投的人也不多,工厂顶峰的时候工人有三四万吧?
庄辉:是的,加上家属可能有十几万人。那个时候画画的人多,工厂有自己的美术班,还有工人俱乐部,俱乐部专门负责做美术培训或者是书画交流的展览。这个跟洛阳的书画传统没有关系,应该是和“文革”的关系比较大。“文革”的时候都成立了工会,工会下面有负责搞宣传的工人俱乐部,黑板报大赛就是宣传的主要方式,需要培养插图骨干。我有时在黑板报大赛上又能派上点用场,其实我知道领导对我是又恨又气。
(三)
杨青:1998年有一个展览“是我”,这个题目非常直接和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宣言,我理解“是我”的另外一种称谓叫“我是谁”。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批实验艺术展览当中,我觉得“是我”和你的“大合影”的内在联系紧密度比较高,因为这个展览开始关注到艺术家看待个人与社会的角色等等的关系。
庄辉:我的看法,与其说“我是谁”,不如说“我是我”比较准确。“我是谁”这个话题比较早就过去了,到这个时候就敢于正视“我是我”。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些艺术家对自己现状的关注非常强烈,一直到“是我”,有了这个阶段集体式的呈现,遗憾的是这个展览在开幕前就被封掉了。“是我”其实非常重要,和“89现代艺术大展”有完全的区别,我认为这是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的开始。这个“当代”当然不是按照西方现当代划分的,可能用“当下”更准确一点。那个时候我们谈的都是当下的经验,正在经历逐渐向个人经验转化的过程。回到我做《为人民服务》的初衷,这句口号也是“文革”前后长期主导中国文艺路线的方针政策,我非常想做的是回到自己的现实来呈现工作。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朱发东也在做《寻人启示》,这些事情基本上就发生在1992、1993年之间。

《玉门人家照相馆》 庄辉 2008年
杨青:你刚才说这是向个人化经验的寻找和转化,但是每个人的个人经验是不一样的,具体到你身上,为什么你关注集体化的这种社会结构,并诞生了《大合影》?
庄辉:这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我是在影像的范围里考虑的,我们从外来的资讯里看到新兴电子类媒体的出现,比如电脑、电视、数码相机等等,虽然还没有使用过,但是已经能看到新媒体的一个趋势,颠覆了对以前传统的影像的认识。我在思考影像和它的技术之间最初的关系,促使一个事物产生的原始动因是最有力量的,我很想在这个作品里强调影像最初的功能和意义。第二个原因是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集体主义正在瓦解和消失,个人的生活和经验不断出现。中国历史上一直处在家国和集体制度之下,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力量进来之后开始瓦解,我想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的大时代。
杨青:这个时代和你1979年进厂时大锅饭开始出现裂缝也是一样的性质,都处在一个变革的点,而你抓住了这些点。
庄辉:这个阶段比较有意思,我要用最朴素的记录方式给它留下影像。
杨青:我觉得你的作品脉络是很清晰的,创作时间跨度都很长,每个作品都是时间和空间叠加的,比如说《为人民服务》《 一个和30个》《大合影》。
庄辉:我想提到1995年我的另外一个作品《东经109.88 北纬31.09》,这个也是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当时我在三峡大坝沿线的几个地方分别打了孔,2007年的蓄水大概到257米高的时候,我又派助手去到这三个打孔的地方各做了30分钟的录像。三峡蓄水埋葬了中国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断了中国人自己的文脉。我为什么派助手去而不是自己去?是因为我完全不忍卒看,你知道民族得以存活和延续下去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靠它的精神气质。我最近才看到当地诗歌的历史,三峡的奉节县产生过中国古代六七千首著名的诗词,杜甫三分之一的诗都是在这个地方创作的。刘禹锡、白居易、李白、杜甫、苏轼在这个地方来了又走,每个后来的人都会留下对前者的凭吊,一代一代相传累积下来这种文化。前段时间我正好去台北故宫看到宋代的绘画,南宋灭亡的时候让人感到这个民族似乎被彻底埋葬了,但是只要艺术还在,精神价值就能留存下来。所以我强调作为艺术家要明白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就不值一提。
杨青:你对一个主题的关注,比如说三峡、大合影、玉门,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图景,有点像是当年你父亲背着照相机的流浪,一个驿站接一个驿站在走。你似乎是在自己的谱系里行进,你对主题是怎么进行选择和评判的?
庄辉:做艺术“做”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每个作品从思考到完成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学习的过程,往往通过一个作品的实施而帮我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当作品呈现完成的时候,这个工作就结束了,如果对别的东西有兴趣我就再转到其他工作,所以我对下一步要选择什么并不是那么明确和具体。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有弊端,不过我喜欢活在当下的感觉,这会让你察觉到一些细微的问题和变化。既然学习对于艺术家更加重要,那么你就要让自己保持比较敏锐的状态,你得像个精灵一样,对这个世界有敏感的察觉,让自己时刻能发现一些问题,时代则是你创作所投射的一个背景。在这个状态里你就会对你的工作方向做出选择。
杨青:做《玉门计划》的时候,也是由于你的敏锐和警觉而抓到的主题吗?
庄辉:这个有比较直接的原因,因为我妹妹就在这个城市。玉门市以前是政企合在一起,当地政府本来是以油田存活的,改革开放以后政企分家,油田归中石油管,市政归当地政府管,政府一下子失去了主要支柱产业。我妹妹一家就是属于市政单位的人,生活长期陷于困顿,我一直给他们提供经济帮助,后来就想去看看为什么生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结果2006年去了以后才发现非常恐怖,然后简单调查了解到中国类似这样的城市原来有100多座,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那次回来以后又查了很多资料,考虑介入的方式,等到真的介入以后造访的频率更高。在之后那一年期间,我们为此走访了石嘴山、白银、大庆,还有攀枝花。当你翻过攀枝花的山往下走,真像是人间地狱,黑的、黄的、红的、粉的各种烟到处冒出来,房子都是灰秃秃的,人在那里像小鬼一样拼命的炼钢。
杨青:这是资源枯竭型的发展模式,当不再有造血能力的时候,其实社会就是整体崩塌,像地下煤矿的塌方。
庄辉:我不想在这里搞纪实摄影,我是艺术家,我应该用自己的身份和方式介入到这个空间和事件里。我一方面要关注这个事情,另一方面还希望给艺术提供一个超越边界的平台。所以我们介入的方式是在玉门当地开设为期一年的照相馆,当然这个项目既有空间的因素也有时间的因素。
杨青:其实“玉门计划”相当于攀枝花计划、大庆计划,可以这样说,它是这类城市或者是这种生活境况下人们共同的状态。
庄辉:不是状态,是最后的命运!看到人类膨胀的欲望,当时我是很绝望的,康学儒曾和我做过一个访谈,文章的名字就叫《没有未来》。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表面所描述的那样,科技的发展,人类驾驭世界的能力,全是杜撰的谣传和神话,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事实,你眼前的整个世界才是事实。我们也会在媒体上看到真相,但是你不深入进去就真的不知道具体细节。
杨青:面对这么残酷和惨烈的现实状况,为什么你采用了这么温情的给家庭拍生活照的方式?
庄辉:因为我还是一个人,还保有良知和人性,我希望把玉门最后残存的表情保留下来。如果再过百年,当玉门成为历史以后,现场的照片也许不如这些人的形象更让观众揪心,更加有痛彻的感觉。
杨青:你20世纪90年代骑自行车去西藏时经过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2000年再去的时候就消失了,有点儿像玉门的隐喻。这种命运很像当时和牟莉莉留下的影像,只是牟莉莉这个影像当时是无意的,但是玉门是有意的,也许再过多少年就是历史存留的一个切片和证据。
庄辉:没有什么比人的肖像更能够传达出此时此刻人的精神活动,因为我相信当一个人面对镜头的时候,你的信息是被摄入在这个底片上,它会将此告诉后来的人。(未完待续)
——访玉门市市委书记雒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