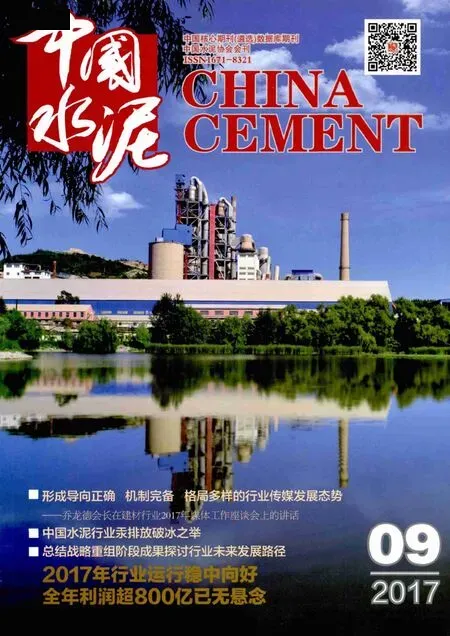水 泥
苗见旭

我第一次见到水泥的时候,还不知道“水泥”这个名字。
父亲从镇上回家,见人就问,你见过“洋灰”吗?众人一律现出艳羡,一律低了头注视父亲捧着的东西。这东西粉粉的、细细的,像钢磨磨的绿豆面。有人干脆捏一点放进嘴里,骨碌着眼睛咂摸,立刻“呸呸”吐掉。“我当成杂面了,你咋倒人呢?”“谁倒你了,这是石头面儿,不是粮食面儿。”父亲得意并戏谑道。
其实,它比粮食面主贵多了,父亲一路敬仰地捧着,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找箩。
我家院子西北角有一棵大槐树,平日里,全家都在下面吃饭,一天,母亲说,多时垒一平展台面,省得木桌搬来搬去的。母亲的话像圣旨,父亲立马就用残砖碎瓦砌了台面。台面砌成,敷了一层黄泥,黄泥之上又施一层白灰,接下来,这一捧水泥就派上用场了。他用箩均匀地筛;一手端箩,一手震动箩框,水泥就灰雪一般洒在白灰上。及至用瓷片打磨几遍,台面就镜子一样光亮起来,我斜了眼睛去看,真就看见了槐树的枝叶,枝叶间阳光的亮斑以及母亲笑成一朵花的脸。
父亲的水泥来自镇上修架的三级提灌,父亲是第一批选出的土木工程师,负责民工的筑建工作。
所谓民工,就是由公社从各个生产队抽调的青壮年农民,吃住在工地。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刚开始抽调了一百多个壮年劳力。几天下来,全部蔫了,无精打采。父亲着急起来,一位年长的民工说话了,“嗨!弄几个娘儿们过来,立马就活泛了。俗话说,男女混杂,劳动解乏嘛。”
三天以后,劳动工地上红旗招展,大闺女、小媳妇的加盟使劳动的阵营热火朝天,人们说着、笑着、唱着,又见缝插针地打着诨,整个工地洋溢在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里。
公社书记坐着东方红拖拉机来了,他穿着白衬衣,绿裤子,站在拖拉机的拖车上,叉着腰大声说话。“老少爷们,大家辛苦了,你们知道车上拉的是什么吗?这是高标号的水泥,无梁产的最好的水泥,县上特批的,比咱烧的石灰强多了,谁不信舀碗水搅和一点试试。”
书记的话应验了,下午的地基浇灌,这高标号的水泥真就发挥了威力。民工们把水泥和沙子按比例拌匀,然后浇水,立时,嗞嗞的声音就拌着水泡响起来,民工们瞪眼、噤声注视着这奇异的现象。就像三伏天,你向干裂的大地泼出一瓢水,“哧喇”一声,水就不见了......
四十年后,站在提灌坚如钢铁的基座前,我就想,这是我最初见到过的原生态的焦渴。这焦渴是水泥对水的渴望的展现,或者说是水对水泥的心悦诚服、死心踏地的皈依。这是阴阳交和的典范,是先“和谐”而后产生凝聚的真理。
再后来,读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才知道石灰的精神以及水泥的前身就是石灰这些知识。是呀!千百年以来,石灰一直就是优良的建筑材料,外国也有石灰石,他们也烧石灰,也约定俗成地用石灰建筑各种雄伟的宫殿,可为什么用着用着就改成水泥了呢?查过典籍才明白,石灰在古时候的优点到了现代就演化成缺点,比如,凝结慢,凝结强度达不到现代建筑标准。也就是说它先天还不完美,还有不足,科学家就是花了气力在石灰优良品质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活性的元素,使石灰摇身成为水泥,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和升华。

由此,我想,一个人天生我材必有用。而这材又不是天生完美,它需要后天的学习和完善,就像石灰需要添加新的活力元素。而当自身修得完美之时,一旦机遇来临,事业便如夏花之绚烂。
同样的道理,一个家庭,夫妻双方,互相比照,取长补短,久之,相貌也会趋于相似,万事不就兴盛了吗?唉!这小小的家庭也有水泥“交融”的影子!
还是《圣经》说得好,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无论是水遇到了泥,或者是泥遇到了水,结果都是泥中有水,水中有泥,都是阴阳聚成的福气。
“水泥”呀,谁起的名字,简明的文字,深邃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