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传播:理论话语的里程碑1
[德]亚历山大·格尔克
翻译: 吴璟薇3
全球化与传播:理论话语的里程碑1
[德]亚历山大·格尔克2
翻译: 吴璟薇3
全球化进程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本文将从传播学和传播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全球社会和全球媒介理论的发展历程。这些理论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进程紧密相关,而在不同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特色。迄今为止,全球社会和全球媒介理论的发展变化总共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阶级斗争下的全球化理念;(2)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念;(3)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4)卢曼的系统论与世界社会。在对上述四种理论进行分析和比较之后,文章将关注点转向大众传媒领域,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娱乐和公关之间的异同。
全球化;传播;世界体系;大众媒体;法兰克福学派;系统论
DOI 10.16602/j.gmj.20170002
当我们今天观察现代社会及传播时,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全球化现象正在兴起。而对于传播学和传播社会学来说,上述现象并不新奇,我们可以从理论角度分析它的整个发展历程。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社会和传播都处在国家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这一观点起源于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蓝图,并(暂时)结束于卢曼(Luhmann)提出的、将世界传播归入一个系统的世界社会(Weltgesellschaft)概念。在二者中间还有一系列从各个角度研究全球社会和全球媒介中的行为的里程碑,它们常常根据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发生变化。从这个背景来看全球化的概念的变迁,就会发现它其实只是认知上的改变,正如阿明·纳瑟黑(Nassehi, 2003, p.192)所言,“也许事物只是呈现出它新的一面而已,但本身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
本文的目的在于呈现事物的这一面是如何变化的。这种变化首先开始于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之后的内容将逐一分析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念、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系统论对世界社会的建构。传播学者Joachim Westerbarkey认为,每种全球化理念都通过一系列的论证文章而发展壮大(参见Westerbarkey, 1991, 1995, 2001),这具有双重意义。在上述四种不同的理论构建中,每种理论首先需要找到自己的核心原理。此外,上述所有理论都会对以下问题感兴趣:大众媒体和传播对全球化的产生具有什么样的贡献,以及这些理论具有什么样的估量意义(Stellenwert)?紧接着是关于贡献的问题: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每种理论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 经济的首要地位
马克思与恩格斯(2002: 19)认为,从经济角度看的话,迄今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资本时代的社会也是如此,并表现出彻底的阶级对立。根据内部分化的对立,封建社会(封建主、臣仆,行会、学徒、农奴)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资产阶级(Bourgeoisie)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资产阶级创造的所有东西中最具革命性的地方在于,它们将封建社会中多元的行为和传播关系凝练为经济核心。
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 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Marx & Engels, 2002, p.22)。①
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赋予了其他社会领域作为“上层建筑”(Überbau)的地位。诸如法律、医学、宗教、艺术、科学以及大众媒体等社会领域,也是为了保证实现经济基础而产生的(参见Bauman, 2003, p.10):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医生、律师、 牧师、 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Marx & Engels, 2002, p.22)。②
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相比于其他物质和精神权利更具有优先地位。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Marx & Engels, 1953)③
没有揭露和创造性的毁灭,这个过程是无法实现的,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启蒙(Aufklärung)时刻:“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Marx & Engels, 2002, p.23)④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看,首先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就是通过劳动而产生的令人绝望的剥削: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MEGA, 1975, 3;85, 转引自Fetscher, 1983, p.95)。⑤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MEGA, 1975, 3; 85, 转引自Fetscher, 1983, p.95)。⑥
在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面前,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受到压制的(参见Adorno, 1973, p.399),在经济基础的支持下,被压迫阶级对自身所处阶级地位的意识正在形成,他们的需求就是消除阶级矛盾(参见MEGA, 1975, p.3, 300)。
基于这样的需求,竞争中的统一隐喻(Einheitsmetaphern),例如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在无产阶级看来就会产生不合适的认同。作为差别而存在的国家,在Gellner (1999, p. 31)[同样可参见(Richter, 1996)]看来虽然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现象,但是最终既不会必然地也不会偶然地(“意识形态的意外,ideologischer Unfall”)被压迫。首先,国家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做在每个人类社会中都会自然产生的一种机制。马克思主义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看作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首先产生于资产阶级所参与的人口集聚和生产资料的集中过程中:“原先各自独立的、 几乎只是由联盟关系联系起来的, 各有其不同利益、 不同法律、 不同政府、 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区, 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 统一的法制、 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 统一的税关的民族了。”(Marx & Engels, 2002, p.24)⑦从区域边界中产生的政治中心化是腐朽的,因为它对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起不到推动作用,反而会起阻碍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构的社会观中,文化差异并没有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同时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Marx & Engels, 2002, p.40)。⑧
由此,一个民族国家的单一社会观念形成了,它那不断加剧的分解(以及不断转化为一个世界体系)与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密切相关:“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 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Marx & Engels, 2002, p.40)⑨相比之下,大众媒体和文化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理论的空白(参见Robes, 1990; Paetzel, 2001)。而马克思理论构思的吸引力在于,它对社会发展中作为核心区别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以及基础/上层建筑进行了明确划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阶级行为被合法压制的情况并不常见,因此这条道路也并不艰难。各种各样的马克思帝国主义理论也沿着这个路径,分析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展变迁,并将自己划分为全球化理论。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帝国主义的内在必要性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探讨。列宁(1946)认为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内部的垄断和卡特尔⑩所形成的,是资本主义过渡的更高(并非更好)形式。

因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在垄断中自由资本竞争开始出现,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危机,这些危机通过以下五个方面体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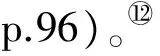
罗莎·卢森堡对帝国主义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a)国家之间以及b)对抗世界上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决战,是资本主义走向末路的前奏:

按照上述分析,帝国主义存在一连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灾难,这些灾难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共同阻碍了资本积累,因而不可挽回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终结(参见Luxemburg, 1921, p.445)。这一结论也正好符合那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批判者的观点,他们一直坚持全球化资本主义会造成全球化战争:
在美国的全球化反恐背后,其实世界上已经很多地区完成了军事化,因而这也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美帝国主义”。隐藏在这些战争后面的目的,是通过全球市场体系将主权国家变成开放领域,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以及过去的远东地区的再殖民,而且也是对伊朗、伊拉克和印度次大陆的再殖民,迫使他们进行经济改革甚至采取军事措施。战争与全球化是联系在一起的(Chossudovsky, 2002, p.414)。
齐格蒙特·鲍曼正看到了这种通过军事手段而达成经济目的的全球化资本结构特征。现代性仅仅是一个通过让各个区域相互分散的空间来推动国家社会向殖民主义时代发展的区域原则。

Hardt和Negri(2004, p.28)进一步发展了此观点,他们将战争看做“所谓的社会最高组织原则”:“政治只是其手段或者其幻象,最后的事实表明,那些国家合约也不过只是打开别国大门的一种战争方式。”在Hardt和Negri(2004, p.29 ff)看来,全球化是一种在时空上对战争的无限制,更是外交和内政之间不断增加的适应与融合,以及一种对传统敌我系统的重新鉴定,正如他们对反恐战争的论述:
尽管敌人很抽象并且边界不明,但合作者的联盟不断扩大且呈现出越来越广的趋势。全人类原则上可以为了反对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恐怖主义,而联合起来。“合法战争”的概念在政治家、记者和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再次兴起,特别是在以人权为名义所发起的反恐战争和各种军事手段中兴起(Hardt & Negri, 2004, p.30)。
众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以及战争灾难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属于理论难题,只有等到从帝国主义发展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溃的那一刻才能观察到,在这个过程中统一和瓦解必须至少发生一次。根据Karl Renner的观点,帝国主义再殖民的新方法(不受时代限制的),就是首先形成全球的统一:

二、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构的由社会内部发展所决定的、与民族国家相分离的社会世界,最终被沃勒斯坦 (参见1974 ff.)的理论构想所打破。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跨国融合、国家边界划分和具有重要作用的商业空间所产生的结果,其中所有的企业、社会、政府、阶级和个人都进行分工。沃勒斯坦发现,这样的世界体系在16世纪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行为而产生,并且此后不断拓展其商业空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类似,沃勒斯坦也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在自我产生的矛盾中建立起来的(参见Wallerstein, 1998, p.315)。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也影响社会文化领域。一方面,这个体系中存在差异,政治和经济按照自身规律、自身逻辑和自己的时限运行;另一方面,每种传播和贸易关系都有其特色,对此沃勒斯坦认为:
此外,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被认为是本体自主的(ontologically autonomous),并且拥有不同的逻辑。然而这只是其推崇者对该系统的自说自话……从表面上看,机构自身构造的复杂性具有相似性(Wallerstein, 1998, p.307/308)。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五种不同的基本要素组成:沃勒斯坦首先用“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这个词来形容经济、产品和销售环节,以及经济财富的创造、交换和储存过程中,让所有要素都具有销售能力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只是经济体系中的第一步,沃勒斯坦仍然在低价销售原则(Vermarktungsprinzips)的结果和渗入过程中看到了(新的)世界体系的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件事物都被推动进入商品化进程中,这个推力在20世纪末已经达到了之前的历史系统无法想象的高度。用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分娩的商品化的时代(Wallerstein, 1998, p.308)。
据此观点,不久前Hardt和Negri (参见2002, p.37 ff.)所描述的“生物力(Biomacht)”就是以世界体系为基础而产生的,不仅仅个人或者他们的意识,就连他们的身体也适用于低价销售。正如吉奥乔·阿甘本(Agamben, 2003, p.47)所言,身体的商业化让人们失去了个性中那个最后能够衡量——以至能够自我启蒙——人类仍然所具有反抗能力的宝藏:
人的身体的商品化尽管服从于大众化和交换价值的铁律,但似乎也同时从千年来标记在人们身体上的不可言说性(ineffability)中救出了身体。从生物命运和个体传记的双重锁链中解放出来的身体,告别了悲惨之身体那不善言辞的哭喊,也告别了喜剧之身体那暗哑的沉默,因此第一次显现出完美的交流和完整的表达(Agamben, 2003, p.47)。
沃勒斯坦所划分的世界体系的第二个基本要素为“劳动控制模式的多样性”(multiplicity of modes of labor control),这使得不同的控制机制成为可能。一方面雇佣劳动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全球的生产活动方式中大部分不仅仅只是雇佣劳动。沃勒斯坦在其中发现了控制和压迫的工具:“维持多元的劳动控制(因而也是劳动报酬)模式创造了固有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工人们不断增长的补偿要求得以抑制。”(Wallerstein, 1998, p.308)

沃勒斯坦根据资本体系在距离上的远近,将世界区域划分为中心和边缘地带:“中心/边缘的矛盾指垄断单位和竞争单位之间的关系,包括高利润/低利润、高工资/低工资的矛盾。”(Wallerstein, 1998, p.310)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并保证资本积累(政治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允许的中心建立了起来,而边缘地区则相互竞争以获利。从这点上讲,世界范围内的全体工人阶级产生了差异:
不平等交易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政治规则产生的结果,这使得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比劳动力的流动更容易跨越政治边界,因此也保证了剩余价值从一位所有者向另一位所有者转换(那些处于中心区域的垄断活动)(Wallerstein, 1998, p.310)。
市场是世界体系的最后一个要素。沃勒斯坦同样将这一概念进行了中心和边缘的区分:用来区分市场和反市场(Gegenmarkt)。沃勒斯坦将物品、服务和劳动力的交换看做是通过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对市场所做的补充,这些利益会阻止市场力量的全面展开。其背后隐藏是资产阶级自己内部的竞争关系,以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对立关系。
国家和国与国之间立刻并同时为巨大的积累和持续的危险建构了一个壁垒。国家可以成为首要捕食者;没有一个捕食者在历史上可以像皇帝那样如此有效地凌驾于一个再分配之上。随着现代社会中技术效率的不断提高,任何用来再创造这样一个政治结构的事物,都将成为对无止境资本积累的惩罚(Wallerstein, 1998, p.311)。
政治体系自身的逻辑因而是不可见的。其中,政治能够引导什么样的非经济利益来设置市场壁垒是完全不清晰的。对资本积累过程独有的关注因而也可以成为对世界体系论的核心批判点。划分每个民族国家之间边界的理念因此产生了,而其中每种社会秩序和机构的建立,因此也被看作是用来保证资本无限积累的工具。基于此,沃勒斯坦(1998, p.315)将这些区别度最高的现象归纳为“全球文化”(Geokultur):
全球文化的建构涉及在知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已经在现代科学成为道德主导的情况下,被赋予了一种本体论的地位,成为分析话语的唯一反应方式(reactional form of analytical discourse)。
三、 流动性: 阶级意识和个人化
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蓝图的预测能力取决于阶级矛盾的发展、尖锐化和最终的压迫。根据批判理论,阶级意识(Klassenbewusstsein)的发展——从统治阶级的各方面来看——是绝对的。在资本主义的思维模式里,阶级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被认为是根本的,但它们的问题在于无法实现改革并始终缺少以阶级为基础的群众支持——尽管这并非不可想象。当这些不可想象的东西(一种起到阻碍作用的阶级意识)能够被进入和被解释,当“零选择的乌托邦”(Utopie der Null-Option)(Offe, 1986, p.104)不再能够掌握的时候,大众媒体的行为——从认知角度讲属于纯上层建筑的现象——在此刻就会变得相关。
假如我们要从一个社会中解放出来,方法就是进一步满足物质与文化需求——大张旗鼓地促成一个永远能够为大部分民众提供物资的社会。结果就是,我们自己必须从一个明显没有为解放提供群众基础的社会中解放出来(Adorno, 1973, p.399; 参见Marcuse, 1989, p.277)。
媒介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因此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它与对社会及根植其中的统治秩序的批判有关,另一方面它也对处于不平等的生产和统治秩序中的大众媒介进行(批判式的)分析。在这一观点中,大众媒介强化和保持了相应的行为——通过“统一消费理念的文化意识形态”(Sklair, 2002, p.119),并且通常站在公众的对立面:媒体已经报道了事实本身的、应该的或者能够成为的样子,它生产出了可控制的传播来满足公众对可信的信息、解释说明和娱乐的需求,并且为自己的再生产而制造了假需求。

文化与意识工业的总体后果是反启蒙的。从这点上看,我们必须严格考虑,大众媒体究竟能够以及应该做什么(应然)。在民主制度中,大众媒体扮演着与事实相反的、按规定行事的角色,试图通过对不合法的生产和统治行为进行解释,来通过全球化标准的严格检定:
大众媒体应该成为被启蒙公众的代表,这是以公众具有学习能力和批判能力为前提和要求的,这些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它应该和司法机构一样,独立于政治和社会领域并受到保护;它应该要求自己独立于党派,并接受公众的建议,反对和来自政治批判的强烈干预,以及合法化约束。因此媒介权力应该是中立的,并且应该在政治相关的出版行为中,排除行政或社会权力的影响(Habermas, 1992, p.457)。
这一论断试图从规范的角度来分析新闻行业(参见 Baum, 1994)。这类新闻行业的集中化进程在早些时候已经被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学者批判(参见Renger, 2003),其关注传播供给(例如娱乐)如何推销日常和流行文化,以致新闻和娱乐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参见Lünenborg, 2007)。从这个角度上看,批判理论对新闻的关注并非没有理由:
诚然,批判传播学派的学者需要坦诚地将新闻提升到话语形式的首要位置上来。它确实需要被提升,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新闻根本不可能不在政治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但没有其他形式的传播也是不行的(McChesney, 1994, p.344)。

媒体企业收集、生产和传播信息,相当于生产和销售新闻产品。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媒体产品必须服从资本的使用条件,也必须带来利润,这样才能使得更多的媒体产品具有和完善其企业的经济基础(Westerbarkey, 1991, p.183)。
根据上述分析,Hardt和Negri(2004)指出传播(以及公共舆论)并不能成为被启蒙的公众的、具有优先地位的代表,并且应该将其理解为多次受到经济权力影响的冲突领域:
公共舆论不是一种代表模式或者一种现代的、技术上的或者统计上的代表的替代物,而是一种民主政体的主体。公共舆论是一个根据权力关系而定义的冲突领域,我们能够并且必须通过交流、文化产品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生物政治产品,政治性地参与其中。在这个公共舆论的领域里并非所有参与者都能公平竞争,他们的处境完全不同,因为媒体主要由大企业控制(Hardt & Negri, 2004, p.292)。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可能会使一种理性的公开讨论变得无效,因为这种讨论并非来自经过统治阶级(党派、企业、政客)行政授权的意见或者最终的决定(参见Habermas, 1990, p.359; 1992, 454 ff.)。此外,Prokop (2002, p.403)还给出了更强烈的批判:“媒介中的真实只是占垄断地位的跨国媒体寡头所给出的真实。”大众媒体中的公众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被二次异化,而且在二次异化中通过忽略与补充受到损害。一种系统上的损害发生于合法化的集体需求(legitime Kollektivbedürfnisse)中, 这种需求是反不平等的统治和生产秩序的,是(老旧的)个人消费兴趣所反对的(参见Warner, 1992, p.385 ff.)。从这点上讲,大众媒体所担心的是,自己是否能参与到商品世界中来购买权力和统治行为。Hagen (2003, p.56 f.)由此提出:“从社会心理上讲,商品世界的恋物欲是大众知觉的倒退”,以此来反对那些忽略大众和阶级意识的理论。
Hagen的观点也抛出一个问题:大众媒体的应然和实然之间的矛盾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它作为一种传播中介的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而存在。这个推论在批判(媒介)理论中被看作一种理论建构技术,因为社会领域并没有预见到它自身回避了经济问题。
相反的是,在经验研究中适合的,在规范式和理论研究中反而不适合。对此Sklair (2002)给出了一个例子,由于全球化进程,四种跨国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中的一种正在形成。Sklair (参见2002, p.119 f.)分别列举了跨国资产阶级的企业管理以及与之相应的本地社会(企业的分支)、官僚、全球化国家的政客(国家的分支)、全球化的专业人士(技术分支)、贸易和媒体(消费分支)。这样一个如此庞大的资产阶级能够创造什么样的利润,这个问题(迫不得已)是没有答案的。“跨国资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创造各种能够在全球和各个地区中增加其自身利益和整个系统的利益的条件。”(Sklair, 2002, p.122)
基于这样的背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让媒介真实成为跨国媒体寡头资本主义首要的真实(参见Prokop, 2002)。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跨国企业也就占有垄断地位,而跨国的和地区的利益也就产生了矛盾。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进程也就被政治化了,“因为全球化的组织和筹划是允许企业及其协会存在的,民主化组织下的资本主义的贸易权力也因此重新开始产生作用”(Beck, 1997, p.14)。同样,经济部分和整个系统也就被贸易权力所驯化,能够从沃勒斯坦所定义的矛盾市场(Gegenmarkt)中获利。Sklair也建议,属于跨国资产阶级的政客,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人们说,政客不仅仅从整体(地区的、州的、联邦的和欧盟层面)的不同层面上联系在一起,他们也同时在创造同一种相同形式的利益。而政治内的区别——从保守和激进的角度讲——在不同层面上差别不大。
起初在理论层面上所构想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强大和弱小之间的矛盾对立也因此开始融合了。从资本角度来看,强大的(全球化的)超级结构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形成矛盾市场的。马克思、恩格斯预测性的阶级意识并没有与至高无上的权力(Allgewalt)相抗衡,并且被压迫的大众并没有因为变得个体化、碎片化和断裂化而面目全非:
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印象越来越深刻,处在一个危险的世界范围之中的一股“全球化”的权力已经兴起,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果很严重,也由此抛出一个问题,难道分析它是无意义的,而与之为敌则更是荒谬和疯狂的,所以从这样一个在历史中形成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中被解放出来,只是白日梦吗?(Forrester, 2001, p.5)
批判理论只能展现出理论内在固有的一面,以及因个人消费意愿所形成的文化和意识工业的集体利益下所形成的一面。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在个人主义(参见 Beck, 1986, p.121 ff.)和公共空间(参见Sennett, 1991)消失的背后,最终是资本利益以及人们已经熟知的马克思所定义的痛苦的熔炉。

通过对集体意义模式和行为模式的流动性的本质思考,鲍曼认为批判理论不再是时空上延续不断的,而是在疆界以外不受管辖的和受时间严格控制的。

社会的权力结构同样也在改变。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权力都已经变成一种治外法权(exterritorial)了:

那些能和不能行使权力的,都会因为治外法权和时间限制而全然不同。一些行为会因为超出时间而完全失效,而另一些则不止一次地成为均衡补偿。鉴于集体行为和意义模式的流动性,一种反对鲍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惊厥与危机的观点出现了。批判理论——以及鲍曼对它的发展演变——因此不得不在个人化进程中目睹社会阶层的消失,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斗争史的消失:“如果我们再次用阶级概念思考人类命运,我们必须承认社会阶级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小资产阶级,而所有阶级都在其中产生。”(Agamben, 2003, p.89) 当阿多诺亲眼目睹选择作出的时候——无论选择的是个人的终结抑或是个人没有终结——都同样令人沮丧的(参见Thies, 1997, p.116 ff.),阿甘本则把这个选择不仅仅当作决定性的,而且还把它与一种新的(启蒙的)不可中介性的希望联系起来:
因为如果不是继续在一个已经不合适和毫无目的的个人化形式下成功地搜寻一个合适的认同,人们就能成功地在这种不合适的归属中,把合适的存在——不是当作一种认同和一种个人财产,而是当作一种非认同的独特性,一种普遍和彻底暴露的独特性——如果人们能够不在这样或那样的特定的传记中做到如此存在(So-Sein),而仅仅是以他们个人的外在和脸庞如此地存在着(So zu sein),他们就会首次进入一个无预设、无主体也不会无法沟通的共通体(Agamben, 2003, p.61)。
如果没有条件,这样的共同体是无法实现的。人类通过社会所赋予的创造力去想象自身的外在,这是人类最根本的存在条件。这类观点区分了传播和意识,在系统论(Systemtheorie)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参见Luhmann, 1995a, 1995b)
四、 世界社会
社会秩序的实现需要什么条件这个问题,正是功能和结构系统论的出发点(参见Luhmann, 1988)。此外,这一理论构思也讨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的优先地位,社会秩序是不可退转的。那些属于非优先经济现象的(如大众媒体、科学)也会在某些条件下成为经济的附属物(作为上层建筑现象或者突出的全球文化中的经济秩序的一部分)。至今仍在讨论的理论构思体现出了非常强的时代性(Akteursorientierung)。当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进行交易或者交流的时候,个人、阶级和分层以及从中产生实施交易与交换的机构也就随之产生了。
系统论认为,上述观点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世界体系由基于传播之上的高度相区别的系统构成(参加Luhmann, 1997, p.145 ff.)。系统论应该让社会秩序的实现需要什么条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不那么抽象和笼统:被关注的不应是“什么”(物质领域,Gegenstandbereich)的问题,而人们应该去询问“怎样”(物质领域如何出现)的问题。社会秩序的建构——无论是为了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物质领域的交易——总是通过减少复杂度和系统建构来实现的:“社会系统具有把握和降低复杂度的功能。”(参见Luhmann, 1988, p.236)系统建构意味着,按照无边界的但必须做出选择(被迫选择)的原则,划定一个可能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减低复杂性。
有效的传播在当今社会是通过所谓的功能系统(Funktionssysteme)进行的。功能系统,诸如政治、经济或者科学,都是现代的、由劳动组织而成的社会通过对意义(Sinn)的特殊传播来保障其持续发展的,并且这个过程中并不包括社会性的意义媒体(Sinnmedium)所带来的特定社会功能——诸如真实、权力、金钱或者爱情——都属于象征性一般媒介(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 Kommunikationsmedien,参见Luhmann, 1975)。它将每个意义的结构根据社会期望进行压缩,由此来展现人们观念中所理解的意义,也划分出功能系统中能够自己建构真实的社会意义范围。因为系统的范围也是意义的范围,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真实建构之间也是相互不透明和不一致的,而它们在相互转换之间也会造成意义的损失:正如Helmut Willke (1993, p.55)所言,“功能分化(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将社会分成四部分,各部分自治,而它们的运行机制和分离趋势则带来了社会的统一(Einheit)和整合(Integration)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像人们所推测的那样成为社会的缺点,反而产生了其独特的效用和效率。
功能相区别的社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功运作的,生产能力由越新和越不同的传播组成,并且能够不断消耗,就越能被扩大。正如Nassehi (1993, p.257)所言,“通过系统分化,不同的东西同时出现的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经发生了,不同系统的同时性也使得不同东西的同时性成为可能”(参见Luhmann, 1990, p.95 ff.)。社会因此具有高度复杂性:不仅仅在物质和社会层面,就连时间层面也是。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社会总是交流性的,并且对于每个组织或者机构来说,国家被符号化了,这也意味着我们与“当代社会”(Gesellschaft der Gegenwarten)有关。世界社会(Weltgesellschaft)的时间限制从这点上讲,仅仅意味着最外层的传播边界之间存在着彼此联通的沟通交往。这些沟通交往处于功能不同的世界体系中,同样地,每种传播也通过边界划分而区分开来。根据系统理论所进行的观察,每时每刻都只能讨论一个社会当下(Gegenwart einer Gesellschaf)的意义,因为人们所称的“全球化”只能在一个原则下来比较世界社会的不同领域:这就是功能分化原则(das Prinzip der funktionalen Differenzierung)。
社会系统以及世界社会的功能边界由此划分——这并不是沃勒斯坦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系统所产生的结果——也不是由民族国家设立的政治边界(参见Richter, 1996; Albert, 2002)。此外,功能分化正好削弱了与国家相对的政治系统(反映了民族国家原则)的权威。无论涉及生态的、经济的、科学的危机,它都能够产生这种削弱作用——特别是通过新闻记者的异己观察(journalistische Fremdbeobachtung, 参见Kohring et al., 1996)——只有少数的人能够让这些破碎的国家原则保持开放。而这些少数的人正是世界系统延伸的代表,批判理论或者一个新帝国的辩护者认为,系统论和其他用来区别不同社会的原则在世界化背景下是不合适的:
如果在不同社会中选择的话,终究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标准能让人满意。制定这样一个标准所面临的,要么是统一的准则,要么是各自的文化;要么是国家的,更不用说地区的边界,要么总是对全民都适用的完美准则。而每个可能的概念,都在嘲笑全球化日常的经验现实(Nassehi, 2003, p.194)。
功能系统的组织和运作离不开社会的观察行为:首先,在功能系统中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不再是等级森严的,它必须是反等级的(heterarchisch,参见Fuchs.1992)。人们可以观察到,经济系统本身存在等级秩序,并和其发展出的新的亚系统存在区别,但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在政治、法律和科学领域同样存在。从这个理论出发,大众媒体成为政治或者经济系统的附属或万用工具。其次,功能分化形式占优势的社会的特色是“架设穹顶”(überwölbenden Gesamtsinn,Nassehi, 1997, p.118):每个与功能系统相对应的观察都是在多种观察中的一种,第一眼看上去要么更坏要么更好,而这都是从他者角度所感知到的。因此,现代社会其实是多角度的。而经济的优先地位,无论是否伴随文化——从这个理论意义上是不成立的。
五、 世界传播: 新闻、娱乐和公关
异体的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 von Verschiedenem)是现代社会的特殊结构,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会给社会自身带来问题:功能分化一方面增加了相互依赖,导致以功能系统为前提的整个系统整合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也让其他功能在其他地方实现。这样的整合是脆弱的,因为它担负着冗余减少的危机(Risiko des Redundanzverzichts,参见Luhmann, 1990, p.341)。此外,功能系统的分化也具有了实现可能,“因为唯一的功能系统不用考虑相互之间不断变化的影响——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自身的动力具有相似性(Indifferenzen)”(Luhmann, 1995c, p.86)。
为了实现其功能,每个功能系统都必须将系统内部结构化。因此有组织的执行角色(执行系统,Leistungssystemen)几乎必然是分化的。在功能系统中,传播和新闻及娱乐一起作为执行系统发生作用(参见Görke, 2007)。卢曼 (1996)也认为公关/广告属于公共传播(öffentlicher Kommunikation)的纲要领域(Programmbereich,参见Westerbarkey, 2001)。通过执行系统的分化,新闻和娱乐将存在一段时间,或然性(Wahrscheinlichkeit)也会明显提高,而通过公共的和新闻的观察,复杂性能带来益处并且链接沟通也会被带动。传播的功能不仅仅服务于个别对象,而且还必须要确保其他群体。公共传播通过一般传播媒介的现实性(Aktualität)来获得同一性(Identität)。因此,新闻由符码(Code)的优先值(+正值),而娱乐则通过公共传播的反省值(Reflexionswert,-负值)来指引。新闻和娱乐在媒介的现实性中都发挥着形塑者的功能,而且可以同时通过分化(正负值)的统一区别开来。社会的同步需求首先让功能系统的传播成为可能,人们可以在新闻的现实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娱乐的可能性的建构中,发现它们之间在专业上的类似之处(参见Görke, 2002, p.73 ff.)。在新闻现实性的构建中,(世界)社会开始同步:物质的和社会的,都是暂时的。娱乐通过降低复杂性来生产传播内容的意义(参见Görke, 2002)。
新闻和娱乐之间的区别在于两个系统的纲要层面。作为纲要(Programme),需要展现出系统中符码值(Codewerte)的规定(详细说明)所允许的差别(参见Luhmann, 1996, p.129)。首先通过符码和纲要的分化,系统在操作性闭合的同时向刺激开放,这使得上述差别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参见Luhmann, 1988, p.91)。新闻和娱乐的传播早就具有了媒介的现实性。特别是对娱乐具有特殊意义的系统正负的现实性,能够而且必须自我改变。总体来说:社会越复杂,新闻和娱乐内部的决定和纲要的结构也就越复杂。人们因此只能在选择纲要(Selektionsprogrammen)和表现纲要(Darstellungsprogrammen)之间进行区分。分化可以被重新用来展现什么样的纲要元素是被选择、复制和改变的,这样才能进一步开发某个系统构建(详见Görke, 2002)。
新闻——娱乐适用其他原则——正是详细说明正负现实性的差别中的复杂的外部边缘。这种形式的复杂性是强迫选择的结果。新闻所处的执行系统中永远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实性也一直在建构其他东西。复制和改变正是那种机制,它能够通过时间来区分执行系统内部新闻自己的分系统纲要。人们也清楚地知道“高质量新闻”(Qualitätsjournalismus)和“小报新闻”(Boulevardjournalismus)之间的区别,这些概念也是新闻现实构建的偶连特色。同样,人们也想通过强调“地方新闻”和“全国新闻”的区别,来观察纲要层面的再建构。
新闻和娱乐的区别产生于组织系统(Organisationssysteme)层面,而组织系统在这两个公共传播的执行系统中分化。组织通常被定义为“来自约束性决定(Entscheidungen)的、在有效传播基础上的自我生产系统”(Luhmann, 1997, p.830)。新闻组织(编辑部门、管理部门、出版社、通讯社)对信息,以及传播广度会将受媒介技术影响的报道内容进行选择。新闻组织处于,并且产生于功能分化的社会进程中那个相互增强的点(wechselseitige Steigerungsverhältnis)上。经济、政治和传播的功能系统决定着组织系统形式的产生和推广程度。而组织系统形式的结果,则取决于组织自身除了传播媒介的现实性之外,是否还能顾及其他要求。换句话说,组织的功能特权(Funktionsprimat)可以与其他功能相妥协,例如与经济需求(如生产成本)或者法律上的考虑(如人格权的意识)相结合(参见Luhmann, 1997, p.841f.; Görke, 2002, p.78 ff.; 2007)。新闻组织的偶连首先发生在被报道的事实情况的多样性中,其次发生在功能特权之下的妥协或者不妥协的多样性中。这就要求作为组织约束性决定纲要的组织准则能够发展和流传下来。产生于纲要层面的新闻和娱乐的区别,也说明了能够将他者作为己用的不同系统形式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因此,被迫不同的选择和变化也从侧面说明了跨国媒体企业缺乏选择性和不合理性。
六、 结语
世界体系理念以一个客观的、纯粹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执行理论的形象,展现出了它作为理想的候补者的一面,因为社会世界的边缘地带具有一个难以逾越的物理世界的边界——使得全球或者地球——产生分裂(参见Stichweh, 2000b, p.232)。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讨论其实造成了第二次边界划分,在这一划分中世界被看作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成为一种以理论为导向的最终发展趋势(阶级对立的压迫),这些论断具有目的论的(teleologisch)性质。它们描绘了世界体系(在想象中)是什么样的,由于实现了对世界体系的描述,人们便可以放弃通过观察来绘制的理论图形。阶级的归属,举例来说,是由统治阶级的生产行为来决定的,但并非人们自身是否意识到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并由此做出相应的传播行为的问题。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世界社会反对给所有互相开放的传播行为之间设立外部边界,而物理边界也并不是被迫相互协调的。这一理论所描述的社会,一方面高度分工组织,从而保证功能上彼此不透明和不兼容的独立生产子系统能够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它也通过功能分化的统治秩序原则来保持统一。因此系统论所描述的并不是“实然”状态,而是来自观察的观察(Beobachtung von Beobachtung),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测量评估世界社会的问题怎么解决(参见Görke, 2008a)。由此,占垄断地位的全球结构原则并不是经济,而是相互关联功能系统。所以系统论的学者认为世界并不是由经济的主差别(Leitunter-scheidungen),而是由为数众多的分化的意义领域(Sinnprovinzen)的来决定的(Haben/Nicht Haben, Markt/Gegenmarkt etc.)。而从经济的、科学的、法律的或者公共的观察角度来说,传播也并非将世界分裂而是融合。世界社会的角度是多元的,相应地,人们也很难预言世界社会将怎样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理论建构所考虑的是将各个系统聚集起来的可能性。功能分化原则因此并不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存在明确(Seinsgewissheit)。更多地应该看到,功能分化只有在社会变革有效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
只有当物理和社会世界边界的理论构建达到很高(或者很低)层次的时候,人们才能在理论设计中测量估计意义、大众媒体以及传播。理论认为世界系统因为经济结构和差别而占优势,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大众媒体(传播)。它要么成为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要么成为系统的附属,并且负有在世界系统内负有保证资本传播顺利运作的重任。大众媒体在分析中通常被当成是(经济的)媒体企业,以及上层建筑的现象或者是反启蒙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媒介和文化工业。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人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分析媒体中的分问题——同时传播也具有一部分功能系统的内在价值(Eigenwerte)、原时性(Eigenzeitlichkeit)和固有理性(Eigenrationalität)。
新闻和娱乐所特有的现实性分类(Aktualitätsorientierung)是和公共传播的固有意义(Eigensinn)紧密联系的,它测量和展现人们会对特定意义媒体(正负现实性)中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同步需求)有反应,这些媒体能反映出大多数不合适的社会问题(发布、纠正、教育、寻求真相)。这样一种分析认为功能系统中的传播——由于社会分系统无法掩藏的相互依赖行为——具有相对较高的测量评估意义。因此,没有一个功能良好的分系统的话,世界体系是无法运行的。同样,人们也可以分析公共传播中与现实性分类相关的组织和纲要的内部分化(如报道形式和新闻范本),这些已经完成的分化也说明全球化并非一个全新的现象。此外,顺利运作的系统功能也能防止系统规则失效。现在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影响,以及应对方法,都让人们迫切地想知道系统研究者是怎样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的。假如马克思和卢曼之间关于金融危机的争论能够最终产生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证的话,那么我对这个结论保持质疑。真实的情况是,不同的理论的存在,也只是让其他理论同样具有它们(理论条件下)的盲点而已。
注释
① 译文参照中央编译局(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68页。
② 同上,第468-469页。
③ 译文参照中央编译局(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2页。
④ 译文参照中央编译局(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69页。
⑤ 译文参照中央编译局(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0页。
⑥ 同上,第93页。
⑦ 译文参照中央编译局(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70-471页。
⑧ 译文参照中央编译局(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88页,德文版语句顺序与中文版有异,这里根据德文版调整了中文句子顺序。
⑨ 译文参照中央编译局(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88页。
⑩ 即cartel,垄断的一种方式——译者注。

















Adorno, T.W. (1973).NegativeDialektik. Frankfurt: Suhrkamp.
Agamben, G. (2003).DiekommendeGemeinschaft. Berlin: Merve.
Albert, M. (2002).ZurPolitikderWeltgesellschaft.IdentitätundRechtimkontextinternationalerVergesellschaftung. Weilerswist: Velbrück.
Baum, A. (1994).JournalistischesHandeln:EinekommunikationstheoretischbegründeteKritikderJournalismusforschung. Opl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Bauman, Z. (2003).FlüchtigeModerne.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Beck, U. (1986).Risikogesellschaft:AufdemWegineineandereModerne. Frankfurt: Suhrkamp.
Beck, U. (1997).WasistGlobalisierung? Frankfurt: Suhrkamp.Beck, U. (2002). Macht und Gegenmacht im globalen Zeitalter: Neue weltpolitische Ökonomie.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Chossudovsky, M. (2002).Globalbrutal.DerentfesselteWelthandel,dieArmut,derKrieg. Frankfurt: Zweitausendeins. Fetscher, I. (1983).DerMarxismus.SeineGeschichteinDokumenten.Philosophie,Ideologie, Ökonomie,Soziologie,Politik. München, Zürich: R. Piper.
Forrester, V. (2001).DieDiktaturdesProfits. München: Hanser.
Fuchs, P. (1992).DieErreichbarkeitderGesellschaft:ZurKonstruktionundImaginationgesellschaftlicherEinheit.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Gellner, E. (1999).Nationalismus:KulturundMacht. Berlin: Siedler.
Görke, A. (1999).RisikojournalismusundRisikogesellschaft:SondierungundTheorieentwurf. Opl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Görke, A. (2002). Journalismus und Öffentlichkeit als Funktionssystem. In Scholl, A. (Ed.),SystemtheorieundKonstruktivismusinder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pp.69-90). Konstanz: Uvk Verlags GmbH.
Görke, A. (2003). Unterhaltung als Leistungssystem öffentlicher Kommunikation: Ein systemtheoretischer Entwurf. In Schmidt, S.J., Westerbarkey, J., & Zurstiege, G. (Eds.),A/effektiveKommunikation:UnterhaltungundWerbung(pp.53-74). Münster: Lit.
Görke, A. (2007). Argwöhnisch beäugt: Interrelationen zwischen Journalismus und Unterhaltung. In Scholl, A., Renger, R., & Blöbaum, B. (Eds.),JournalismusundUnterhaltung:TheoretischeAnsätzeundempirischeBefunde(pp.87-115).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Görke, A. (2008). Die Gleichzeitigkeit des Verschiedenen: Nation und Weltgesellschaft als Referenzgrößen des Journalismus. In Pörksen, B., Loosen, W., & Scholl, A. (Eds.),ParadoxiendesJournalismus:Theorie-Empirie-Praxis.FestschriftfürSiegfriedWeischenberg(pp.269-295).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Görke, A. & Ruhrmann, G. (2003). Publ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facts and fi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etic risk.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12(3), 229-241.
Habermas, J. (1990).StrukturwandelderÖffentlichkeit.UntersuchungenzueinerKategoriederbürgerlichen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Habermas, J. (1992).FaktizitätundGeltung:BeiträgezurDiskurstheoriedesRechtsunddesdemokratischenRechtsstaats. Frankfurt: Suhrkamp. Hagen, W. (2003).Gegenwartsvergessenheit:Lazarsfeld,Adorno,Innis,Luhmann. Berlin: Merve.
Hardt, M. & Negri, A. (2002).Empire.DieneueWeltordnung. Frankfurt: Campus Fachbuch.
Hardt, M. & Negri, A. (2004).Multitude.KriegundDemokratieimEmpire.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Horkheimer, M. & Adorno, T.W. (2002). Kulturindustrie. Aufklärung als Massenbetrug. InDialektikderAufklärung.PhilosophischeFragmente(pp.128-176). Frankfurt: Fischer.
Kausch, M. (1988).KulturindustrieundPopulärkultur:KritischeTheoriederMassenmedien.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Knoche, M. (2001). Kapitalisierung der Medienindustrie aus politökonomischer Perspektive.Medienund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49, 177-194. doi:10.5771/1615-634x-2001-2-177.Kohring, M., Görke, A. & Ruhrmann, G. (1996). Konflikte, Kriege, Katastrophen: Zur Funktion internationaler Krisenkommunikation. In Meckel, M., & Kriener, M. (Eds.),InternationaleKommunikation:EineEinführung(pp.283-298). Opl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Lenin, W.I. (1946).DerImperialismusalshöchstesStadiumdesKapitalismus. Berlin: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
Luhmann, N. (1975). Einführende Bemerkungen zu einer Theorie 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r Kommunikationsmedien. InSoziologischeAufklärung2:AufsätzezurTheoriederGesellschaft(pp.170-192).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Luhmann, N. (1988).SozialeSysteme.GrundrißeinerallgemeinenTheorie. Frankfurt: Suhrkamp.
Luhmann, N. (1990).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Luhmann, N. (1995a). Bewußtsein und Kommunikation. InSoziologischeAufklärung6:DieSoziologieundderMensch(pp.37-54). Opl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Luhmann, N. (1995b). Was ist Kommunikation? InSoziologischeAufklärung6:DieSoziologieundderMensch(pp.113-124). Opl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Luhmann, N. (1995c). Die Behandlung von Irritationen: Abweichung oder Neuheit? InGesellschaftsstrukturundSemantik.StudienzurWissenssoziologiedermodernenGesellschaft.Band4 (pp.55-100).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Luhmann, N. (1996).DieRealitätderMassenmedien(2nd Ed.).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Luhmann, N. (1997).DieGesellschaftder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Lünenborg, M. (2007). Unterhaltung als Journalismus—Journalismus als Unterhaltung. Theoretische überlegungen zur überwindung einer unangemessenen Dichotomie. In Scholl, A., Renger, R. & Blöbaum, B. (Eds.),JournalismusundUnterhaltung:TheoretischeAnsätzeundempirischeBefunde(pp.67-85).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Luxemburg, R. (1921).DieAkkumulationdesKapitals.EinBetragzurökonomischenErklärungdesImperialismus. Leipzig: Frankes Verlag.
Marcuse, H. (1989). Liberation from the affluent society. In S. Bronner & D. Kellner (Eds.),Criticaltheoryandsociety:Areader(pp.276-288).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Marcuse, H. (1994).DereindimensionaleMensch.StudienzurIdeologiederfortgeschrittenenIndustriegesellschaft. München: DTV. Marx, K. & Engels, F. (1953).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 Berlin: Werke. Marx, K. & Engels, F. (1986).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 Ditzingen: Reclam.
McChesney, R.W. (1994).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t the crossroads. In Levy, M.R. & Gurevitch, M. (Eds.),Definingmediastudies:Reflectionsonthefutureofthefield(pp.340-34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GA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1975). Gesamtausgabe. 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 ZK der KPS und vom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 Berlin. Nassehi, A. (1993).DieZeitderGesellschaft.AufdemWegzueinersoziologischenTheoriederZeit.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Nassehi, A. (1997). Inklusion, Exklusion, Integration, Desintegration. Die Theorie funktionaler Differenzierung und die Desintegrationsthese. In Heitmeyer, W. (Ed.),WashaltdieGesellschaftzusammen?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AufdemWegvonderKonsens-zurKonfliktgesellschaft(pp.113-148). Frankfurt: Suhrkamp.
Nassehi, A. (2003).GeschlossenheitundOffenheit.StudienzurTheoriedermodernen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
Offe, C. (1986).DieUtopiederNull-Option.ModernitätundModernisierungalspolitischeGütekriterien. Bielefeld. Paetzel, U. (2001).KunstundKulturindustriebeiAdornoundHabermas.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Prokop, D. (2002). Die Realität des Medien-Kapitalismus. In Hepp, A., & Löffelholz, M. (Ed.),GrundlagentextezurtranskulturellenKommunikation(pp.403-420). Konstanz: Utb.
Renger, R. (2003). Kulturtheorie der Medien. In Weber, S. (Ed.),TheorienderMedien(pp.154-179). Konstanz: Utb.
Renner, K. (1917). 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 über offene Problem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ud praktischen Sozialismus in und nach dem Weltkriegn. Stuttgart. Richter, D. (1996).NationalsForm.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Robes, J. (1990).DievergesseneTheorie:HistorischerMaterialismusundgesellschaftlicheKommunikation. Stuttgart: Silberburg.
Sennett, R. (1991).VerfallundEndedesöffentlichenLebens.DieTyranneiderIntimität. Frankfurt: Fischer.
Sklair, L. (2002). Medienforschung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In Hepp, A., & Löffelholz, M. (Eds.),GrundlagentextezurtranskulturellenKommunikation(pp.118-139). Konstanz: Utb.
Stichweh, R. (2000b). Konstruktivismus und die Theorie der Weltgesellschaft. In Stichweh, R. (Ed.),DieWeltgesellschaft:SoziologischeAnalysen(pp.232-244).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Thies, C. (1997).DieKrisedesIndividuums:ZurKritikderModernebeiAdornoundGehlen. Reinbek: Rowohlts Enzyklopadie.
Wallerstein, I. (1974).Themodernworld-systemI:CapitalistagricultureandtheoriginsoftheEuropeanworld-economyinthesixteenth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Wallerstein, I. (1998).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 Preyer, G. (Ed.),StrukturelleEvolutionunddasWeltsystem.Theorien,SozialstrukturundevolutionäreEntwicklungen(pp.305-315). Frankfurt.
Warner, M. (1992). The mass public and the mass subject. In Calhoun, C. (Ed.),HabermasandthePublicSphere(pp.377-401). Cambridge: MIT Press.
Westerbarkey, J. (1991).DasGeheimnis:ZurfunktionalenAmbivalenzvonKommunikationsstrukturen. Opl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Westerbarkey, J. (1995). Journalismus und Öffentlichkeit. Aspekte publizistischer Interdependenz und Interpenetration.Publizistik, 40, 152-162.
Westerbarkey, J. (2001). Propaganda-Public Relations-Reklame.Communicatiosocialis, 34(4), 438-447.Willke, H. (1993). Systemtheorie I: Grundlagen-eine Einführung in die Grundprobleme sozialer Systeme. Stuttgart, UTB.
(编辑:曹书乐)
Globalization and the Public: Markings of the Theory Discourse
Alexander Görke
(FreieUniversitätBerlin,Germany)
Globalization is emerg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ories about global society and global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ociolog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theorie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expanding of the capitalistic world system, and correspondently represent some specific perspectives. As su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ori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ur steps: (1) the global concept under the class conflicts according to Marx and Engels; (2) The notion of world system from Wallerstein; (3) Critical theories of Frankfurt School; (4) Luhmann’s system theory and the world society.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se four step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ories , I will then change my focus to the mass media,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Journalism, entertainment and PR in a globalized world.
Globalization; Public; World System; Mass Media; Frankfurt School; System Theory
1. Görke,Alexander(2009): Globalisierung und Öffentlichkeit. Wegmarken eines Theoriediskurses. In: Klaus Merten(Hrsg.): Konstruktion von Kommunikation in der Mediengesellschaft. Wiesban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pp.45-70. 本文由作者授权,从德文译为中文。
2. Alexander Görke: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3. 吴璟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