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头
田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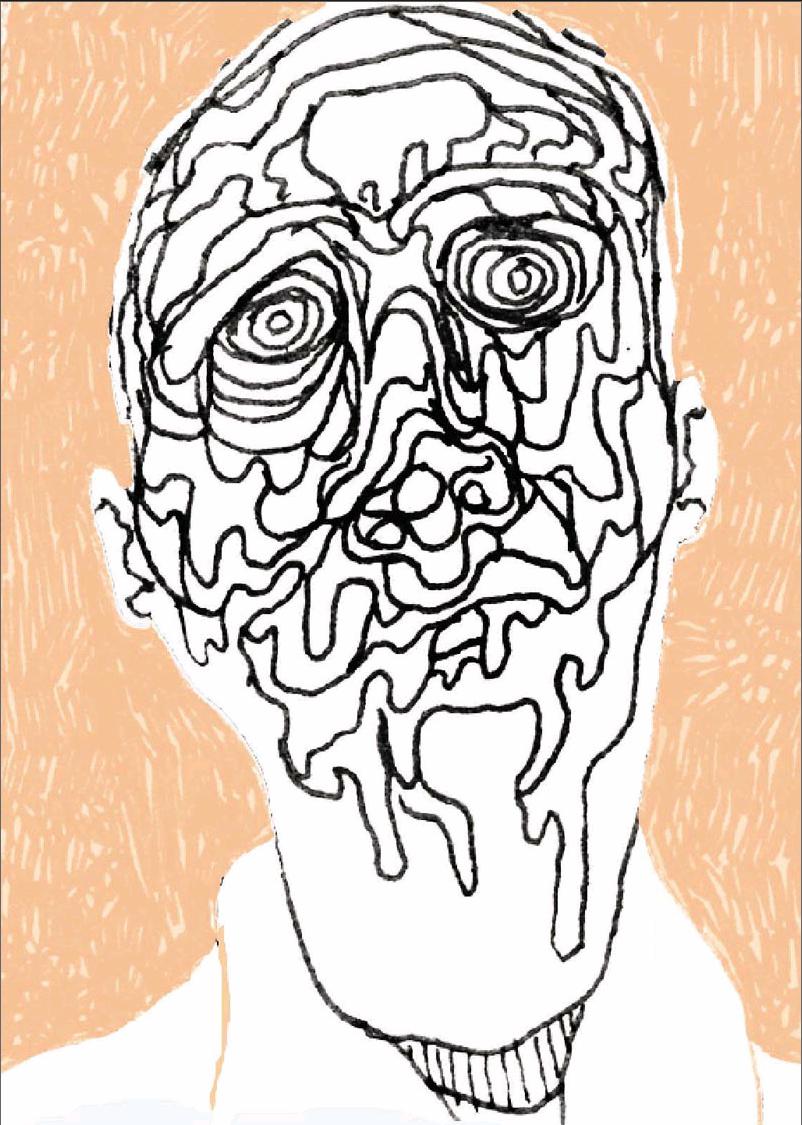
佬佬——
在山坳口,他扯起喉咙喊了几声。当地话把儿子叫佬佬。这里是儿子丢失的地方,具体讲就是从那块大岩头后面消失不见的。
回音把他的喊声传得很远,寨上人听见,都晓得他又回来了。当然他主要是喊给屋里人听的,这阵子,她不管在做什么,都会丢下手里的活计,沿着大路一路小跑迎上来,开口就问:佬佬挪得没?
挪是找的意思。
佬佬挪得没?今天照例又这样问。
其实不用问,她已经从他的脸上看出了结果。他一脸闷闷笑,那笑瞬间就要雷一样炸开。她的心不禁狂跳起来,真的?这消息和当初听说儿子失踪一样来得突然,眼前一黑差点晕倒。丈夫脚快手快一把扶住了她,顺势一揽抱紧了。他的蛮劲通过手臂传达给了她,箍得她出不得气,骨头都要被箍断了。
整整十二年前,哪月哪日哪个时辰,他都清楚地记得。那是他命中最黑暗的一天,天垮下来了,一颗铆钉扎进了他的独心,他忍着不让它生锈,每天带着锐痛去寻找儿子,这样他的信心才不至于有丝毫动摇。
逢场的日子,他一早起来看天,看出了晴朗,便决定带儿子去赶场。儿子才两岁,顽皮如小狗,起初要背,背到坳口见了大岩头来了玩性,要和父亲捉迷藏。不料这出游戏玩大了,一玩十二年。他躲在岩头后面,却让父亲钻天入地也找不到他。
岩头屹立在三岔路口,仿佛专门要制造一场人间悲剧,在那里埋伏了一万年。岩头以前在他眼里是一尊菩萨,现在成了吃人的巨兽。悔不该听儿子的话,要他离岩头远些,无非是想给自己留下足够隐身的时间。当他回到岩边时,还以为儿子就躲藏在路旁的石缝里或草丛中。他天真地逗着儿子:我看见你了,看见你了,出来吧!其实他四顾茫然,什么也没有看见。回应他的是窸窸窣窣的风和不知名的虫鸣。他一点也不着急,干脆坐下来点了一根烟,用抽烟的方式和儿子比着耐心。其他赶场的人从他跟前经过,问他怎么不走,他坦然作答:歇下气。这一歇气不要紧,注定他从此身心再也歇不下来了。他哪里晓得,他在原地死等的同时,不谙世事的儿子存心不让他找到,已经随意选择一条路越跑越远,后来肯定是落到了人贩子手里。
一声晴天霹雳把屋里人击倒了,呼天喊地要他赔儿子。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赔法,好像儿子是她一个人的。如果用他的命斢得回儿子,他当然愿意,但是这由不得他,他只能够用死也要找到儿子的誓言来安慰妻子。
若不是去找儿子,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去那么多地方,特别是那些陌生城市。想起日后路长,他在胶鞋底下套了一双草鞋,避免直接磨损鞋底。草鞋是他亲手打的,总共打了十双,剩下的随身带着,路上好斢换。他蹲在屋檐下打草鞋的时候,根根金黄色的稻草如同丝线,编织着他的梦。梦若成真,他的心就要醉了,而现在心是碎的。不时地抬头瞟一眼屋场下的水田,自然想起秋天收割谷子的事,怎么偏偏想到要多留几捆稻草,好像就是为这一天作了准备似的,真的是鬼摸了脑壳。
他就这样以一副典型的农人形象出现在城市。他走了很多地方,把所有的车票都保留下来,车票准确地记录着他的行踪。和无数城里人相遇,又擦肩而过,很少有人留意到他,当年网络上流行这个哥,那个哥,却都恰恰忽略了这个草鞋哥。他不顾别人怎么看他,只管走他的路,足迹遍及每一条街道,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人海里找人形同大海摸针,这个道理他懂,他就是要找到被他搞打落的那颗针。到底走了多少路无法计算,直到最后一双草鞋快要磨烂,他决定回一趟老家。夫妻俩分了工,妻子在屋里做事,供养他,包括他所有的花销。他想这次回去多带些盘缠,多打几双草鞋,以后多一些在外面的日子,少耽搁寻找儿子的工夫。
行走漫无边际,这样下去何時得了,他心里实在没有底。到了晚上,他无异乞丐和浪人,落宿在桥下,街头,或者废弃的工棚,脚步一旦停顿下来,心里反而空洞得如同深渊。一天早晨,他好像刚刚入睡,就被一个稚嫩的声音吵醒:爸爸,他怎么在这里过夜呢?睁开眼,只见三三两两穿着相同的小孩被大人牵着手,然后送进了旁边的大门。原来这里是一家幼儿园。他立刻振作起来,确切地说人一下子变得痴呆。他不知如何走完从起身到大门之间那几步路的,好像夜游一般没有记忆。沉重的铁门紧闭,他心里却有一扇亮窗打开,想我的儿子也肯定上幼儿园了,不在这里就在别处,以后他不必盲目乱跑了,找遍天下幼儿园不就晓得儿子下落了吗?
放学前,他夹杂在家长们中间,盼望放学时刻的到来。如果不是来接孩子,闲人没有理由来凑热闹。他两者都不是,却更有理由站在这里等待。门开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迎上前去,他反而成了碍事的人,便赶紧避让到路边旁观。他眼睛鼓鼓地在人群中搜索,希望发现他熟悉的那张脸。但是命运并没有能够让他如愿。结果,每个大人都牵着一个小人儿走了,唯独他的手上是空的。那一刻他感到天色刷地阴暗下来,天提前黑了。
公园的周末,就没有平常那么清静了,成了孩子们的天下,好像幼儿园搬到了这里。许多家长带孩子来玩耍,他也来了,而且最先到达,早早就蹲在门口守候,既是迎来又是送往。通常他是不进门的,感觉不会再有人来了,便转去另一家公园。今天的情况不同,他看见一个男孩长得很像他儿子,于是就跟随进了公园。世界上有些事情巧得很,他发现公园里竖立着一块和山坳口形状同样的岩头。更奇怪的是,男孩一下子挣脱父亲的手,直奔石头而去,嘴里喊着:捉迷藏!捉迷藏!他吓到了,曾经的一幕恍若眼前。他本能地冲上去制止那个身为父亲的男人,而又更像是制止自己:这个搞不得!千万搞不得!父子间的游戏被打断,男人疑惑地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管什么闲事,走开!他如梦初醒,才明白自己的身份,愣了半天回不过神来。
是的,儿子是人家的,城市也是人家的,关我什么事!他怏怏地回去了。
类似经历还碰到过。不是他眼睛差,而是同龄小孩子穿了同样衣服很容易混淆,不好辨别。他是想儿想疯了,恨不得有孙悟空的本事,变出一个儿子来。后来他又认错人,惹了祸,被人铲了耳光。他本来并没有那么莽撞,经过几天蹲守,细看,才认准那个小孩就是他儿子的。那几天,他不晓得是怎么过来的,整天魂不守舍地在幼儿园门口来回游荡。心里的一块石头时而落地,时而又悬了起来。儿子是找到了,这一点他感到很踏实,但是一想到他是在人家的地盘跟城里人争儿子,心里又缺少足够的底气,因为一个胆子再大的乡下人一旦进城都不免胆怯的。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在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大胆地拦住了那个男孩,并且喊了一声:佬佬!
男孩显然受到了惊吓,想转身逃走,但是被一双鹰爪般的手抓住了,固定在了原地,动不得。
他把男孩的身子扳正,自己蹲下来,扬起自以为是父亲的脸让儿子辨认。其实他是想跪下来,这个父子相认的时刻,他理应跪谢天地。
佬佬,你好生看下,我是你爹!他的声音发颤,全身都在打抖。已经大半年时间没有这么近距离面对儿子,儿子长高了些,又嫩白嫩白的。城里的水土就是养人。他想。
那个耳光就是这个时候在他的耳根边炸响的。下手很重,他的嘴歪向了一边,一丝血从嘴角里渗出来。
放开他!这是配合耳光同时炸响的一声雷霆。
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抓住男孩不放,生怕一松手,儿子就会像小鸟一样飞走。
他是我儿。他说,声音几乎带着哭腔。
那只扇他耳光的手再度举起,但是在落下的瞬间出现了迟疑。这个身为男孩父亲的男人被一双乞求无助的眼神打动,心里的愤怒化作了怜悯,他意识到了肯定是一场误会。
你的儿子丢了吧?他说。
嗯。他说。
你先放开他,怎么证明他是你的儿子?儿子,你认识他吗?他说。
男孩惊魂未定,使劲地摇了摇头。
他的屁股上有颗痣。他说。这将是他出示的最有利的证据了。接下来,验证一颗痣便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光天化日之下,男孩的裤子被当众扒开,露出两瓣小光腚。他清楚地记得儿子长痣的部位,那个地方现在却光洁如玉,连一点印记都没有。他不相信眼前事实,瞪大眼睛死死盯着男孩的屁股,恨不能即刻长出痣来。最后,他喊了一声天,天自然帮不了他,若能帮他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
你报案了吗?男孩的父亲问。
报案?报什么案?他反问道。
你这个傻卵!男孩的父亲骂了一句粗话。出于好心,他带他到就近的派出所报了案。提供资料时,他从怀里掏出了儿子失踪前照的相片。儿子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但就是不晓得人在哪里。照片每天被他拿出来看无数遍,四角都磨起了毛边。儿子的确长得像极了眼前的这个男孩,简直就是他本人或者同胞兄弟。他是不是应该庆幸这次遭遇,一个耳光把他打醒了,让他明白了报案的重要。儿子的照片挂在了网上,等于全国的公安都在帮他寻找,这要抵多少人工,光靠他自己,纵然三头六臂也是徒劳的。
日子过得风一样快,四季轮换都好像是一眨眼的事情。说时间会改变一切,但对于他是个例外,改变不了他的信念。几年过去了,儿子依然杳无音信,你以为他会就此罢休就错了,他始终都没有放弃,一刻也没有停止寻找。他曾经碰到过好多摆地摊的算命先生,又去有名的寺庙里抽签和卜卦,还费神拜访过民间传说中的高人,给他们许诺,说哪个若讲准他儿子下落,他将用全部家产谢恩。牵涉到人命关天的事,除非真的是神仙,否则没有人敢答应他的条件。结果他想通了,什么人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有人好心相劝 ,说你们还年轻,趁早再生一个吧。这话妻子听进去了,动了心。女人一旦有了某种念头,是非要去做不可的,她在等待时机的到来。
他从里屋搬出一只木箱,打开,里面装满了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车船票。如果把票面上的地名串起来,将构成一幅密如蛛网般的线路图。他就是网上一只不知疲倦的蜘蛛,常年往返于这些城市之间。他花了几天工夫,将票据按时间顺序排列,然后熬了一锅浆糊,把它们依次贴在几大张拼接起来的报纸上,再挂上堂屋的板壁。于是,家里便有了一幅纸糊的壁画。做完这一切,他仰天长叹:老天爷,你长眼睛了没?你看见了吗?山里人敬畏天地,他们理解的老天爷就是至高无上的神,神若存在,此刻就应该在附近或隐藏在云端里,它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人间的一切行径。正值太阳落土时分,要落不落之际,它要把最后的辉煌留下来,接替它的将是月亮,月亮已经从天空的另一端露出了半边脸。日和月可能就是代表老天爷的两只眼睛,分别看管昼夜。现在光线还很明亮,只是带着一点血的颜色,从敞开的大门斜斜地照进来,正好打在他的脸上,看上去他的面容有些沧桑。他面壁而立,凝神,或发呆。记忆的潮水滚滚而来。从第一张车票数起,那是他最初出发和到达的地方。他看见自己匆匆的影子,上车,下车,然后汇入城市的人流。后来他的目光在某一个点上停顿良久,事实上他可能在那里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一幕,现在想起来不禁泪流满面了。正在忙着家务的妻子几次从他身后经过,没有惊动他,他也没有察觉。妻子看不懂那面壁画,但是她猜得透丈夫的心思,她和他的心都一起痛着。天色渐漸地暗下来,他仍然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站成了一根木桩。
在山里,月亮才能真正显示出它的大而圆来。它每次总是挂在岭岗的那棵大树冠上,从来不会挂错地方。它是纯银打造的吗,要不然发出的光何以和银子相似?老辈人说,好月亮等于半个太阳。有月光照耀,不需要灯也可以做事。以往这样的夜晚,她是不会浪费月光的,总有忙不完的事,但今天她辜负了月光,早早地洗脚,上床,只借助月光纯粹想她的心事,这心事自然和另一件真正的大事有关。
两口子睡在一头,这是年轻夫妻通常的睡法。床铺挨着窗台,月光直接照到床上,看上去月亮近在咫尺,好像贴在窗户上面,只要起身,就可以伸手触摸到它。这些年来,他们聚少离多,难得睡到一起,好不容易同一张床,也往往各睡各的。尽管身体相挨,却都没有反应。沉默是他们达成的默契,交谈不用出声,呼吸,叹气 ,就是他们的耳语,是无尽的枕头话,闭着眼睛也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有时候,他们默契到几乎不约而同睁开眼睛,同时看着窗口出神。开窗已经养成习惯,尤其有月亮的夜晚,他们投向窗外的视线是久久收不回来的。彼此都晓得各自的秘密,都怕说穿,一说穿就会戳到两个人的痛处。与其说是在望月,不如说他们的眼神是冲着月亮旁边的一颗星子去的。它一闪一闪,按乡间说法叫一眨一眨,眨眼睛的意思。他们都清楚地记得,儿子顽皮时,小眼睛就是这样子眨巴的。今夜,星子格外亮些,也就格外牵动了人间的两颗心跟着跳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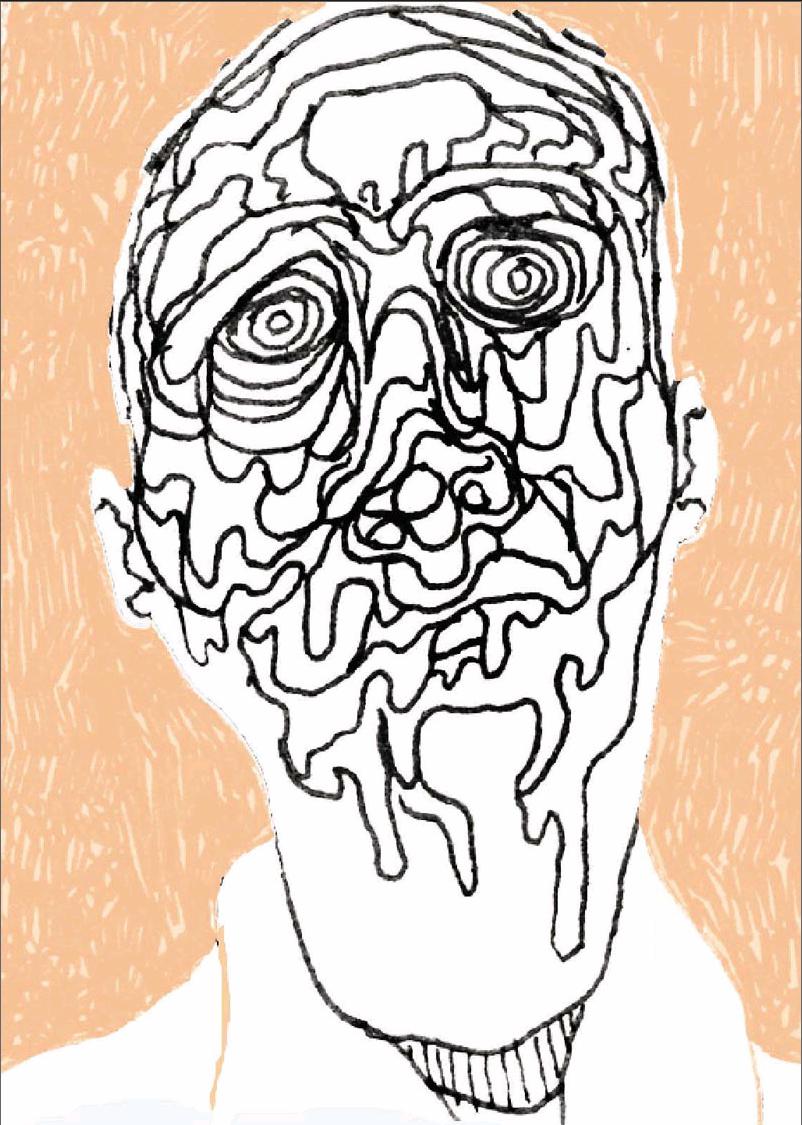
有那么一刻,他感觉身边人出气有些异样,便侧过脸,发现月光下她的眼角湿了,慢慢凝聚成两颗露水般的泪珠,一边眼睛一颗,晶亮的。
你怎么啦?他问。
她趁势抱紧了他,接着腾出一只手捂住他胸脯。这只被锄头柴刀之类农具磨出厚茧的手,既擅长稼穑,又可以充当爱的天使,在解风情方面,是丝毫不亚于别人的。男人有一撮胸毛,她曾经梳理头发一样一遍遍梳理着它。手上的蚕茧不是白长的,对于男人,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蚕茧刮着毛根,如活的蚕虫爬过,形同撩拨,搔痒,男人就在那一刻被调动起来,兴奋得不能自已了。但是今天男人却一反常态,他拒绝了那只手,用自己更有力的手摁住了它,将它视作入侵者,制止了它的侵入。
我已经几年都不想这个事了。他冷冷地说。
我想再生一个儿。闷在她心里的话终于脱口而出。
要生你自己生,又没有哪个阻拦你。他说。这话很适合调情,眼下却不是场合。生孩子怎么是她一个人的事,这分明是在气她。她委屈得哭出声来,泪水由两滴变成了两行。
我发过誓,若找不到儿,这辈子宁愿做孤佬。他说。
是的,他一直是这么说的。她了解他,脾气比牛牯子还犟,儿子是他搞丢的,惩罚自己,就是赎罪。如果再生一个,那么他的心思就在这个身上了,就等于放弃丢失的那一个,这样怎么对得起儿子?
到头来,还是依了他。床上复归平静,不得信鸡叫了三遍,天快亮了。
这次回家,他带来了儿子的消息。一连串的事情,简直像做梦,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事隔12年,人贩子落网,供出了儿子的下落。儿子先是被卖到了一百多里外的邻县乡下,后来随做生意的父母住进了县城。公安还帮他们做了亲子鉴定,证明儿子是他亲生,并且安排好了认领时间。
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两口子欢喜癲了。他们请来了三个木匠,把东头的房间装修一新,又打做了新床和书桌。家里唯一的电灯,原来挂在屋檐下,现在也牵进了新房。他们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但是知道灯光对于读书人的重要。夜深时分,他蹑手蹑脚来到门前,眯起眼贴着门缝悄悄地往里面窥视。在他的想象中,儿子正在熟睡,他仿佛听见了儿子轻微的鼻息或鼾声。这一幕恰好被妻子撞见,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这时候,夫妻俩其实是心照不宣的,明天就要去接儿子,他们已经等不及了。行李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儿子爱吃的灯盏窝,板栗,刚摘的阳冬梨,还有送礼用的两块腊肉和一大包野生木耳。这些城里人有钱也买不到的特产,都装在篾制的背篓里。一应物品,最不该拉掉的是那幅车船票糊就的壁画,他把它揭下来,卷成筒状,并且用塑料纸包好以防打湿。带上它,说明了他的用心良苦。这次出远门非同寻常,穿着要有讲究,妻子翻出了结婚时的嫁衣,想此时不穿再也没有机会穿了。先试了一下,依然合身,便就穿上了,但看上去怎么也不像新娘。而他呢,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将就着挑一件洗干净的旧衣服作罢。
他们就这样见到了久违的儿子。当地警方带着他们敲开了城郊的一幢别墅大门,开门的是一对和他们年龄相仿的男女,大概就是这里的主人了。這对夫妇自己没有生养,却能经商,儿子就生活在这户有钱的人家,算有福气。久别重逢的时刻到了,这一人间仪式,自有天地作证,证明凡违背良心的事,终会得到纠正,一如今天的情形。儿子是这出戏的主角,他是很不情愿被推到前台的,喊了半天,才慢慢腾腾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一副典型的城市少爷形象,脸上稚气未脱,相貌和神态酷似年少时的生父,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意料中的事情发生了,他连背篓也来不及解,就喊了一声“佬佬”,人跟着扑过去,要去拥抱儿子。意料之外的事情也发生了,他扑了空,儿子显然缺少准备,两岁前的经历早已经失去记忆,也不愿接受还有一个乡下父亲的事实。当这个土里土气的父亲真的突如其来地来到,他吓到了,老鼠见猫一样掉头就跑,躲进了自己的房间。接着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叫喊:不——可——能——!
房门很牢实,用很厚的原木做的,敲不开,他便改用额头撞击,嘭嘭地响。打死也想不通,明明是我儿,怎么会不认我,我挪你挪得好苦啊!
回应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
危急时候喊天,是山里人的习惯和本能,他又喊了一声天,天再次塌下来了。
山湾里散布着他的田土,树林,以前劳作,只见妻子孤单的影子,现在有他做伴,两口子从此形影不离了。天地间,他们用行动演绎着夫唱妇随的神话。特别需要二人合作的农活,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冬天是种麦子季节,他挖坑,她播种。锄头扬起,落下,她便将一把草灰连同几粒麦种准确地丢进坑里,动作协调得有如舞蹈。不远处,两只喜鹊在觅食,它们的巢就筑在土坎边的木油树上,巢里的小喜鹊嗷嗷待哺,相比人类,喜鹊父母的劳动显得更有意义。每喂完一次食,喜鹊总要站在枝头叽叽喳喳一阵,将它的喜悦广告天下。传说喜鹊是报喜的信使,它的聒噪,在人间的这对夫妻听来很烦人,不禁悲从中来了。
一天,山路上出现了一个人影,一摆一摆直朝他屋里走来。原来是城里的那个儿子父亲。
见面就只差下跪。说求他们再进一趟县城。
从来人语无伦次的叙述中,他得知儿子精神受到刺激,害了心病,现在不吃不喝躺在医院里,又拒绝打针吃药,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了。医生最后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唯一的办法是让乡下父母来当面认个错,错在误会,承认他并不是他们亲生,这样孩子的心结才有可能解开,得救。
来人打开提包,取出一样东西,放在他的面前。东西用报纸包着,捆扎着,表面形状像砖头,其实远远超过砖头的厚度,由此断定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砖头。
一点小意思。他说。
明白人一听就明白,这是一摞现金,是钱。钱有时候很灵,摆得平好多事情。尤其对于一个缺钱的农人,面对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是难免不动心的。但是在他看来,那就是砖,甚至不值一块砖。他的眼睛望着一边,心根本不在钱上,而是有两个自己的声音在吵架,一个说:连老子都不认,凭什么去?另一个说:毕竟是亲生的儿,怎么能不去?结果第二个声音占了上风,他决定去了。
清早起床,推开门,他的眼睛扎实晃了一下,一夜之间,满世界耀眼的白。老天爷赶在他出门之前把雪下了,足有膝盖深。这是什么兆头?农人很在乎天气,雪的降临给了他好心情,首先联想到年成,雪下得越大心里就越踏实,好像不做功夫都可以坐享其成了。雪又给他即将出行制造了麻烦,意味着要走更远的山路才能搭上班车。当然这难不到他,他的行程是雷打不动的。两口子按时动身,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外走去。脚像绑了磨盘一样沉重,每挪一步都要格外攒劲。至山垭口,必然遭遇那块岩头,想绕都绕不过去,便干脆停下来歇一口气。由于雪的覆盖,岩头一改往日形象,变成没有棱角的雪人。雪打扮了它,戴了帽子,穿了棉袄,也遮掩了它的凶神恶煞相。照一个农人逻辑,他曾无端迁怒一块石头,视其如仇,想起就血翻,碰见就要狠狠地踢它几脚。一回大热天,出脚时才意识到自己打的赤脚,想收回已经来不及了。脚伤得很重,断了大拇指,血流了一地,几个月才复原。那种钻心的疼终身都不得忘记。今天怪了,怪在他没得了脾气,适才还一肚子火,见面居然就烟消云散了。他惊异于自己的变化,究其原因,恐怕就是落雪的缘故,雪能改变万象,也是能改变人心的。于是,人和岩就在那一刻达成了和解。
直到他们走进医院,雪还在下。他们是披着满身雪花进入病房的。儿子斜靠在床头,目光痴呆地望着门口,其实眼睛里空洞无物。一进门,他愣住了,怔怔地看着几步开外的儿子。这期间室内的空气几乎凝固,墙壁上的挂钟也停止了摆动。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艰难地走完了那几步,来到儿子床前。一路上,他都在反复背诵那句违心的话,一再告诫自己千万别说错了,说完他算是最后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就打算尽快回去。可是话到嘴边怎么也说不出口。他心如刀绞,咬紧嘴唇暗暗地用劲,目的就是想把那句话憋出来,临到张口嘴巴背叛了他,却喊出了一声“佬佬!”
儿子听到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接着回叫了一声:爹——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儿子认他作爹了。
雪停了。天气很晴朗。通往山寨的路上,出现了三个人的脚印,路的尽头是他们的家。
选自《广西文学》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