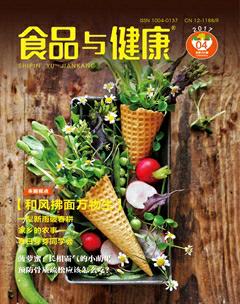古代文人酒趣琐记
潘春华
翻开中国文学史,常常能闻到扑鼻而来的酒香。在我国古代,不知多少文人雅士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饮酒与吟诗作画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常自取或被人赋予了与酒有关的雅号,如“酒圣”“酒仙”“酒狂”“酒徒”“酒雄”“酒鬼”“醉龙”“醉翁”等等,留下许多轶闻趣事。
唐代诗人贺知章人称酒仙,与张旭、包融、张若虚并称“吴中四士”,个个都是嗜酒如命的人。有一次贺知章遇见李白,两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一天,贺知章邀李白对酒共飲,正喝得尽兴,却发现兜里没钱,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解下身上佩带的金龟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金龟乃御赐物品、官品标志,真让人替这位贺大人捏把汗。
李白更是爱喝酒,他自称“酒中仙”,人称“酒圣”“酒仙”“酒星魂”。他一生喜酒、爱酒,写诗著文时尤其离不开酒。饮酒几乎就是他生命的第一需要。因此,无论得意、求仕期间,还是隐居之时,也不管何时何地,人多人少,有钱没钱,他都要想办法喝酒。暮年时,甚至将自己心爱的宝剑换了酒喝。他不但喜欢饮酒,而且几乎每饮必醉。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称:“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曾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以至后来“游采石江中,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真是“生于酒而死于酒”。
辛弃疾一喝就醉,还爱把醉酒的事儿记下来。他在《西江月·遣兴》中写道:“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诗人喝醉了,把松树看成了人,就问他:“我醉得怎么样啊?”恍惚中看见松树活动起来,以为是要来扶自己,于是就不耐烦地推推松树说:“走开走开!”这首词给人一种孤傲潇洒的感觉,没有半分矫揉造作,一个“去”字是词眼,有一分的寂寞,却有十分的傲气。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喜欢饮酒。他在范县当县令时,公务清闲,常邀三朋四友猜拳行令,喝醉了还掀桌子、撂板凳发酒疯,简直有损县太爷的威仪。结果这事儿传到了夫人耳朵里。夫人一顿猛批后,规定其工作期间禁止饮酒,下班后才能喝三壶。可见夫人对郑板桥还是相当宽容的。
饮酒最有度的是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苏东坡一生爱酒、饮酒、写酒,可是绝称不上酒鬼、酒仙或者酒徒,他是好而有度,嗜而不酗。他的酒量不大,不超过五杯,每次饮酒,适可而止,饮不及乱,中规中矩。他自己喝得不多,却喜欢看别人喝酒,欣赏别人的醉态,揣摩别人的感觉,把此当作一种乐趣。他自己呢,则常常举着一个空杯,无酒当有酒,未醉当已醉。苏东坡饮酒适度,寻找“适醉”“醉中有醒”“醒中有醉”的境界。而在这似醉非醉、飘飘欲仙的感觉中,妙诗佳句呼之即来,锦绣文章一挥而就。
北宋诗人钱惟演生病康复后,第一件事就是喝酒,“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生怕杯子小,酒斟得太少。那种急着喝酒的馋相栩栩如生。读其诗,让人有如见其人、临其境之感。魏晋时期大酒鬼刘伶,常乘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锸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东晋有个叫毕卓的吏部郎,夜间醉后偷饮邻人之酒被缚于酒瓮边,天亮时主人见是毕吏部,大惊,解缚谢罪,而他却大笑:“让我闻一夜的酒香,多谢了。”
尽管关于古代文人与酒的趣闻不胜枚举,说起来滔滔不绝,听起来津津有味。但饮酒并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酗酒对身体是有害的,切勿好酒贪杯。花看半开,酒至微醉,才是恰到好处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