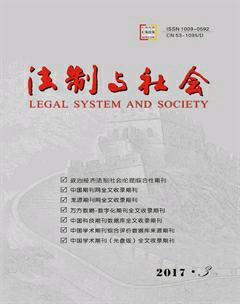浅析隐私权语境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
摘 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功利性与正义性平衡的立法价值中所具有的推定逻辑与隐私权保护存在现实的冲突,但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置和对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进行限制统一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要求,因此,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限制符合法律的基本理念,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隐私权 平衡 限制 正当性
作者简介:王赞,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研究方向:检察理论及实务。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3.320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价值中的推定逻辑与隐私权的冲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反腐败形势下寻求功利性和正义性的平衡点而产生的一个罪名,由于现代腐败犯罪手段的隐蔽性和司法资源的限制,控告方往往并不能彻底地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的增加与犯罪有关,而将证明责任转移给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同时赋予该罪的嫌疑人主动排除怀疑的机会,即在司法机关责令其说明时,主动提供其财产来源合法的证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价值在于既不放纵腐败犯罪,又不破坏刑法原则,从而在立法技术手段上实现功利性与正义性的平衡。
但无论以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价值进行解释,都无法排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存在着推定的逻辑。这种推定逻辑使得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将自己的财产状况进行公开的负担,并且这种负担往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的。当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被问及巨额财产的来源时,如果其认为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并且属于公民的隐私而不愿进行说明,这就产生了公权力和隐私权现实的冲突。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限制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正当性分析
(一)隐私权到公共利益为止
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财产状况亦是隐私权的重要保护对象,然而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保护应当遵循不同的原则。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中,国家工作人员在财务状况方面的隐私权应当保护抑或限制,关键看该隐私内容是否已经触碰到了公共利益。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角度来看,通说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内容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要求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学习学历、社会交往、财产收支等私人领域信息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勤政廉政情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状况等私人信息内容的公开已经成为公共利益的要求。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优越于普通公民的地位,因此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决定了这种对于巨额财产持有状态的社会危害性必然有别于一般社会公众,该巨额财产与腐败行為存在高度盖然性的联系,国家工作人员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危害是普通公民实施同样的行为所不具备的。因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也符合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二)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博弈
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诚然有来源合法之可能,对其公开会导致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社会道德评价降低或者使其产生道德方面的不安全感。如国家工作人员受人包养所得巨额财产,在现有刑法体系中并不必然构成犯罪,但显然属于当事人的隐私权内容,并且这一情形极有可能造成当事人的社会道德贬损。因为隐私权本来就是与道德判断更为相关的一个社会问题,人们是将社会道德标准内化为自觉行为而对隐私加以保护。
在刑法的框架内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持有状况及来源的探究,是一种关于罪与非罪的法律判断,应当遵循法律判断的逻辑和标准,对于当事人隐私权的考虑则是在维护其社会道德评价。相比之下,法律判断的标准显然更加刚性,并且法律判断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程序,应当在适用中优先于道德判断,保护隐私权的道德成本显然不能成为妨碍法律判断的理由。因此,即使并非是违法手段获得的巨额财产,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的过程中,仍有必要进行公开,通过限制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为正确的刑事司法判断提供条件。
(三)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规定与国际的接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0条规定各缔约国应考虑采用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资产非法增加,即公职人员的资产显著增加,而本人无法以其合法收入做出合理解释”的行为定为犯罪,这说明国际社会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视为具有更大隐蔽性的腐败行为从而认为有予以打击的必要,于是对这种行为做出了犯罪化的要求。
我国刑法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补充,说明我国刑法在打击这种高隐蔽性腐败行为的立场上与国际是接轨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置与现代腐败犯罪的高隐蔽性密切相关,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状况方面的隐私权进行限制也是必要的和无法避免的。在国际社会加大反腐败力度的趋势之下,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惩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行为,有利于我国国内立法与相关国际公约的衔接。
三、对“不愿说明”巨额财产来源情形的认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过程中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进行必要限制是具有正当性的,笔者认为该“不愿说明”情形的说服力因此受到了严重削弱,其应当与“不能说明”承担同等的后果。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是将国家工作人员持有巨额财产以推定的逻辑认定为不法的状态,实现功利性的效果,同时给予当事人说明来源的机会作为救济的手段,以维护其正义性。因此,作为一种在推定逻辑下自我救济的机会,持有合法巨额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应排斥对于该巨额财产来源的说明。并且,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具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正当。综上,持有巨额财产而“不愿说明”其来源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应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一些国家对巨额财产来源的说明标准比我国要高出很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不以该国家工作人员仅对财产来源做出说明或解释为限,如香港、新加坡就要求做出圆满解释, “不愿说明”显然是不能排除国家工作人员的证明义务和腐败嫌疑的。
四、从实践中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价值在于实现功利性与正义性的平衡状态,因此在该罪的认定中存在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限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生活的基本安宁状态也应当受到尊重,国家工作人员合法的隐私权应当受到保护。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中,应当维持惩治腐败犯罪和保护私法权利的平衡,避免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公民所享有的隐私权发生过度侵犯。笔者认为,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并不存在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过度侵犯。
在司法实践中,鲜有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单独立案的情况,本罪进入司法机关的视野多是在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其他经济犯罪等已经进入侦查程序之后。 侦查机关在发现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贪污、受贿等腐败情节后,又发现其具有超出合法收入水平的巨额财产,这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与腐败犯罪联系的盖然性被放大,必然引起一般社会公众强烈的抵触情绪以及对其合法性的高度怀疑,也就更有说明来源的必要。因此,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等隐私权内容并没有被积极主动的探究,而是在腐败的盖然性放大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才具备了调查的必要,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过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尊重。
综上所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中存在着功利性与正义性结合下的推定逻辑,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国家公权力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冲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与对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在保护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不应以隐私权为理由对财产来源的说明进行排斥,否则应当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承担刑事责任。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当腐败的盖然性放大至必要程度才会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状况等隐私内容进行探究,并不存在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过度侵犯,符合功利性与正义性平衡的立法价值。
注释:
时延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理研析.法学.2002(3).39-43.
王治东.哲学与文化视角下隐私问题的探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9-12.
杨俊.完善我國贪污贿赂犯罪刑罚设置的省思——侧重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角.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37-42.
王敏.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思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108-110.
张旭、王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价值及其法定性分析.法制与社会.2007(5).33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