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选讲
管子选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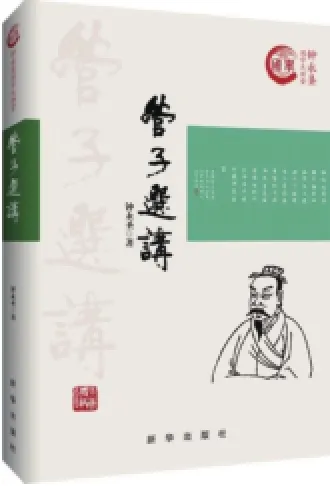
钟永圣 著/新华出版社/2017-01/58.00/9787516630266
本书是作者系列讲座的结集。作者首先以亲和力的语言,向读者传授了学习传统经典*重要的三个方法——“以经解经”、“体慧”,以及“至诚诵读”。作者重实践的“体慧”而非仅止在知识的了解,重至诚的感悟而不拘泥于学术的辩驳,在他的充满智慧的讲解下《管子》不再是玄之又玄的“天书”,是一部人人都能看得懂,获得切实的启迪和智慧,从而改变自身命运的读物。
《管子选讲》书摘
许久了,人们谈论春秋“诸子百家”,总是儒、墨、道、法、兵、阴阳,忘了还有“管”家,忘了以“经济家”为代表的齐国“稷下学派”曾经那么举足轻重、那么独领风骚、那么称一时之盛。
按照出生时间的先后顺序,管子实际上是“春秋第一子”,老子、孔子、墨子、孙子、韩子皆生在其后;如果把以管仲为代表的思想理论体系称为“管家”,那么管家其实也是“春秋第一家”,齐国正是凭借管家思想才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因此《管子》一书,也就是“中华经济学第一书”,上海财经大学已故的胡寄窗教授称其为“一本伟大经济巨著”,认为《管子》全书以“经济”为论证主题“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我们说其第一,并非是把它评价为中华传统经济学的“创始”,而是指《管子》论述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文献上“最完备”、在战略上“最理论联系实际”、在国家经济策略上“最集大成”。
孙中山先生解释“政治”为处理众人之事,中国文化中“经济学”本来就是“政治的”,本不需要在“经济学”前加“政治”这个限定语。之所以还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是顺应近代以来借鉴西方的文化概念早已经形成的表达习惯。有些文化语汇一旦形成,就成了约定成俗的观念,不暂时将错就错似乎就无法沟通。要想彻底地扭转偏见和误解,只能依靠长时间的历史验证。
华夏文明的传统经济学核心理念创始于《易经》,《乾卦·文言》中说:“利者,义之和也。”指明了取利的原则和财富的伦理来源。这一理念源头是如此重要,不但体现了华夏文明“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且清晰地阐明了“利”的贯通性质:物理上的利,实际是伦理上和气的体现。利,因和气而成为“益”,因争夺而成为“害”。一种所得到底是“利益”还是“利害”,不是由资本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当事人心念和行为的伦理性质。例如,同样一笔钱,因为捐赠而成为“善款”,因为贪腐而成为“赃款”;作为生产和分配决定因素的资本,一方面可以因为拥有者的自私与残酷,成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另一方面也可以因为拥有者的关怀与善意,成为“匡扶正义、兼济天下”的善财之源。
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学者把这种“贯通各学科”的现象称为“跨学科”,实际上是未能彻本知源的提法,因为社会科学学问的实质本无学科界限。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中也有一些人大谈“人本经济学”,同样是不能明心见性的未到之语,人有善恶好坏诸种不同的表现,试问经济学到底要“本”哪一个“人”?最根本的说法在中华传统经典里,例如曾子在《大学》里表达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最彻底的说法应当是“德本经济学”。
说到经济的“德本”,超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界限。西方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首要问题,只在财富的“物”象上做文章,始终未能深入到财富的“本”地。而中国传统经典往往以达到“学究天人之际”境界的语言,一语道破“财富的来源”。例如,《易经·坤卦·文言》中指出“厚德载物”,明言德行积累不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承载(获得)一切“物”质财富。再如《道德经》中指出“道生一二三乃至万物”,清晰地指明作为万物中的一物的财富,在根本上是由“道”生发出来的。可是由于世间人大多数不明“道”,所以还是对“财富的来源”不明所以。这样,老子在《道德经》的结尾就直截了当地把答案和盘托出:“即以为人己愈有,即以与人己愈多!”那就是说,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己拥有的就越多;给出去的越多,自己收回来的也就越多!
人类社会在伦理上界定“为他人”是公、是善、是德,界定“给出去”是公、是善、是德,这正是对“德本财末”观念异曲同工的解释。《黄帝内经·灵枢·本神》中说“天之在我者,德也”,说明“我”要想发财,就必须积“德”;我要想积德,就必须遵守“天”的规矩。“天”就是自然,自然的规矩就是“天道”,就是“天理”。天理化为人间的规矩,就是人伦,人伦的具体内容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管子恰恰明确地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以此作为治国理政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在齐国倡导中华伦理经济学,最后在短短二三十年间,“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把齐国送上霸主地位,影响后世几百年。以至于孔子都感慨地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至于孔子以圣人境界,因管子未能倡行王道、复兴周室而“小之”,导致后世既无实践经验也无圣人境界的儒生居然也长期轻看管子及其学说,实在是自命清高、因噎废食、求全责备、流弊深远的憾事!
以现代分科的角度看,管子经济学是伦理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统一,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统一,是政府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的统一。在中华文化中,“经”指恒常之道,是最权威、最彻底、最合适的“理性”;“济”的本义是过河,引申为周济、帮助、与乐和拔苦。综合起来,“经济”的本义是指“以最智慧、最无害、最有益的方式让天下人民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全方位满足”。绝不仅仅是西方起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那个研究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这种文化翻译的历史误会,据某些学者考证,肇始于一个叫神田孝平的日本人,他在1892年前后把economics这个词汇翻译成汉字的“经济学”,导致当时没有文化自信的国民以为自家没有经济学,这一错就是一百多年。其实管子经济学恰恰是包括但不限于资源配置的经济学;是强调与时竞而不与人争的经济学;是圆觉的智慧而不是局限分科的经济学。
以今天的学术视角来看,《管子》的根本理念都是“跨学科”的论述,既是伦理的经济学,也是政治的经济学,更是行为的经济学。例如,管子论述德、义、礼这些伦理内容都是以实实在在的经济内容为依托的:德有六兴(另一说,叫六典),分别是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和振其穷;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纤、啬、省用,以备饥馑;礼有八经,分别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在这样的理论体系内,涵容着解行相应、知行合一的智慧,绝不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所批评的那种远离真实的“黑板经济学”。
之所以很确切地说《管子》中所述的内容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因为管子时刻把国家的治理与发展经济统一起来。例如《管子》开篇就提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那么怎么能达到天下大治呢?管子认为只要热爱人民,利益大众就能做到:“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天下治矣。”利益大众,治理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富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
如果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从“党的富民政策”开始的!不能不佩服管子论述国家治理政策见解之深。如果我们放眼当今世界上那些动荡的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能不说是从国家思想价值观念的局势混乱开始的,越乱越贫,越贫越乱,越乱越无法实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能不佩服管子论述伦理经济理念之高。可是,即使这些很有现实说服力的论述被人知晓,仍然不能使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拥趸消除对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鄙夷和不屑,常常提起“人家”西方经济学有多深刻和多科学!例如说亚当·斯密论述人性自利多么有洞见,由此“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论证的起始点而被广为传诵。那么我们不妨看看《管子·禁藏》篇中论述人性自利的思想有多么深刻,而其文言又有多么美:“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孵卵,无形无声,而惟见其成。”
特别是最后几句,“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相当于把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用十六个字就论述完了,精彩绝伦。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号召大家“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管子》以中国古代文化的表达形式阐述的传统经济学具有鲜明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如果我们很好地梳理和总结,它同样可以有现代学术规范所需要的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不但内容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语言上具有独创的中国风格,而且在境界上更具有安定天下、傲视群雄的中国气派。
恢复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挖掘和整理,恢复中华经济学的本义,以使大众树立正确的经济观念,具有正本清源的教化作用。 通过传统经典的温习以在文化源头上认祖归宗,可以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摒弃“人在局限条件下利益最大化”的错误经济观念,可以挽救世道人心;确立经济学“善财利生,普济天下”的“中国标准”,可以造福世界。

